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普遍仇恨苏联,是有原因的。就拿阿塞拜疆来说,首都巴库市观景台核心位置是长明之火,用来纪念1990年2月阿塞拜疆独立运动中被苏军杀死的抗议者,旁边的公园里埋的就是当时的死难者,每天都有人献花。 那团火,一直在燃。不论风雨昼夜,哪怕气温零下几十度,它也不曾熄灭。站在那片高地上,俯瞰整个巴库城时,仿佛能感受到火焰下埋藏的愤怒。烈士墓一排接一排,石碑上镌刻的不是将军,而是大学生、工人、普通市民。他们不是战场上倒下的士兵,而是被自己的国家——那个名叫苏联的庞然巨兽,用坦克、枪炮碾碎的抗议者。 这一切并不是突然爆发的。在更早之前,阿塞拜疆人就已经积累了太多怨气。民族认同被压制,语言被边缘,经济资源长期被巴库以外的“中央”掠走,而他们想要说话,却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最初的抗议,只是围绕纳卡问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那个阿塞拜疆境内的自治州,一直是阿亚两国争端的焦点。当亚美尼亚方面提出将其并入本国时,阿塞拜疆民众的愤怒被彻底点燃。 游行迅速蔓延。自由广场人山人海,年轻人高举标语,老人手捧照片,要求中央政府给出回应。起初只是和平请愿,但很快局势失控。一部分示威者开始拆毁苏联象征的雕像,有人袭击苏共地方党部,有人公开焚烧红旗。空气中弥漫的不只是怒火,还有彻底决裂的情绪。苏联当局开始紧张,巴库局势被列入最高级别处理。 戈尔巴乔夫下令出兵。精锐部队从北高加索调动,坦克、装甲车、步兵夜间进城。行动代号保密,民众毫无准备。1990年1月19日深夜,巴库全城停电。随后苏军分三路突入城区,封锁通讯、占领广播台,坦克沿主干道推进,对人群无差别开火。街道上鲜血横流,汽车被压成废铁,住宅窗户被子弹打穿。那一夜,至少130人当场死亡,更多人重伤,现场惨烈到连军医都说“不忍多看”。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但城市已然变色。几十万市民聚集在自由广场,自发组成送葬队伍,护送死者遗体前往巴库南山上的高地公园。他们不喊口号,也不再举旗帜。沉默成了最强烈的控诉。这一行为没有组织者,却异常有序。那天晚上,高地上升起了第一缕烟火,也就是后来“烈士路”的起点。 这些死者不再只是抗议者,而成了民族的象征。他们的葬礼就是对苏联统治的公开告别。从那以后,烈士路不断扩建,逝者不断增多。从黑色一月的死难者,到纳卡战争的阵亡士兵,阿塞拜疆把所有的痛苦与牺牲都集中埋在这一处。一个城市的记忆,一个民族的哀悼,被集中塑造成一块块墓碑。 但阿塞拜疆人不满足于哀悼。他们要复仇,要独立。黑色一月之后,政府内部出现裂缝。很多地方党干部辞职,有的公开谴责莫斯科的军事镇压。中央权威开始动摇,本地民族主义力量趁机崛起。报刊上开始刊登被禁言已久的民族诗人作品,电台里传来本土音乐,连课堂上也开始教授历史中被掩盖的章节。整个国家的神经,从恐惧转向奋起。 烈士路也不再是悲伤的象征,而成了鼓舞士气的战场。1994年后,阿利耶夫家族掌权,推动烈士路全面升级。他们修建纪念碑,点燃常燃之火,请来艺术家设计八角星座与透明穹顶。这不是普通的纪念,而是一次强烈的国家认同重塑。它告诉人民,那场屠杀不能被遗忘,那些血不能白流。 这团火,于1998年正式点燃,自此再也没有熄灭过。每年1月20日,整个国家进入默哀日,列车停运,商场暂停营业,电视台全天播放纪念节目。孩子被带到烈士路看碑文,老人会在碑前留下鲜花。这个国家用实际行动记住了历史。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把它写进日历、刻进城市、烙进每个人的日常。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阿塞拜疆,你几乎见不到苏联的痕迹。街头不再有列宁像,纪念馆不展苏军功绩,甚至很多苏联时期建筑也被悄然拆除。他们不想遗忘,但更不愿被代表。他们用一场血火洗礼,从“加盟共和国”变成“主权国家”,从“被统治者”变成历史的书写者。 而那团火,依旧在燃。照亮的不只是墓碑和山岗,更是整个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走过屠戮、沉默、觉醒、抗争,最终在烈士路尽头,走出属于自己的未来。阿塞拜疆人记得血,也记得火。更重要的是,他们让下一代也无法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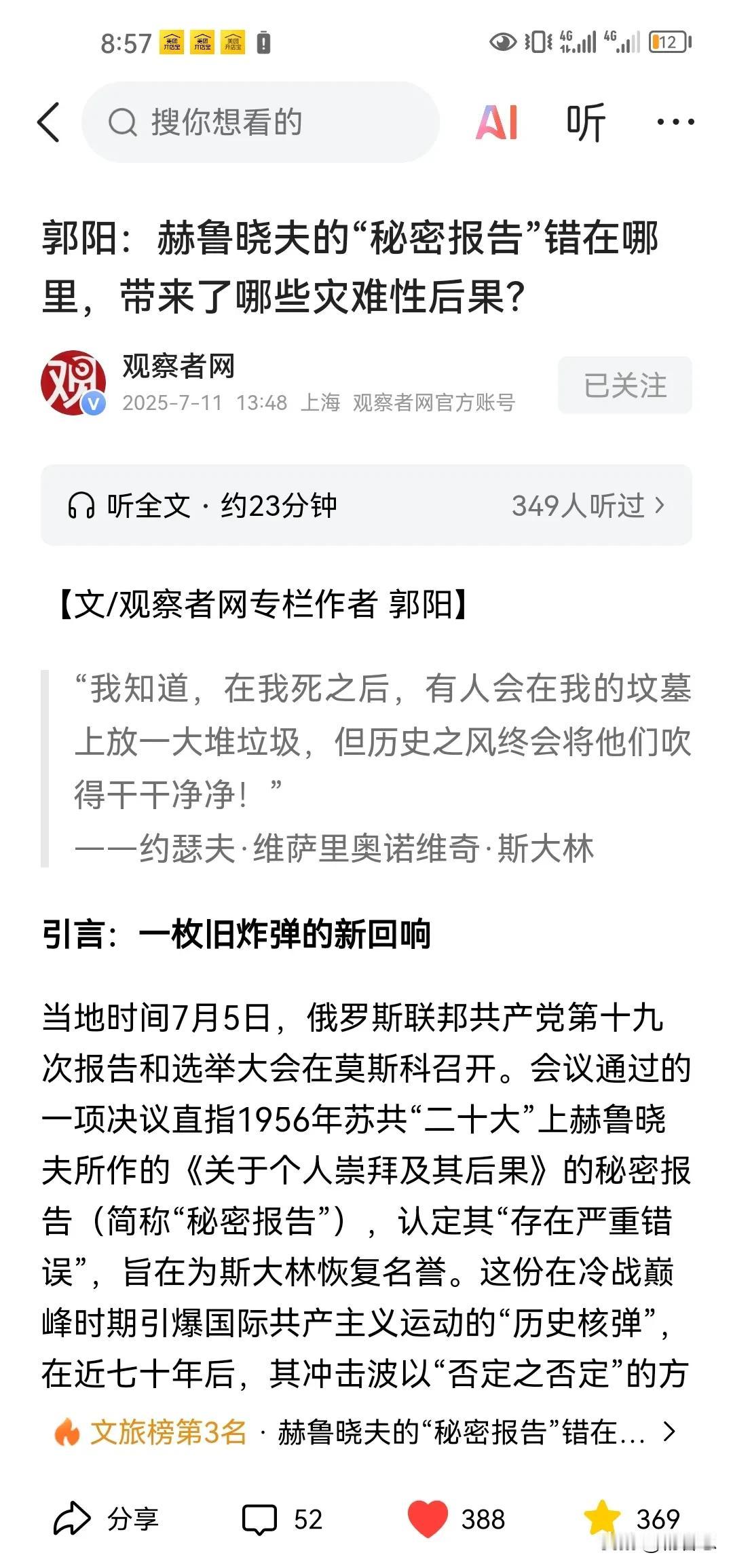






goldf
ngo节奏
用户11xxx20
小编发此文,其心可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