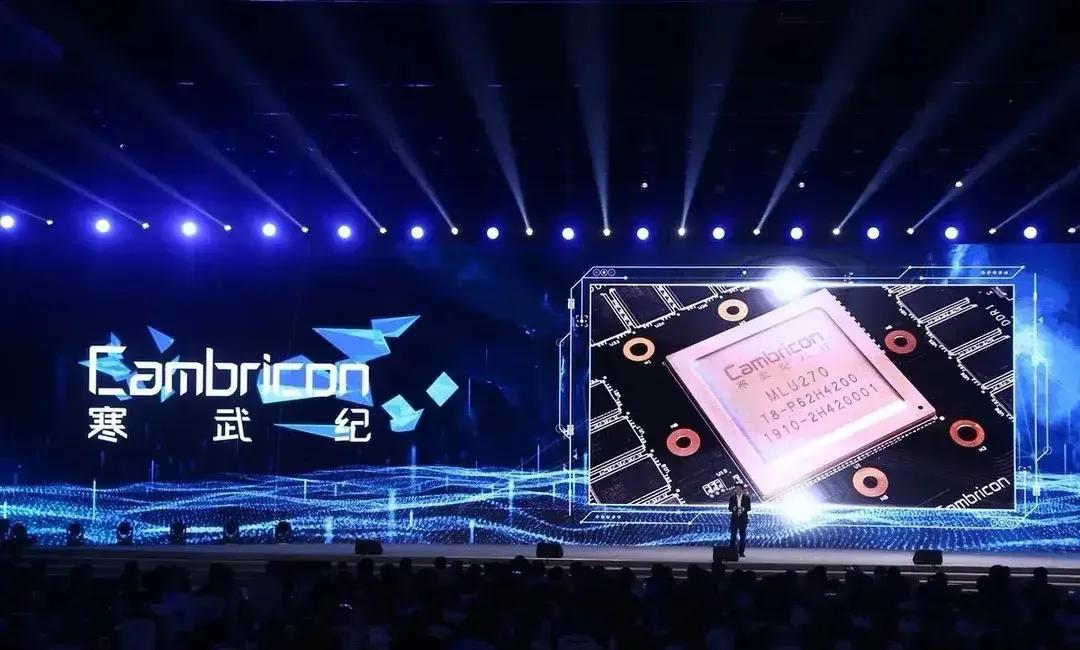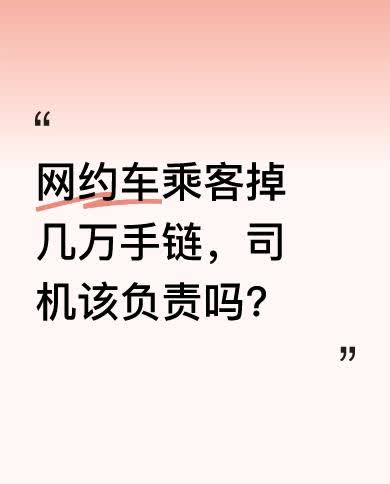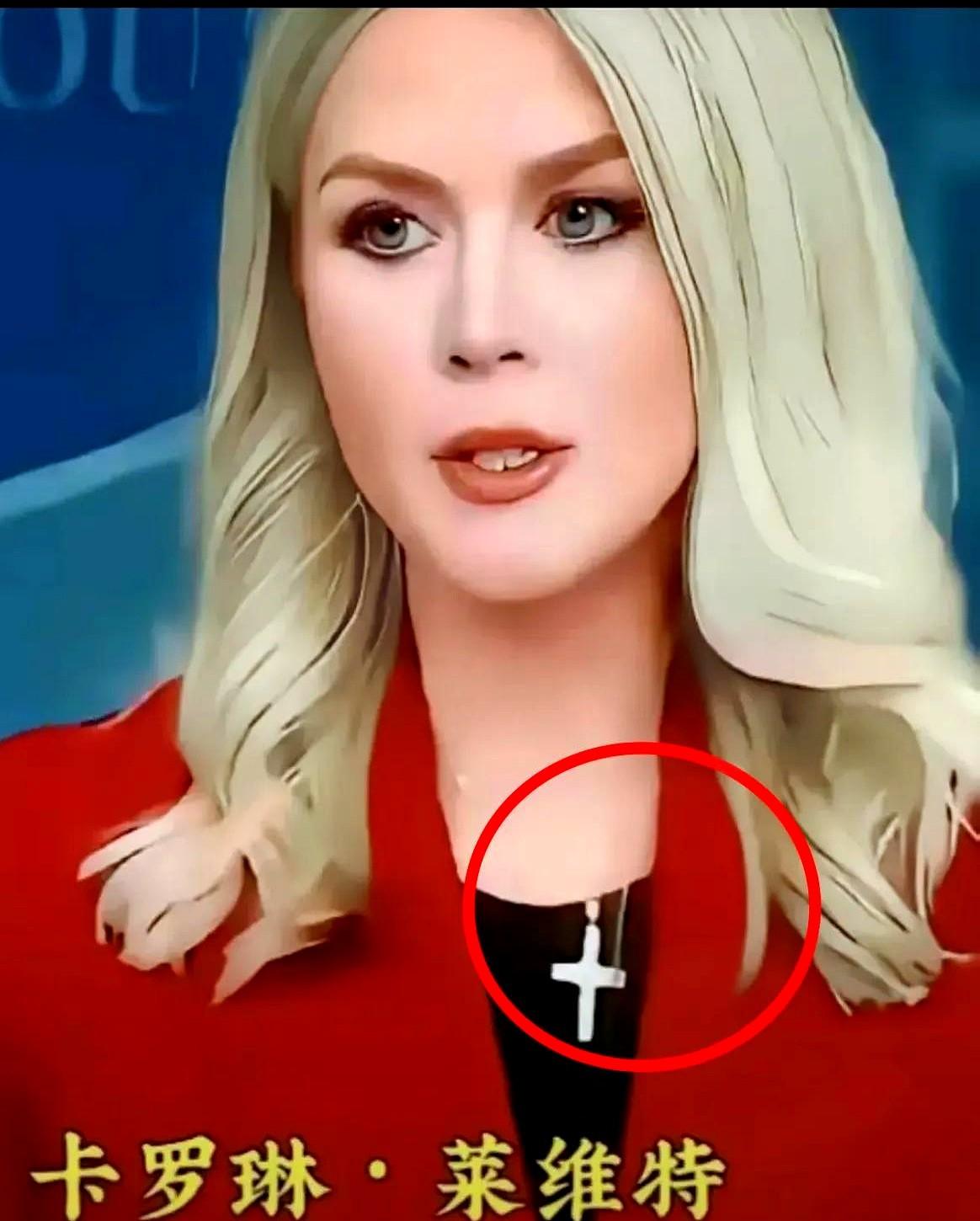几年前在旧稿里提过的那场对话,至今仍像深夜的潮水漫上心岸。记得推开病房门时,消毒水混着中药味扑面而来,心电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里,老前辈半躺在病床上,形容枯槁却仍挣扎着要坐起身。他插着留置针的手微微发颤,指节上暴起的青筋像老树虬结的根。 “别忙乎,躺着说。”我按住他的肩膀。他却执意要将床头柜上的保温杯往我手边推了推,杯口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凹陷的眼窝,“小同志,你看这医院的白炽灯多亮啊。”他忽然望向天花板,“我年轻时总嫌日光不够长,现在倒觉得,这病房的灯把时间都照得明晃晃的,每一秒都能听见沙漏漏沙的声音。 那些日子,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清醒时会絮叨着年轻时下乡考察的见闻,讲着讲着突然沉默,伸手摩挲贴在床头的全家福;迷糊时又反复念叨某个未完成的研究数据,像在追赶随时会消散的幻影。医院的走廊永远回荡着轮床轱辘声,而他的故事,却在这喧嚷里织成了一张细密的网,将生命的脆弱与坚韧、遗憾与豁达,尽数裹进了我记忆的褶皱。
几年前在旧稿里提过的那场对话,至今仍像深夜的潮水漫上心岸。记得推开病房门时,消毒
风景如画看社会
2025-04-19 11:47:11
0
阅读: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