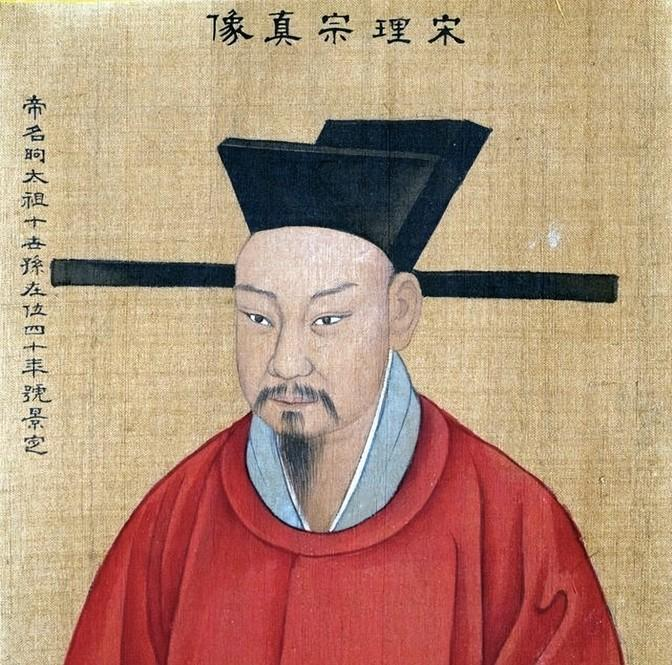大明最为忠烈的臣子,死于公元1457年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京师崇文门。 这一天,巍峨的城门外,皇家刽子手正在准备处决一名皇帝钦定的犯人。 这犯人虽然带伽落铐,但步态稳健,神色从容,很显然,他对死亡似乎并不恐惧。 沿街百姓夹道相送,人群中不时传出阵阵呜咽声。 远处山峦起伏,烟波浩荡,落日融金,一派河山大好。 这犯人驻足远眺,眼中目光闪动,已然泪湿眼底。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英雄人物。 刽子手手起刀落,一腔热血洒满天际,云层红褐如血,一片萧条和落寞。 这一天,明朝史书上只有寥寥四字的记载: 天下冤之。
于谦的父亲于仁,是个不折不扣的追星族。 老爷子不追倡优,不追戏子,专门追随一位叫做文天祥的人。 文天祥是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名臣,抗元将领,一生忠心为国,悲愤慷慨,气势豪放,是典型的仁人志士。 于仁仰慕文天祥的气节,自己虽然姓于,但却在家里专门供奉了文天祥的牌位,日日焚香诵经,从不间断。 结果这么一来二去,竟闹出一桩十分奇异的坊间谣传。 据说于仁的儿子于谦出生当晚,于仁曾经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绯袍金幞的神人从天而降,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先忠肃公年谱》:“吾感汝父子侍奉之诚,顷即为汝之嗣矣。”
我乃南宋文天祥,感怀于你们于家对我的供奉,更欣赏你们于氏祖上一门忠烈,遂转世投胎,来做你们于家的子嗣。 梦醒不久,于谦就出生了。 这一段记载,并非正史,只是写出来给各位读者朋友们做个分享。 于氏一家,祖籍是在杭州府钱塘县,于谦的祖父在明洪武年间做过工部的主事,父亲于仁素有才学,但无心仕途,于是便在钱塘隐居。 和淡泊致远的父亲不同,于谦同志生来就是一个志向高远,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儿的人。 他和他的父亲于仁一样,都是文天祥的死忠粉,所以在他的年少时代,他时常高悬一幅文天祥的画像在身侧,十几年如一日的参拜。 七岁时,钱塘县里来了个游方和尚,到于府讨要斋饭,得见于家的小公子于谦,不住地发出感叹: 《明史》:“他日救时宰相也。”
这孩子不一般,长大之后是可以拯救世间的人物。 和尚的话,于家并非放在心里,于谦也并不在意,他年少即胸怀壮志,谈不上想要拯救世界,但却总想着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儿。 对出身并不富贵的于谦来说,想要干大事儿,无非是四条路。 其一,是经商。 江浙多富甲,奇商遍天下,如果用心经营商道,便可经商致富,到时富甲一方,可做一个扶贫济困的“小孟尝”。 其二,是务农。 江南气候温润,独得天地之造化,水土养人,更养得出四时风物,如若扎根农业,到时良田千顷,钱粮满仓,想来也蔚为壮观。 其三,是研工。 明初科技繁荣,坊间奇人异士居多,如钻研奇门遁甲,通晓天文地理,也可以名动一方,成为乡间传颂的奇才。 但无论是做生意,做农民还是做手艺人,于谦似乎都不是很感兴趣,他唯一有兴趣的,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 致仕。 于谦的理想从一而终,他终生的志向,就是可以成为像文天祥那样“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读书人,只愿肝脑涂地,报效国家。 而这个理想,很快就得以实现了。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于谦一路科考,最终考中当年辛丑科进士,成为了大明王朝的一名公务员。 永乐皇帝的时代,是名臣辈出的时代,内阁中的大臣们,如杨荣,杨士奇,夏元吉,无不是天纵奇才,响彻世间的名臣,所以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于谦,并没有得到什么重用。 孟子曾说: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天如果要把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一个人,必然要千方百计地磨炼他,让他的意志受到挫折,让他的身体经受疲累,让他挨饿,让他百无聊赖。 于谦有没有读过《孟子》作者无从得知,但上天对他的磨炼却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盛况空前的永乐盛世,命运没有给于谦太多机会,它只是轻轻地告诉于谦: 不着急,你要慢慢等待。 这一等,就等到了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 这一年,受封在乐安州的汉王朱高煦举兵叛乱,打算复刻一下自己父亲朱棣的“靖难之役”,把自己的侄子,即宣宗朱瞻基拉下马来,自己当一回皇帝。 宣宗仁慈,实在不忍刀兵相见,于是皇帝打算选派一名御史前往汉王的营中,予以招降。 而这个被选中的人,正是时任御史的于谦。 汉王是个鲁莽粗暴的人,于谦区区一介文臣,深入敌营,实可谓是九死一生。 三军帐中帅旗高挂,宝剑高悬,数万士卒挥戈呐喊,这场面着实让人胆寒。 但对于谦来说,这却只是小场面。 为臣者,但求杀身成仁,不负皇恩,所以此来,生死不惧。 他只身去到汉王的营帐之中,面无惧色,见了汉王更不胆怯,反而高声斥责,正词崭崭,声色震厉,痛斥汉王篡权谋逆,乱臣贼子的行径。 而这个饱经沙场,也算一代枭雄的汉王朱高煦,在于谦如此凌厉的攻势之下,居然跪倒在地,连连称罪。 《明史》:高煦伏地战栗,称万死。
由是,在于谦的帮助之下,宣宗朱瞻基不废一兵一卒,就平定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在汉王叛乱中表现出色的于谦被宣宗皇帝所倚重,令他巡抚江西府,而于谦更是不负期望,短短数月,就平反冤案数百起,政绩斐然。 仁宗朱瞻基对于谦十分器重,但他的儿子,即英宗朱祁镇却并不是一个能信任臣子的人。 年轻的小皇帝初登帝位,最为信任的不是大臣,而是一个叫做王振的宦官。 王振,大明王朝初代权宦。 在王振的时代里,皇帝是他的掌上玩物,大臣是他的门下走狗,整个明朝的军政民大权,他一手掌握,堪称滔天的权势。 那时节,君无君威,臣无臣节。 小皇帝朱祁镇唯王振之命是从,王振让他往东,他绝不往西,王振让他吃苹果,他绝对不吃梨。 帝王尚且如此威仪扫地,朝臣们更多有趋炎附势之态。 京官为求自保,纷纷投身于王振门下,而地方官员为了不被打压,但凡进京,必然要携带厚礼拜访王振,对其予以重贿。 当然了,有臣子屈节,必然也有臣子守节,而当时的守节派代表,正是于谦。 于谦在地方事务繁忙,一年到头,进京奏事没有十回也有八回,但奇了怪了,无论于谦去多少回,每次去总是两手空空,而且从来不去拜访王振。 同僚时常规劝于谦,让他明哲保身,该送礼总是要送礼的,你在地方素来清贫,无钱可送,送点当地的土特产总是可以的, 面对臣僚善意的劝告,于谦不以为然,每次都甩一甩宽大的官服,只轻轻说四个字: 只有清风。 于谦如此做派,王振自然心怀恼怒,于是利用手中权柄,刻意打压,将其逮捕,投入了监狱之中。 王振势力庞大,收拾于谦这样的地方小官,本质上来说,就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但让王振没有想到的是,他收押于谦的行为却在天下间激起了一层厚重的波澜。 《明史》: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
山西,河南两地的百姓们成群结队,赶往京师,跪在宫门前,联名上书,请求释放于谦,朝中更有诸多宗族和官员为于谦伸冤,打抱不平。 可以看得出来,于谦在人民群众中的基础,不是一般的大。 昔日后蜀孟昶举国投降,有蜀中百姓千里相送,今日于谦落难蹲了大狱,更有千万百姓伏地跪拜,以性命担保。 王振迫于压力,只好开释于谦,官复原职。 看来,所谓史书之评价,只能兼听,而人民群众的评价,永远是最为公正的。 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于谦卸任地方,调任京师,担任兵部左侍郎。 或许是冥冥之中上天有感,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人事调动,却成了大明王朝的神来之笔。 因为一年之后,即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就去瓦剌留学了。 当年七月,蒙古瓦剌部滋扰边境,明朝不厌其烦,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年轻的英宗皇帝带领数十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弄了个灰头土脸,折戟沉沙,不仅大明精锐尽丧,朱祁镇本人还被瓦剌人给俘虏了。 战场失利,皇帝被俘虏的消息很快传回了北京,京师震动,举国为之震惊。 面对如此巨变,朝廷里的大臣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 所谓商量对策,其实无非是议定是战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