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二战时期日本第一批娘子军,下场比慰安妇还惨,可却一直坚信自己是为国奉献,直到回到家乡的一幕让她彻底崩溃。 1947年的春天,日本横滨港码头上挤满了归国的军人和平民。幸子抱着她那刚满周岁的孩子,站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单薄。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娘子军,如今面容憔悴,眼神空洞。 "一个饭团,就要这些钱吗?"幸子颤抖着从怀中掏出一叠军票,那是她在军中服役四年攒下的全部积蓄。摊主看了看那些钞票,摇了摇头。 "这些已经不值钱了,小姐。战败后,这些军票就成了废纸。" 摊主的话如同一记重锤砸在幸子心上。她呆立在原地,任凭人群从身边涌过,仿佛世界在一瞬间凝固。孩子在她怀中啼哭,但她似乎已经听不见了。 "所以...这十年...我的付出...都是为了一堆废纸?"幸子喃喃自语。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十年前,十七岁的她满怀热情地报名参军,坚信自己是在为大日本帝国的光荣未来而战。她曾在工厂日夜不停地生产武器,为出征的士兵欢呼,甚至在成为慰安妇后,也一直告诉自己这是为国家做贡献。 在被英军俘虏的那一年多里,她始终相信自己终将光荣归国。然而现实给了她无情的一击—不仅是那些军票一文不值,更是周围人看她的眼神。 "看那个女人,抱着个混血儿,肯定是慰安妇回来的。"一位路过的妇女对同伴低声说道,却足以让幸子听见。 她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向家乡所在的方向。然而,当她终于到达曾经的家门口时,却发现房子已经在轰炸中变成了一片废墟。邻居告诉她,父母在两年前的空袭中已经去世。 "你还是走吧,"一位曾经的邻居老太太说,"这里没人欢迎你这样的人回来。你那孩子会给村子带来不幸。" 幸子在家乡附近的一间简陋避难所里暂住下来。夜深人静时,她抚摸着熟睡的孩子,眼泪无声地滑落。曾经为国家奉献一切的自豪感,如今只剩下无尽的空洞和绝望。 "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她望着窗外的月光,回忆起当初参军时的情景。那时的她,多么年轻,多么热血,又是多么愚蠢地相信着那些爱国宣传。 在避难所的那个夜晚,幸子翻开了尘封已久的记忆。1937年初春,17岁的她和好友惠子站在征兵处外,手挽着手,脸上带着青春特有的坚定和憧憬。 "我们一定要参军!为天皇陛下尽忠!"惠子拉着幸子的手说道。学校里的老师常说,大日本帝国正在亚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女孩子们也应该为国家出一份力。 当时的日本,到处张贴着鼓舞人心的标语和海报。电影院里放映的新闻片中,士兵们英勇作战的画面引来观众阵阵欢呼。街头巷尾,人们欢送着出征的军队,将樱花和千纸鹤抛向军车。 "幸子,你要为家族争光啊!"父亲送她去训练营时,眼中闪烁着骄傲的泪光。那时的幸子不知道,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父母。 在东京的训练营里,幸子和惠子学习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和后勤技能。很快,她们被分配到一个军需工厂,日以继日地生产子弹和炮弹零件。工作虽然辛苦,但每当听说前线的胜利消息,工厂里的女工们就会欢呼庆祝。 "南京已经攻下了!我们的皇军真是无敌!"1937年12月,工厂主任带来这个消息时,所有女工放下手中的活计,欢呼鼓掌。幸子和其他女孩一样,为这场她们认为光荣的胜利而自豪。 没人告诉她们南京发生了什么。 1939年初,军队人手紧缺,幸子和惠子被调往前线,负责军队的洗衣做饭等后勤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军营里,她们是整个连队中仅有的两名女兵。 "能为前线将士服务,是最大的荣誉。"幸子常对惠子说。她们从未想过命运会在一天之内改变。 那是一个下午,营地里只留下几个放哨的士兵,大部队出去执行任务了。 "趁现在没人,我们去洗个澡吧。"惠子提议道。幸子同意了,两人带着脸盆回到营房,反锁了门。 她们刚脱下衣服,突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叫喊声。 "开门!快开门!"是队长的声音,男兵们提前归营了。 惊慌之下,幸子手忙脚乱地穿衣服,但已经来不及了。队长透过门缝看到了里面的情景,随即踹开了门。 那天晚上,幸子和惠子被拖到了慰安所。惠子在第一个月就因为不堪折磨而死去,留下幸子一个人在地狱中挣扎。 从那时起,幸子不再是娘子军,而是成了一个军中的"慰安工具"。她的身体属于国家,却连最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即便如此,军中宣传仍让她相信自己在为国家做贡献,为前线将士提供"精神支持"。 当战争进入1944年,日军局势日益恶化。幸子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按规定,她不能堕胎。石桥太郎帮她求情,但随行医生坚持让她生下孩子。 在缅甸丛林的溃败逃亡中,幸子抱着哭泣的婴儿,艰难地跟随着残兵败将。士兵们因为担心孩子哭声会引来敌军,曾几次要她抛弃孩子,但幸子始终拒绝。 1945年8月,幸子和其他幸存者被英军俘虏。在战俘营里,她第一次听说了日本投降的消息。 "天皇陛下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位日本军官低声告诉大家,"战争结束了。" 一片沉默中,幸子感到了一丝解脱。多年来第一次,她允许自己想象回家的场景。然而,等待她的将是更深的绝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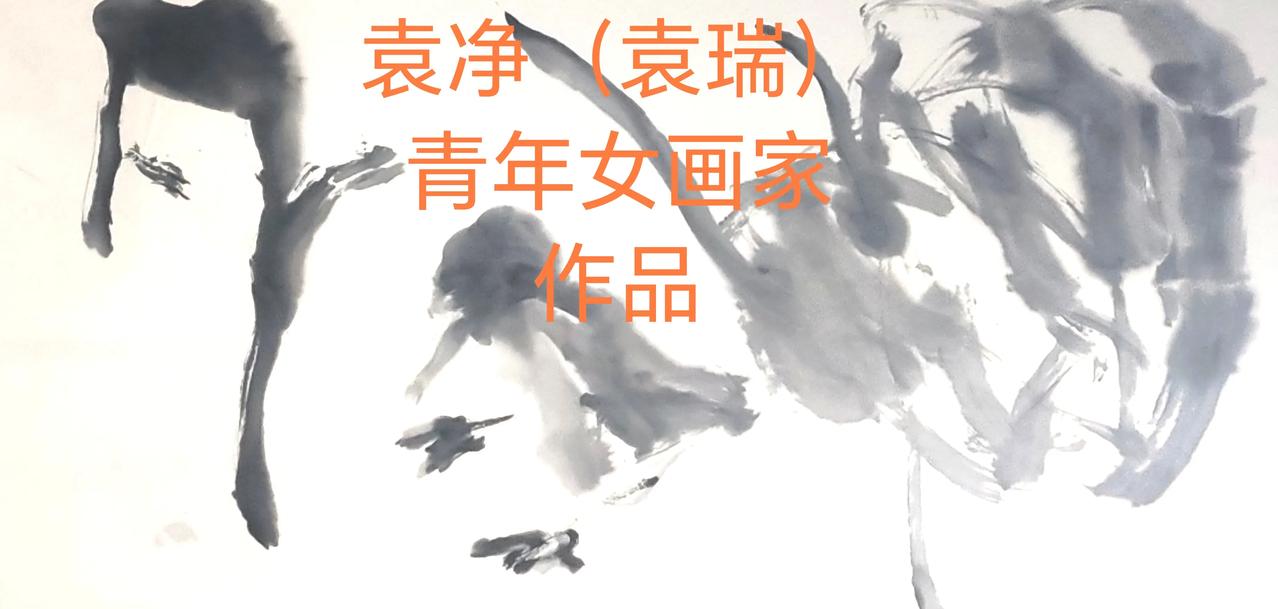
![@孟子义最新,悄然而至[比心]](http://image.uczzd.cn/427498249630188292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