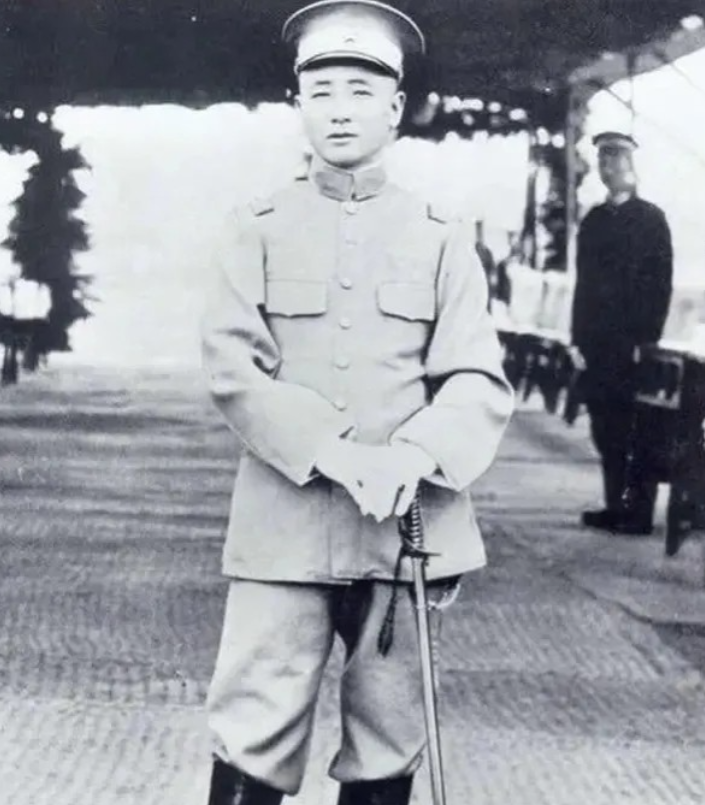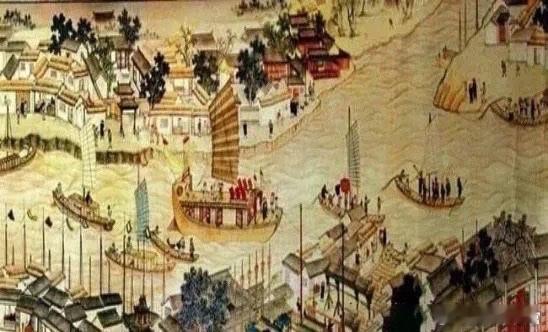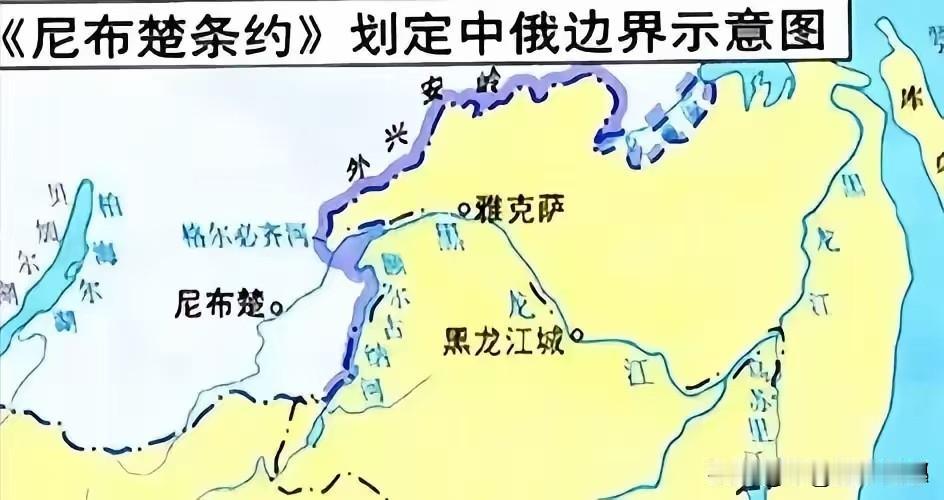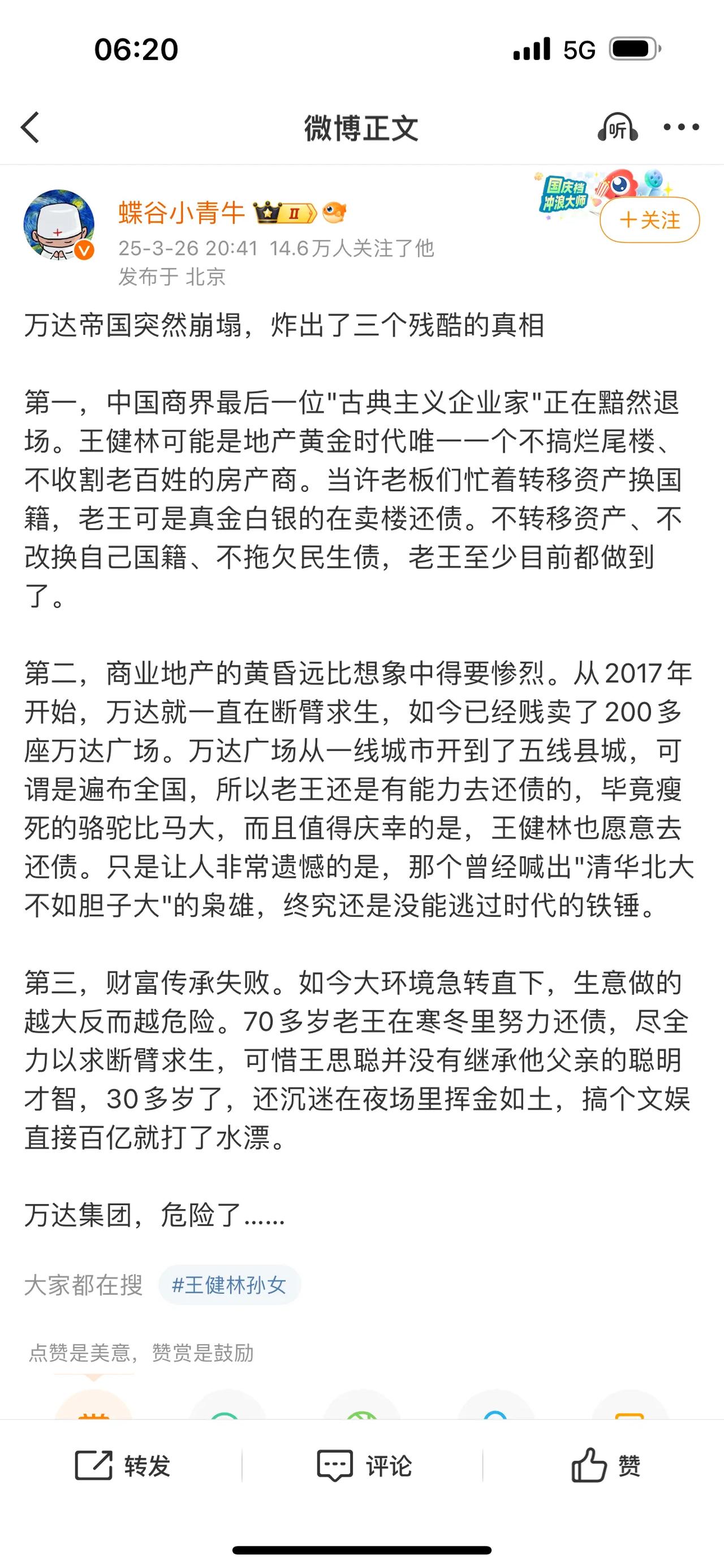1912年,张学良从乡下赶到奉天,怯生生叫了声“爹”,张作霖猛地回头道:滚!都给我滚!张学良吓得一个激灵,半晌才说:爹,娘病了,快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
1901年6月4日是张学良的生日,但1928年,这个日期对他而言变得尤为沉痛,因为他父亲张作霖在这一天被日本人所害,逝世的消息给他带来了深深的痛苦。为了将父亲的忌日与自己的生日区分开,张学良将自己的生日改为了6月3日。他曾说,“在父亲丧日庆祝我的生日,我笑不起来。”
张学良曾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提到,自己8岁时,父亲张作霖拼尽全力为他谋得了一个五品官职,他感叹道:“他是个好父亲。”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对父亲张作霖的评价非常高。每次回忆父亲时,他常常说:“我聪明,我父亲比我还聪明,他比我厉害。”在他流亡到美国后,每当有亲友探望,他总会不由自主地提到:“我想回东北,我想我爸!”这无疑表明了他对父亲深厚的感情。
然而,少有人知,张学良在少年时期与父亲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实际上,在他年轻时,他甚至曾一度想过要杀死父亲。父子之间的矛盾,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其中,张学良的母亲赵春桂在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张作霖和赵春桂的婚姻并不和谐,父子之间的裂痕,也与母亲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作霖作为一个有着雄心壮志的军事人物,性格严厉,时常通过高压手段教育儿子,甚至在某些时刻,张学良感到自己完全被父亲压制,无法自由呼吸。张学良对于母亲的过度溺爱与保护,对父亲的高压管理产生了强烈反感,这也加剧了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奉天城内一片萧瑟。张学良匆匆赶到父亲的大院,脚步虽快,却显得犹豫不决。他在门前踌躇了片刻,才鼓起勇气迈进了院门。看到正在处理公务的父亲张作霖,他轻声唤了一声"爹"。张作霖闻声猛地转身,不等儿子说完:滚!都给我滚!张学良吓得一个激灵,半晌才说:爹,娘病了,快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
张作霖只是淡淡地扫了儿子一眼,眉头微皱,似乎对这个消息并不在意。他认为这不过是赵春桂又在和他赌气罢了。挥了挥手,他让张学良回去,言语间满是不耐烦。年轻的张学良含着泪水,转身离开了这座威严的大院。
在回去的路上,张学良骑着马,思绪却回到了几天前。母亲赵春桂卧病在床时的场景历历在目。那时的母亲已经很虚弱了,躺在新民老家的炕上,脸色苍白如纸。她一直在咳嗽,却还在安慰着焦急的儿子。赵春桂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她从未在儿子面前表露出对丈夫的怨恨。
当年在辽西,父亲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正是母亲不顾家人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父亲。在父亲组建保险队的艰难岁月里,母亲不但操持家务,还常常规劝父亲要多行善事。母亲的贤惠温柔,为父亲赢得了不少乡邻的好感和支持。
自从父亲在奉天站稳脚跟后,家中陆续添了几位姨太太。母亲从未抱怨什么,只是在一个雨天,悄悄搬回了新民老家。张学良记得,母亲搬家那天,只带走了几件衣物和一些日常用品,甚至连陪嫁的首饰都未取走。
在张作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赵春桂走入了他的生活,但当张作霖逐渐强大时,她却感受到了冷落。张作霖有过六位妻子,而赵春桂是其中最为普通的一位。她不仅长相普通,而且还患有斜眼病。婚后不久,张作霖便迎娶了第二位妻子卢夫人。赵春桂内心不悦,但她宽容大度,亲自主持了这场婚事。
令她惊讶的是,卢夫人与她关系十分亲密,几乎如姐妹一。然而,随着张作霖的升迁,他迎娶的妻妾逐渐增多,这使得赵春桂无法继续容忍。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争吵不断。最终,赵春桂一气之下回到了老家辽西,带着她与张作霖所生的三个孩子——首芳、学良和学铭,开始了独立生活。
在新民的家中,日子越来越拮据,赵春桂并没有亲自去找张作霖。她不愿意见到丈夫,便派了儿子张学良去向父亲要生活费。张学良那时从未去过奉天,甚至连奉天是个什么地方都不了解。他乘坐着拉粪车前往奉天,甚至没有换上正式衣物,因为他认为见父亲不需要讲究这些。
可当他到了张作霖的住处时,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进入大门。门卫把他当作乞丐,甚至用刺刀将他的狗皮帽挑飞。张学良那一刻深感羞辱,愤怒与委屈让他泪流满面,心中对父亲的怨恨也愈加深刻。
1912年,东北的局势并不平稳,赵春桂担心儿子的前途受到影响。一天,她将10岁的张学良叫到身边,给他塞了一些钱,缝在衣服里,并叮嘱他:“如果今晚有事,赶紧跑,去找一个老人,告诉他你是谁的儿子,把钱交给他,让他帮你去。”
她没有提及丈夫张作霖的名字,只称“他”。这一次,张学良从新民县出发,冒险来到了奉天,进入了帅府。张作霖随后为张学良安排了众多的老师,教授他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甚至为他请了专门的英文老师来学习英语。
他不喜欢父亲给他规划的生活,并处处与父亲作对。在周大文的介绍下,张学良接触到基督教青年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渐爱上了网球、高尔夫球,甚至学会了开飞机。张学良回忆时曾说:“受西方教师和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的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