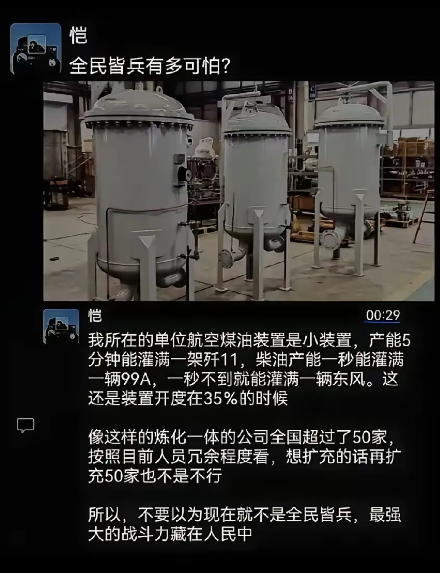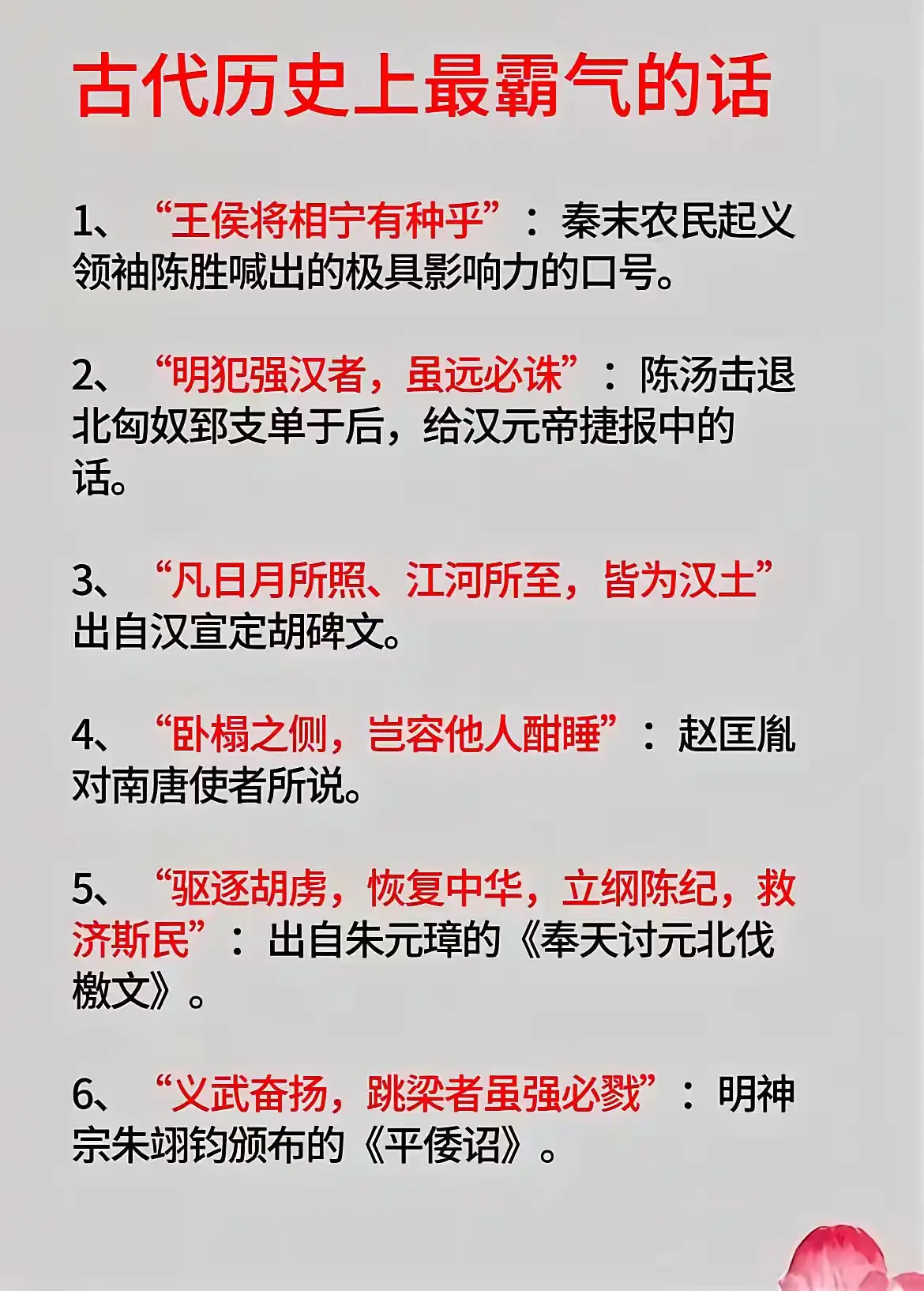1901年,闻一多和高孝贞订婚。到新婚夜,高孝贞让闻一多睡地上,闻一多没好气问:“难道你不打算行周公之礼?”高孝贞说:“您不当我是妻子,我何必让你做夫君呢?”闻一多反问说:“如果我用强呢?”
抗战胜利后,孙毓棠在闻一多的推荐下准备前往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皇后学院的客座研究员。闻一多在给孙毓棠的临别赠言中写道:“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必国家有光荣,个人方能有光荣。”
这句赠言不仅表达了他对孙毓棠的深切祝愿,也反映了闻一多个人的人生选择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一直认为,只有国家强盛,个人才有光荣与尊严。这种理念深深影响了闻一多的一生,使得他始终将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连。
闻一多从少年时期便表现出了非凡的学习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他在家中的书房里认真读书,其他孩子看到花轿或龙灯等热闹场面,都会跑去张望,而他却总能专心致志地埋头读书。白天,他在家塾学习,晚上还随父亲一同阅读《汉书》,这段基础教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和人生志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闻一多前往美国留学。在美国期间,他成绩优异,但时常感到无奈。他看到许多中国学子在外国遭遇的屈辱和歧视,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深切关怀。怀着这份赤子之心,1925年,年仅26岁的闻一多写下了《七子之歌》,这首诗表露了他对祖国的深情,并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感。
写完诗后,闻一多没有选择继续在国外深造,而是决定带着满腔热血返回祖国,他认为,只有让更多中国人读书,国家才能变得强大。闻一多深信,作为一位诗人,最重要的天赋是爱,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这份情感贯穿了他的一生。回国后,他致力于教育和文化事业,他以身作则,提倡学习和自我提升,鼓励青年学子投身于国家的建设中。
1901年的冬夜,湖北浠水县一户人家的新房里,散发着喜庆的红烛光芒。这是闻一多和高孝贞的新婚之夜,但房间里的气氛却与传统的洞房花烛夜大不相同。新房内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与沉默。
红色的喜被整整齐齐地铺在床上,而地上则随意地丢着一个枕头。这个场景让人不禁疑惑:为什么新婚之夜,会有人需要睡在地上?原来,这个枕头是新娘高孝贞特意为新郎闻一多准备的。在这个本该甜蜜的夜晚,她却要求丈夫睡在地上,这种出人意料的举动打破了传统婚礼的所有常规。
当时的闻一多,年仅十三岁,正值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录取后的准备期。而高孝贞作为他的表妹,虽然年龄相仿,却展现出远超年龄的果断与决绝。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安排,闻一多显得既困惑又无奈。他试图与新娘理论,询问她是否准备履行新婚夫妻的义务。
高孝贞的回应更是让人意外。她并没有像传统女子那样顺从,而是直截了当地表示:既然闻一多不愿意真心接纳她这个妻子,她也没有义务履行妻子的职责。即便闻一多暗示可能会采取强制手段,高孝贞也只是报以不屑的冷笑,径直躺在床上安然入睡。
这样的场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显得格外特别。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包办婚姻仍是主流,新娘子通常都是温顺听话的。但高孝贞打破了这一传统形象,她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这门并非两情相悦的婚姻。
1923年,梁实秋向闻一多寄去了十二张风景照片,并附带了一封信:“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那时,闻一多在芝加哥学习绘画,而梁实秋则在美国的科泉留学。梁实秋的初衷不过是想逗弄一下闻一多,给他一个机会去羡慕自己。但出乎意料的是,闻一多没有多说什么,提着箱子便来到了科泉,成为美术系唯一的中国人。
在那里,闻一多将自己过得像一位真正的画家。曾有他的系主任评价说:“他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固然优秀,而他这个人本身也就是一件艺术品。”从他脸上的纹路到嘴角的笑容,都散发着极为完美的节奏感。他总是扎着黑领结,披着长发,尽管因为长期绘画,衣服上常常沾满了颜料,显得非常脏乱。
他节俭度日,自己做饭,偶尔炒点木犀肉充饥。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他消沉,反而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在回到祖国后,闻一多在清华大学任教,深知国家的未来依赖于教育和文化的振兴。他为此制定了庞大的学术计划,涵盖了从《毛诗》到《全唐诗》的众多经典。他的这五年可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安定和充实的一段时期。
然而,时局却并不安宁。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不幸遇刺身亡,震惊了期盼和平的中国人民。闻一多作为李公朴的挚友,毫不犹豫地站上了讲台,面对着可能的特务监视,他依然用愤怒的语气质问:“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的演讲掷地有声,数次因为掌声中断,显现了他为国家、为民众所做出的坚守与担当。
1944年,经济困难时期,闻一多通过书法、刻章等手工劳动维持生计。尽管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教育的热爱。家中经济状况困窘时,他的孩子们曾因一次化学实验发生小事故而受到惊吓,然而他并没有责备他们,而是通过这次事件教育孩子们“一知半解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