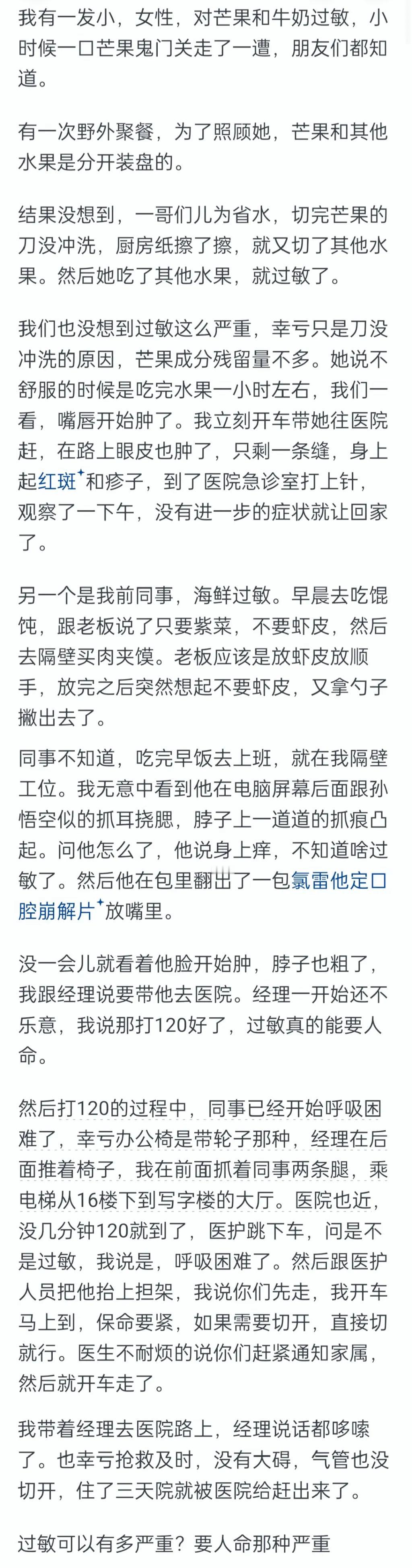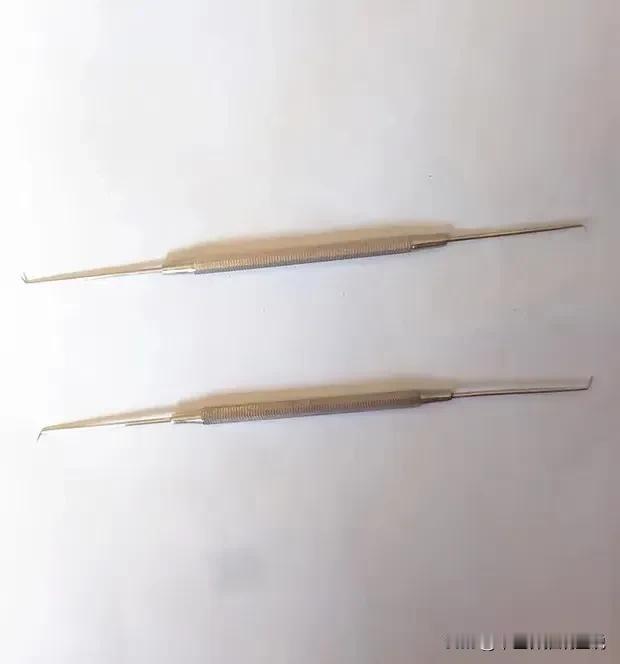1972年,医学博士陈菊梅:“请帮我摘掉扁桃体、割掉阑尾,再拔光牙齿!”医生愣住“你不要命了?陈菊梅淡淡地说道:“我已经没有了命,我的命早已交给了医学。”
这是陈菊梅几十年如一日的拼搏,和她对医学事业的执着。
在她的内心,身体早已不再是重要的东西,她将一切付诸于自己的事业——研究,治病救人,甚至是挽救更多的生命。
陈菊梅出生于浙江省普通家庭,好学的她,在高中的时候便立下志愿,要做一名医生,成为解救他人生命的英雄。
那时她对医学的理解,还非常单纯,只是觉得治疗病痛、拯救生命是自己一生的使命。
陈菊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医学院,顺利完成学业,被选派到苏联留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生活艰辛,陈菊梅依然刻苦钻研,不断参与各类医学研究项目。
苏联的日子里,她除了攻读专业知识,还时常亲自下到病房,向病人们学习,如何做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1960年,陈菊梅回国,回到北京的解放军302医院,开始从事传染病的研究。
她致力于传染病的研究,经过几年的努力,渐渐在医学界崭露头角。
论文被国际医学期刊发表,医学界的专家们,纷纷称赞她的能力,成了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医学人才之一。 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让她的身体开始出现了问题。
陈菊梅每天都在加班,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医院的工作十分繁忙,肝炎病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她和同事们彻夜工作,日以继夜地研究病毒、分析数据。
时间久了,陈菊梅感到身体每况愈下,开始出现慢性疲劳、头晕等症状。
起初她没有在意,只是觉得工作压力大,休息几天就能恢复。
可渐渐地,陈菊梅出现了严重的血尿,身体的虚弱,让她不得不去医院检查。
医生告诉她,病情已经出现了恶化的迹象,病情的严重性让陈菊梅感到深深的焦虑,自己不再是年轻时,那个可以拼命工作的医学博士,身体出现了无法忽视的警告。
陈菊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想要通过清除自己体内,可能引发炎症的器官,来减轻对身体的负担。
她找到了医院的外科医生,平静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包括她的牙齿,她的扁桃体,阑尾。
医生愣住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你不要命了吗?”年轻医生忍不住问道。
她淡淡地笑了笑,说:“我已经没有命了。我的生命已经交给了医学。扁桃体、阑尾这些小小的器官,不会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我的目标是为医学研究而活,为了科研,清除身体上的负担。”
这个决定,让在场的医生,感到震惊不已。
常人的理解中,扁桃体和阑尾是“废弃”的器官,也未必意味着它们不重要。
拔光牙齿,更是超出了常理,很多人不理解,甚至觉得陈菊梅,简直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陈菊梅不觉得这些器官,对自己的健康构成威胁,认为自己更需要以健康的身体,去继续从事科研工作。
如果她不及时“清理”自己的身体,未来的工作和研究,都可能受到影响。
手术之后,陈菊梅继续投入到传染病的研究中,开展了大量的临床试验。
通过对肝炎患者的长期观察,她发现,某种安眠药中的五味子成分,能够显著降低肝功能指标——转氨酶。
陈菊梅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还为世界医学界,贡献了巨大的价值。
此后的岁月里,陈菊梅继续带领团队,为国内外数以万计的患者,带去了希望。
也未停止过对自己的身体清理,依旧保持着自己一贯的严苛态度。
直到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陈菊梅已年过七十,她投入到一线工作,和同事们一道,编写了《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
年事已高,仍然亲自为患者进行治疗,不畏病毒的威胁,日日守在病房里。
她是那场危机中的坚守者和无畏者,全力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晚年陈菊梅没有放松对医学的研究,她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医学人才,亲自进行指导。
直至91岁,她依然坚持在医疗岗位上,继续治病救人。
她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了首都医科大学,作为医学研究的基础,在她的心里,死亡不可怕,真正值得害怕的是,停止前进的脚步。
她用一生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使面对疾病、困境、挑战,只有对信念不变,对医学不舍,才是真正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