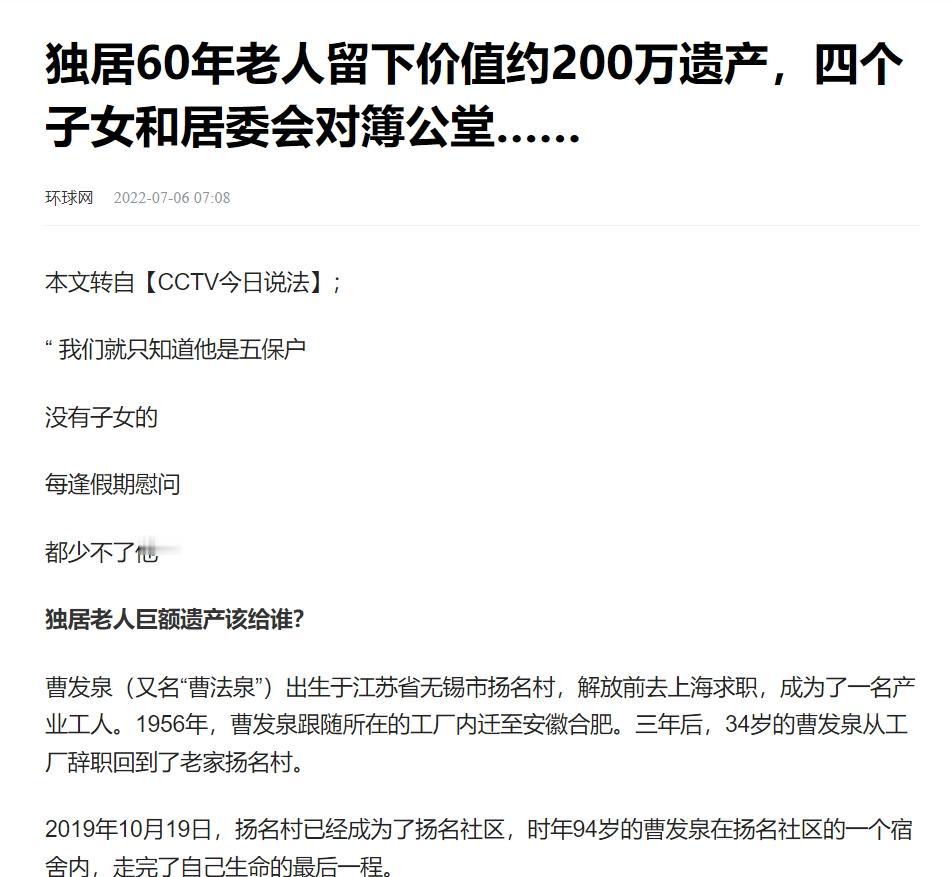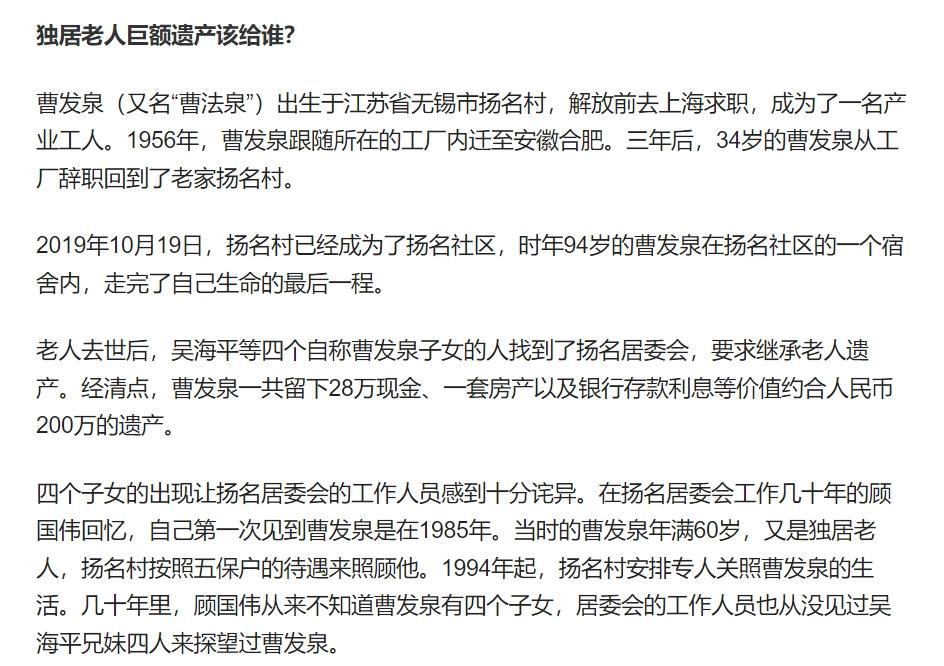94岁老人去世,将230万遗产留给居委会,这天,老人的四个子女突然找上门来,他们要求继承老人的遗产,却遭到了居委会的拒绝,居委会说:“老人独居60年,从没看到儿女养过老人一天。” 2019年初的一天,无锡市某社区居委会迎来了一群不速之客。四个面容憔悴的中年人站在办公室门口,自称是刚刚去世的曹法泉老人的子女。他们此行的目的很明确:要求继承父亲留下的遗产。 这套位于城区的120平米住房,加上30万元存款,总价值约230万元的遗产,成为了这场纷争的焦点。居委会工作人员面对四人的要求,态度异常坚决。"曹老伯独自一人在这里生活了60年,从未见过任何子女来看望。现在人已经走了,你们却来要遗产,这恐怕说不过去。" 面对居委会的拒绝,老人的二儿子吴海平激动地提出了几点质疑。首先,老人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收入,足以维持基本生活;其次,分给老人的新房一直空置,居委会并未安排老人入住;再者,所谓的日常照料,不过是安装了一个监控,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都要老人自己打理;最后,在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居委会将其送入养老院,不到一周就离世了。 这些质疑声此起彼伏,使得原本平静的居委会办公室陷入了一片混乱。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搬出了当年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这份在2003年签署的法律文书清晰地记载着:居委会承担照顾老人的责任,而老人则将遗产留给居委会。 然而,这份协议并未能平息争议。四姐弟坚持认为,作为曹法泉的亲生子女,继承遗产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甚至采取了一些过激行为。无奈之下,居委会只能将此事诉诸法院。 在随后的法律程序中,居委会请来了两位关键证人。一位是老人的堂侄女曹建华,她详细讲述了这些年来居委会对老人的照顾:从日常生活用品的供应,到冬季御寒物品的准备,事无巨细。另一位证人是老人的同事兼好友蒋士铭,他道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当年老人的简易房拆迁时,能够置换的面积仅有24平米,是居委会额外出资,才使得老人获得了这套120平米的住房。 这场遗产纷争,表面上是一起普通的继承权争议,实则折射出现代社会养老问题的复杂性。在法律框架下,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高于法定继承权,这是保护尽到赡养义务一方权益的重要法律保障。然而,在亲情面前,法律的冰冷条文似乎总显得苍白无力。 纷争仍在持续,但对于已经离世的曹法泉老人来说,这场争端早已无法触及。那套承载着他晚年生活的房子,和他积攒的些许存款,成为了一个关于亲情、道德与法律的复杂难题。 要理解这场遗产纷争的来龙去脉,需要回溯到六十年前。那时的曹法泉,还是一个充满闯劲的年轻人。34岁之前,他在安徽某地打拼,与当地女子吴阿多结为夫妻,并育有四个子女。生活本该就此安定,却因为对未来道路的分歧,夫妻二人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曹法泉不愿继续工厂的工作,执意要回无锡老家生活。而吴阿多则坚持留在安徽,最终两人分道扬镳。离婚后,吴阿多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人,而曹法泉则独自返回了家乡。回到无锡后,曹法泉在村里搭建了一间简易平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独居生活。他日出而作,靠种地种菜维持生计,过着清贫但规律的生活。在那些年里,村里人很少见到有亲戚来访。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田逐渐消失,曹法泉失去了耕种的机会。居委会看到这位老人的困境,便安排他在社区环卫站工作。在环卫站里,曹法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同事们的敬重。退休后,他每月能领到固定的退休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2003年是曹法泉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他居住多年的简易房面临拆迁,78岁的他本该享受天伦之乐,却仍是形单影只。居委会多方联系其亲属,但均未能得到积极回应。最终,在老人弟弟的协调下,居委会与曹法泉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 协议签订后,居委会安排专人照料老人的起居生活。每逢节假日,社区工作人员会带着慰问品登门看望。老人生病时,社区都会及时送医就诊,医疗费用也由社区承担。这种照料一直持续到老人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曾经有过一次令人唏嘘的偶遇。一天,在环卫站附近,一位来自上海的年轻人驻足观望,那是吴海平的儿子。然而,或许是顾虑太多,这次相认的机会最终还是错过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考虑到需要专业的护理,居委会不得不将其送往养老院。然而天不假年,曹法泉老人在入住养老院不到一周后便离世了。 这起遗产纷争最终被诉至法庭。法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认定遗赠抚养协议效力优先于法定继承。一审判决支持了居委会的诉求,即便吴海平四姐弟提起上诉,二审法院仍维持了原判。这个案例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养老问题的深思。在法律层面,遗赠抚养协议是对实际付出赡养义务一方的保护;而在道德层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则是任何遗产都无法填补的。 生前未尽赡养义务,死后争夺遗产的行为,既不合情理,也难获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