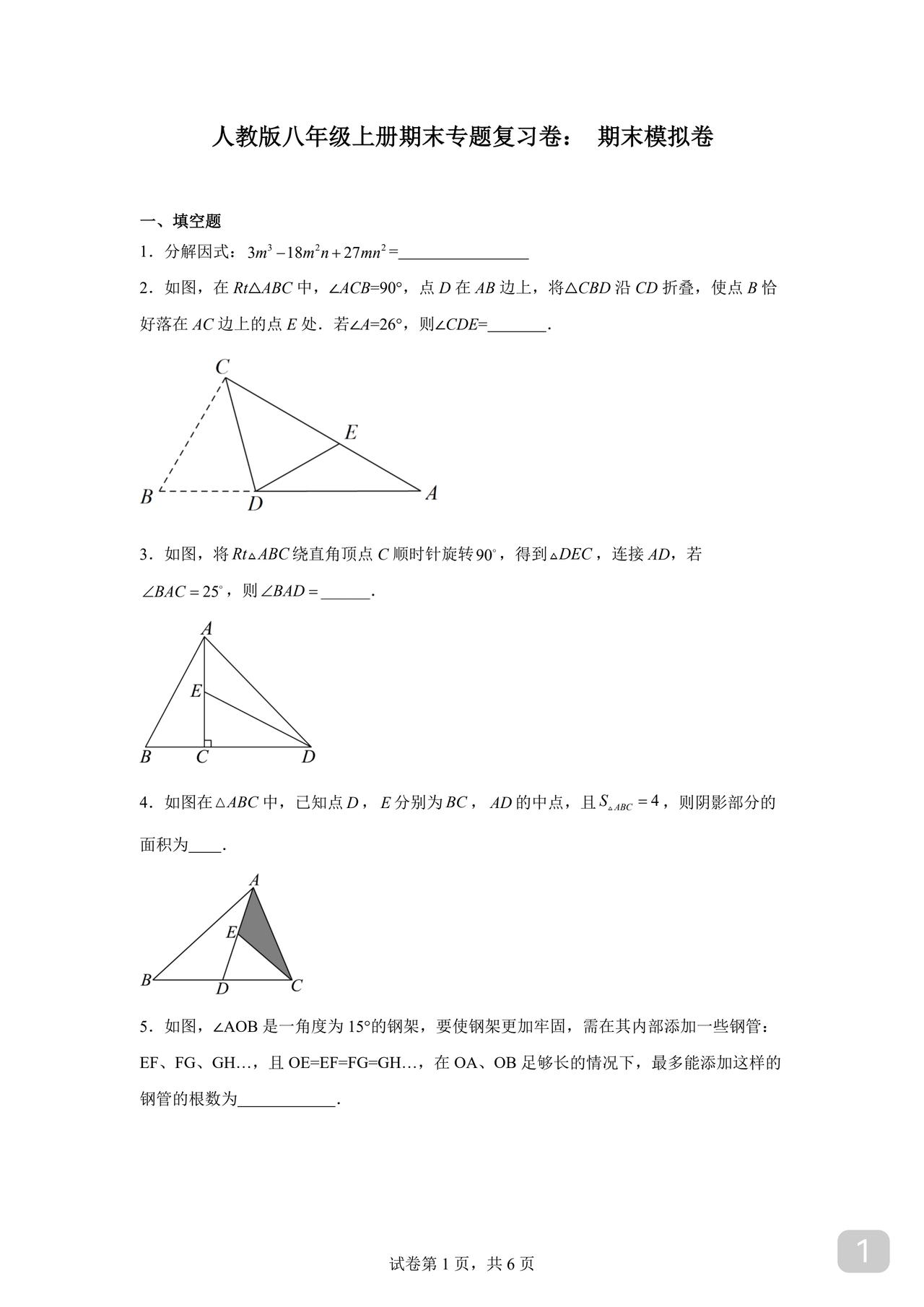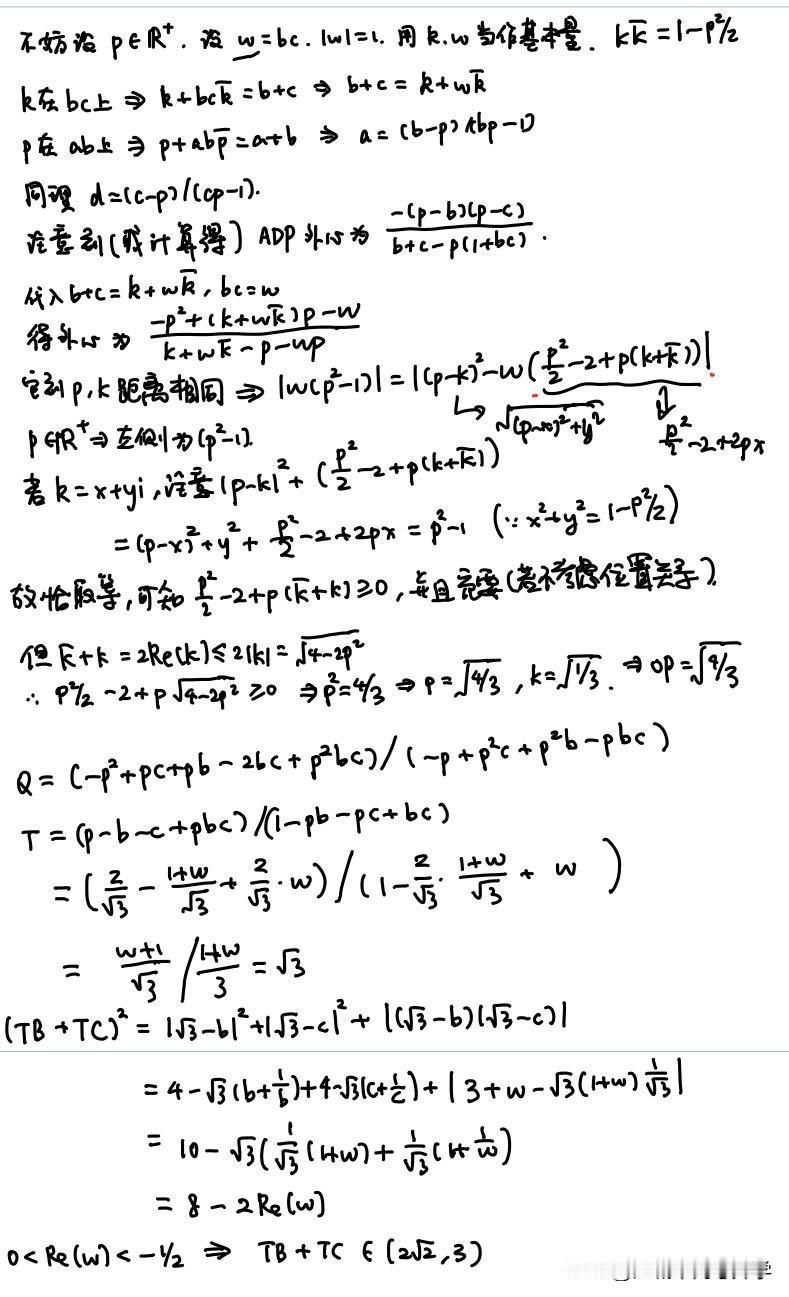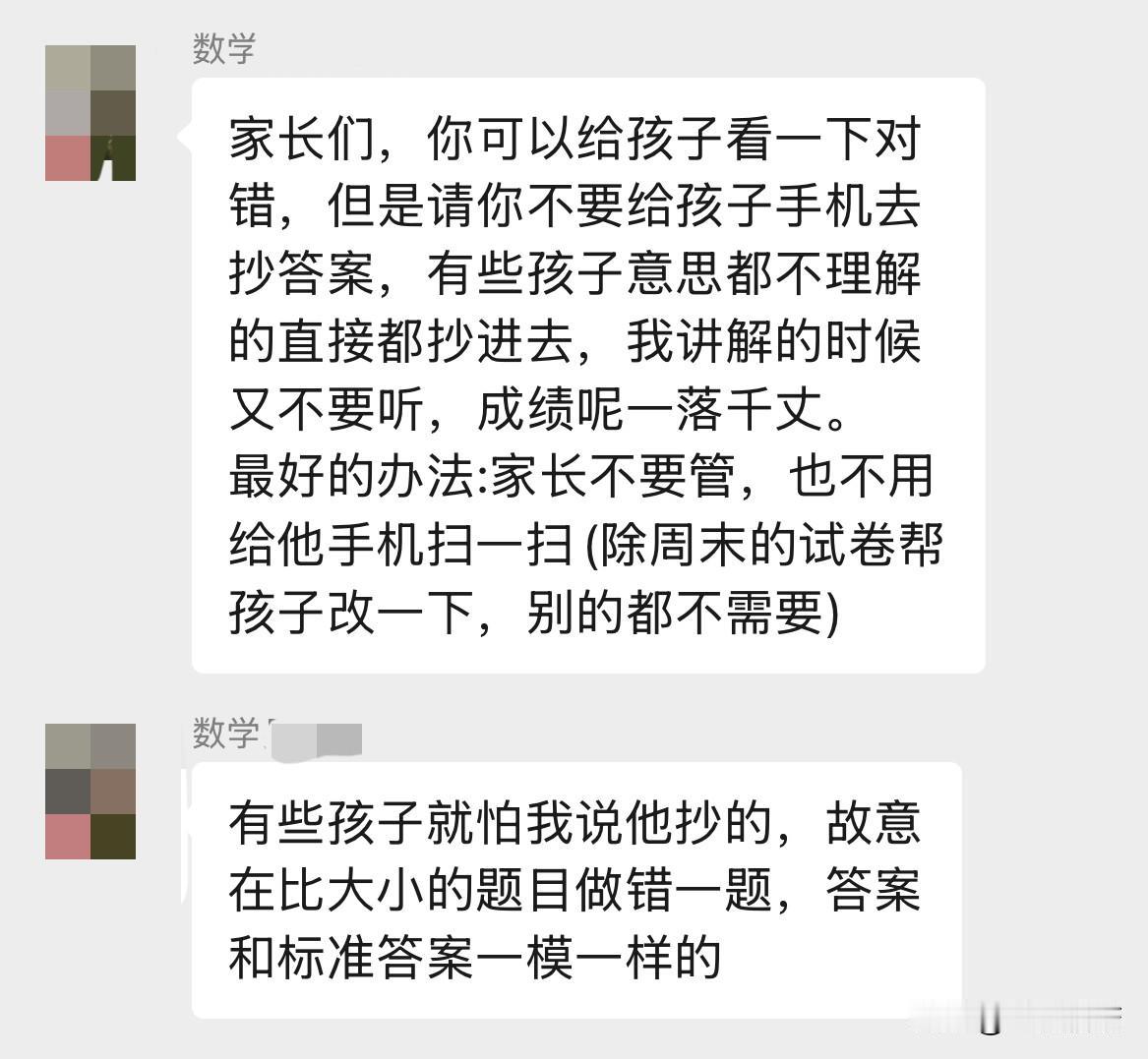在数学世界里,存在着一个迷人的“三角关系”:离散、连续与概率。它们看似毫不相干,但却在最底层的逻辑中相互交织,共同构筑了我们从理解“微观量子”到驾驭“宏观智能”的数学基石。
最惊艳的例证,就藏在“量子力学”中:世界的本质是“离散”的(能量量子化),但描述它的波函数 ψ(x) 却是一个“连续”的数学形式,而“概率” |ψ(x)|² 则成为了连接二者的桥梁。

要追溯这段关系的起源,我们需要回到17世纪,见证“离散”与“连续”两大数学支柱的诞生。
1679年,莱布尼茨发明了二进制,说起“二进制”,我们会不由得想起我们的老祖宗以“阴阳学说”为基础而创立的《易经》。
1689年,莱布尼茨在游历意大利时,结识了曾经到过中国的传教士,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法国汉学大师布韦向莱布尼茨介绍了《易经》和八卦的系统。在莱布尼茨看来,“阴”与“阳”几乎就是他的“二进制”的中国版。
由此可知,莱布尼茨独立发明了二进制,但后来发现《易经》六十四卦与其系统吻合,并由此受到哲学启发,进一步推崇二进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

在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二进制”,发现它已成为了“离散数学”中最重要的实践工具与思想载体。
同时,我们也发现,“离散”与“连续”,也构成了现代数学的两大重要的分支。
在“离散”这个分支里,伽罗瓦与阿贝尔所创立的“群论”,是一个不灭的经典。
而在“连续”这个分支里,牛顿和莱布尼茨所创建的微积分,点燃了近代人类文明300年来的夜空。
一个研究“离散”,一个研究“连续”,虽然分属于数学的两个不同分支,但它们在现代数学的深处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微积分用于研究“变化”,核心是变化率(导数) 和累计(积分)。它处理的是函数、极限、连续性和光滑性。
群论用于研究“对称性”,研究几何图形、方程、物理定律等在某种“变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

当我们开始研究具有“对称性”的“变化对象”时,它们有趣而深刻的联系就开始了。
群论的“对称性”可以用来简化微积分问题,这是群论在微积分中最直接、最强大的应用。如果一个数学或物理问题具有某种“对称性”,那么利用群论可以极大地简化计算。
“群论”如此重要,但是其创立的过程,却极为坎坷。
伽罗瓦与阿贝尔并称为“现代群论”的创始人,这两位出生于不同国家的绝世少年天才,坎坷的经历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群论为何物时,两位天才少年正在试图用另一种方法证明一元五次方程没有根式解,这所谓的“另一方法”最终演绎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成为了现代数学重要分支的“群论”。

可惜的是,阿贝尔和伽罗瓦的工作成果在生前都没有得到认可。
伽罗瓦三次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代数方程论文。
第一次是1829年,伽罗瓦将他在“代数方程解”的结果呈交给法国科学院,由柯西负责审阅,柯西却将文章连同摘要都弄丢了。
第二次是伽罗瓦进入高等师范学院就读,次年他再次将方程式论的结果,写成三篇论文递交到法国科学院。
但是当论文送到傅里叶手中后,傅里叶不久便去世,使得伽瓦的数学论文再次被埋没。

第三次递交的论文则由泊松审阅,泊松作为当时分析数学和数学物理领域的权威,但他的专长并不在伽罗瓦所探索的这个全新领域。
1831年,泊松给出了最终的评审报告,其核心内容是:“我们已经尽力去理解伽罗瓦的证明……他的论证既不够清晰,也远远不够充分,我们无法判断其正确性。……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无法推荐这篇论文被科学院采纳。”
伽罗瓦一直在等待着论文被采纳的好消息,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有等到。
1832年5月31日,年仅20岁的伽罗瓦因参一场决斗去世,他的朋友舍瓦烈遵照伽罗瓦的遗愿,将他的数学论文寄给高斯与雅可比,但是都石沉大海。
最终,这些手稿辗转到了刘维尔手中,与泊松的“无法理解”不同,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些手稿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宏大且未知的数学体系。

刘维尔花费了数月时间,潜心研读这些杂乱、不完整的手稿。
在决定发表伽罗瓦的著作时,刘维尔亲自为其撰写了长篇的导言。在这篇导言中,他不仅介绍了伽罗瓦的生平悲剧,更重要的是,他向数学界解释了伽罗瓦工作的核心思想、重要性和基本框架。
1843年,刘维尔向法国科学院宣布他发现了伽罗瓦工作的重要价值。随后,他在自己主编的、极具影响力的 《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 上,于1846年正式发表了伽罗瓦的主要论文。
如果没有刘维尔,伽罗瓦的工作成果,也许永远地埋没在了历史的尘法之中。
正如后世评价:‘伽罗瓦创造了理论,而刘维尔则将它献给了世界。

无独有偶,与伽罗瓦处于不同时空且因解决一元五次方程是否有根式解而意外创建的“群论”的阿贝尔,也有着同样令人扼腕的经历
1824年,阿贝尔完成了《一元五次方程没有代数一般解》的论文。
他把论文寄了给当时有名的数学家高斯,也同样石沉大海。
1824年,阿贝尔完成了《一元五次方程没有代数一般解》的论文。
他把论文寄了给当时有名的数学家高斯,也同样石沉大海。
1825-26年的冬季,他远赴柏林,认识了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克列尔,克列尔是一个同样热爱数学的土木工程师。
1826年,克列尔创立了一份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杂志,在第一期刊登了阿贝尔所取得的关于五次方程的工作成果。
1826年夏天,他在巴黎造访了当时最顶尖的数学家,却倍受冷落。科学院秘书傅立叶仅仅读了论文的引言,然后委托勒让德和柯西负责审查。遗憾的是,柯西把稿件带回家后却弄丢了。

他失望地离开了巴黎,不久不幸染上了肺结核病。
1829年4月8日,克列尔写信告诉阿贝尔,已经成功地为他争取到了柏林大学数学教授职位。
可惜这一切已经来得太迟,一代年轻的数学天才于两天前的凌晨去世了,年仅26岁。
两位天才少年虽然离我们而去,但是他们所创立的“群论”,成为了人们理解“离散数学”的基石。他们的工作成果,也构成了今天的现代数学中的“离散”、“连续”、“概率”的铁三角。
那么,“概率”在这场“离散”与“连续”的宏大叙事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有趣的抛硬币的游戏开始说起。

当我们每抛一次硬币,落地后的结果都将是一个“离散”的二元事件:正面或反面。但当我们连续抛掷成千上万次,并记录正面朝上的次数时,一个神奇的现象发生了:这个离散的分布(二项分布)图形,其形状会越来越接近一条光滑的、连续的钟形曲线(正态分布)。
这就是概率论中著名的“中心极限定理”的核心思想:大量独立的、微小的“离散随机变量”,其总和的分布会趋向于一个“连续的正态分布”。
概率在这里施展了它的“平滑”魔法,将一颗颗“离散”的“沙粒”(单个随机结果),堆砌成了“连续”柔和的“沙丘”(整体分布规律)。
反过来,当我们需要研究连续对象(如一个粒子的位置、一段声音信号的强度)中的随机性时,概率也提供了完美的工具。

对于一个在空间中“连续运动”的粒子,问“它恰好出现在某个精确的点上”的概率是多少,在数学上是没有意义的(概率为零)。于是,我们引入了“概率密度函数”。
这个函数本身是“连续”的,但它所描述的是该粒子出现在某个区间(一个连续的“段”)内的“概率”。我们通过对这个“连续函数”进行积分(微积分的核心工具),来计算出离散的概率值。
在这里,概率再次将“连续”的数学形式与“离散”的测量结果联系了起来。
最终,“概率”论将“离散”和连“续统”一在了一个更宏大的框架下——“随机过程”。
无论是描述网站访问量的“离散模型”(泊松过程),还是刻画股票价格波动的“连续模型”(几何布朗运动),抑或是兼具“离散”与“连续”特性的物理现象(如我们开头提到的量子力学),都可以被囊括在“随机过程”的理论中。

在现代数学的视角下,“离散”与“连续”的界限变得模糊,而“概率”成为了一个核心的“统一概念”并构成了一个深刻的三角关系。
“分析学”认为,“离散”可以通过“极限”和“逼近”走向“连续”。
“代数与组合学”认为,“连续”可以通过“生成”和“解析”照亮“离散”。
而“概率”提供了统一的、严格的数学基础,揭示了它们在更深层次上的一致性。
当我们理解了这三者的关系,也就理解了现代数学中所描绘的既“确定”又“随机”、既由“基本单元”构成又呈现出“连续流形”的复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