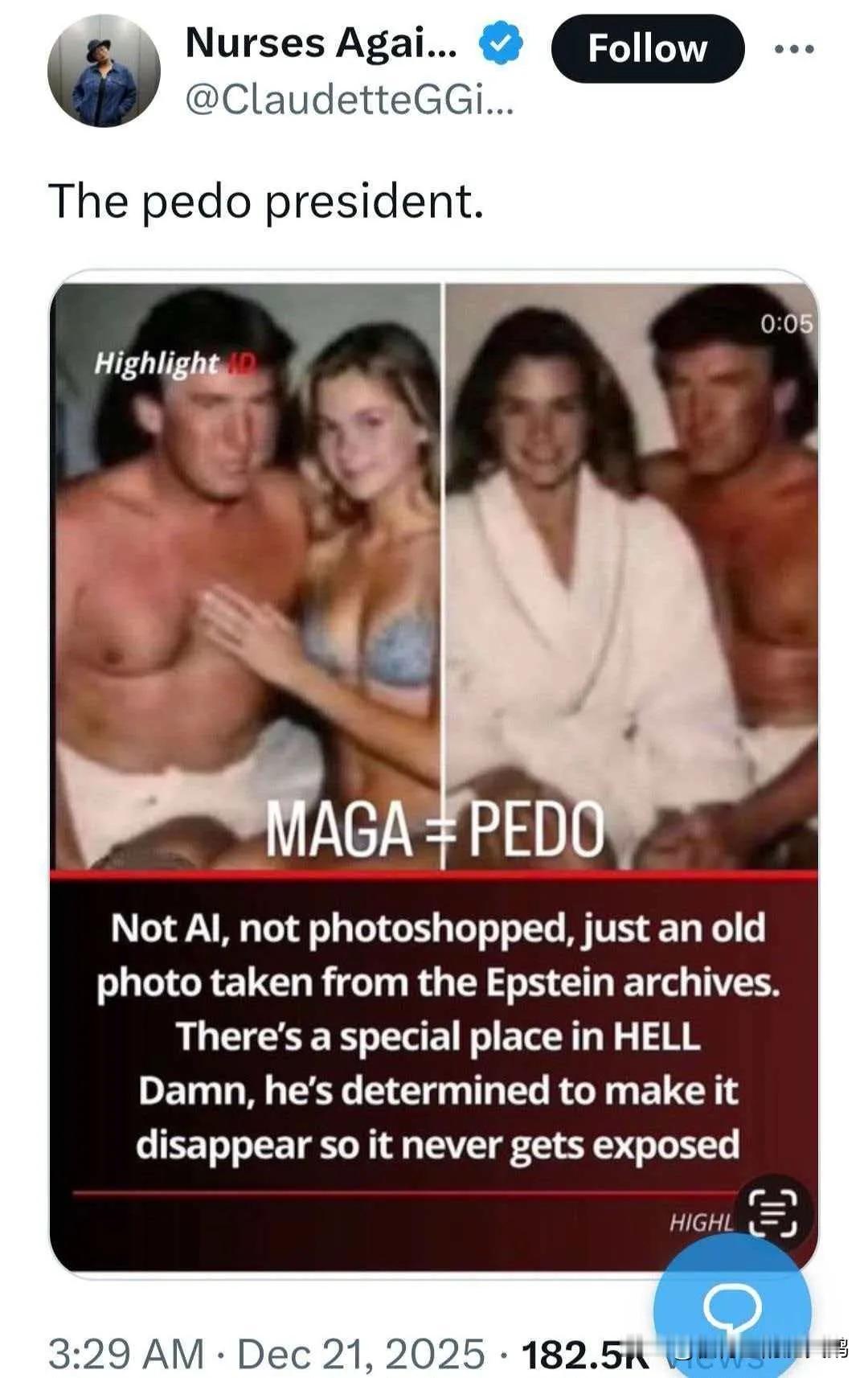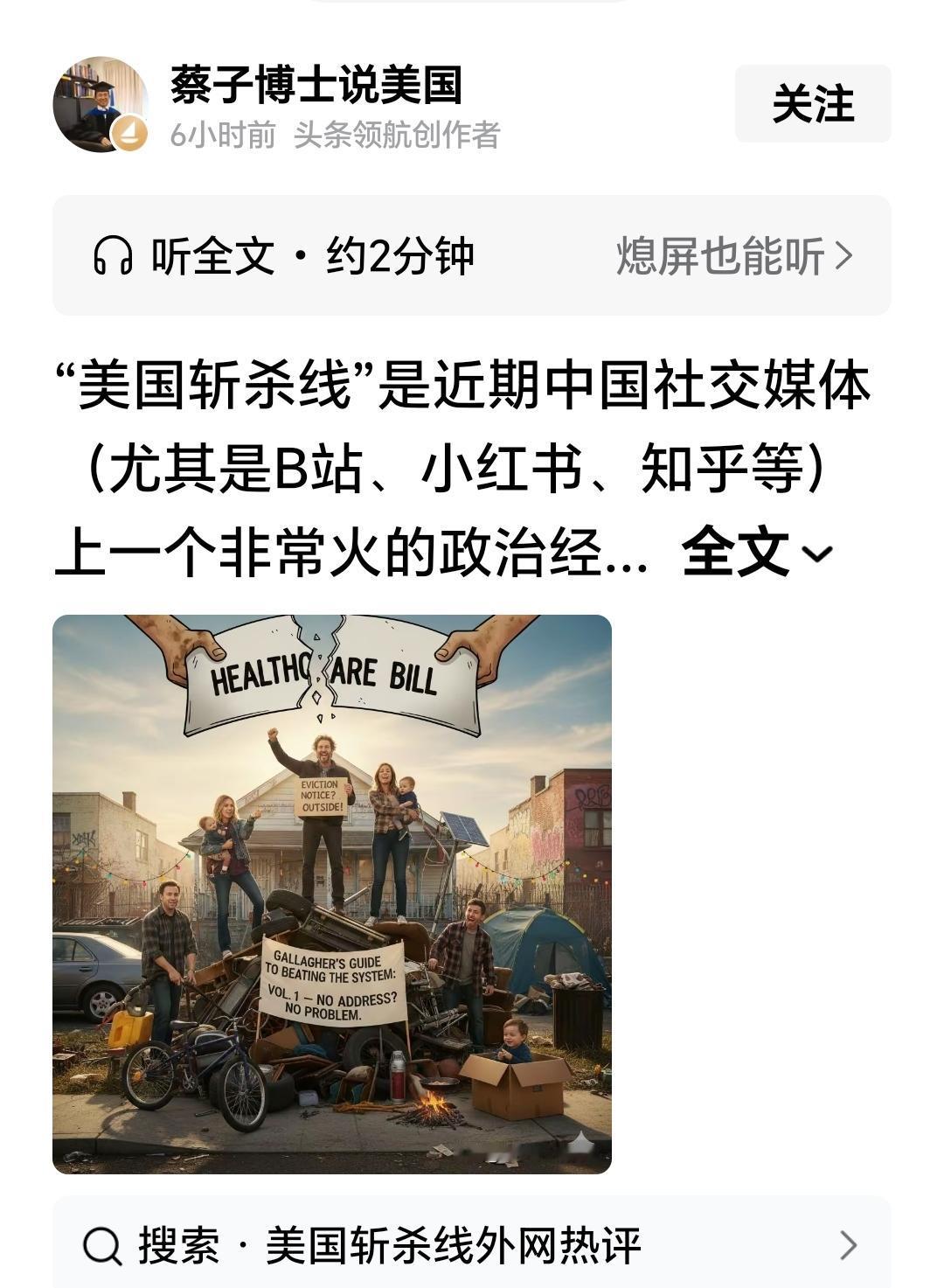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代表作《双城记》《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艰难时世》《远大前程》。
《艰难时世》《艰难时世》发表于1854年,这部作品以双线叙事结构,编织了一幅关于意识形态专制、阶级矛盾与人性异化的全景图,至今仍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预言。

托马斯·葛擂硬——这个五金批发商出身的国会议员,是狄更斯塑造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之一。他所奉行的“事实哲学”将人类经验简化为可计算、可衡量的数据,其著名宣言“人从生到死的每一步都应该是一种隔着柜台的现金买卖关系”,彻底暴露了功利主义伦理的冰冷本质。在葛擂硬的世界里,情感、想象、艺术与精神追求因其无法产生直接经济利益而被视为无用甚至有害的赘余。
这种哲学在其子女教育中得到了最极致的实践。露易莎和汤姆在童年时期被剥夺了所有幻想与游戏的权利,他们的生活被囚禁在“事实”的牢笼中。狄更斯以令人心碎的笔触描写了这两个孩子如何像温室植物般畸形生长:露易莎学会了用沉默承受痛苦,将全部情感寄托于弟弟身上;汤姆则在压抑中滋生出扭曲的利己主义。当露易莎在父亲追问“什么是婚姻”时,只能机械地回答“一个契约”,这种情感能力的彻底萎缩,正是葛擂硬教育最可怕的成果。

更富悲剧性的是,葛擂硬的“事实哲学”最终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中彻底破产。露易莎为帮助弟弟而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银行家庞得贝,这桩纯粹利益交换的婚姻很快陷入绝望;汤姆则在放纵与堕落中沦为窃贼,最终需要靠父亲一贯鄙视的马戏团艺人拯救。狄更斯通过这种情节安排完成了对功利主义的终极讽刺:那些被认为“无用”的情感与道义,恰恰是危机时刻唯一可靠的精神支柱。
银行家约西亚·庞得贝是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自我标榜“白手起家”的工业巨头,通过精心编造的弃儿奋斗史,建构了一套符合时代精神的神话叙事。他不断宣扬自己如何从“阴沟里爬出来”成为焦煤镇的主宰,却严苛禁止亲生母亲出现在公众视野,甚至污蔑她曾抛弃和虐待自己。这种对血缘亲情的背叛与工具化利用,揭示了新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主要矛盾:他们既需要传统伦理作为社会认可的基石,又在实践中彻底颠覆这些伦理。

庞得贝对待工人的态度进一步暴露了这一阶级的意识形态本质。他将斯蒂芬等工人视为纯粹的“人手”,是可以随意替换的生产要素。当斯蒂芬因拒绝加入工会而遭排斥,又因不愿充当密探而遭解雇时,庞得贝表现出的不是同情而是恼怒——他不能理解为何有人会拒绝成为他权力游戏中的棋子。这种将人物化的思维,正是工业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产物。
最令人深思的是庞得贝失窃案的情节发展。银行被盗后,他毫不犹豫地怀疑并通缉早已离镇的斯蒂芬,这一行为不仅展现了权势者的傲慢,更揭示了新资产阶级社会认知的局限:他们只能理解金钱关系,无法理解道义、忠诚等超越性价值。斯蒂芬为自证清白而赶回焦煤镇,最终失足坠入废弃矿坑惨死,这一结局成为对整个制度的血泪控诉。
在葛擂硬与庞得贝主宰的冰冷世界里,西茜·朱浦所属的马戏团成为了人性最后的避难所。这些流浪艺人被主流社会视为“不务正业者”,他们的表演被认为缺乏“事实”基础。然而,恰恰是这个边缘群体保留了完整的情感能力与道德直觉。

当葛擂硬的“模范学生”比周——这个完全内化了功利主义逻辑的青年——冷酷地追捕汤姆时,是马戏团成员以朴素的道义感伸出援手。他们帮助汤姆逃脱不是出于利益计算,而是基于“他是个陷入困境的年轻人”这样简单的人性判断。这一情节构成了小说最强烈的反讽:被“事实哲学”排斥的情感与同情,恰恰是维护基本人性尊严的最后屏障。
马戏团在小说结构中的位置极具象征意义。他们游走于社会边缘,不受葛擂硬式教育的污染,保持着对美、欢乐与人际温情的天然感受力。西茜对露易莎的友谊、对葛擂硬的原谅,代表了一种超越功利计算的生命智慧。狄更斯通过这个群体暗示:一个彻底驱逐了“幻想”与“情感”的社会,最终将在精神上自我毁灭。

要真正理解《艰难时世》的批判力度,必须将其置于1850年代英国的社会语境中。此时的英国刚举办完万国博览会,工业产出占全球三分之一,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维多利亚时代看似达到了繁荣的顶点。然而,狄更斯穿透了这层光辉表象,揭示了工业化带来的深刻社会重组。
小说中的焦煤镇本身就是工业英国的缩影:机器永不停歇地轰鸣,烟囱如同巨树般林立,空气弥漫着煤烟,河流被染成紫色。在这个环境中,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重构。旧贵族虽然保留了象征性地位,但实际权力已转移到葛擂硬、庞得贝这样的新兴资产阶级手中。这些工业家、银行家、商人的崛起,标志着基于血缘的等级制让位于基于财富的阶级制。

然而,这种阶级流动性的增加并未带来社会和谐,反而加剧了阶层矛盾。庞得贝对工人的剥削、葛擂硬对“人手”的冷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积累财富过程中的残酷性。斯蒂芬的命运——熟练技工却生活困苦,四十多岁已头发花白、弯腰驼背——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普遍困境。狄更斯通过斯蒂芬之口提出的问题:“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经常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不是对的?”直接挑战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艰难时世》最深层的批判指向了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奉为最高原则,在实践中却往往沦为替现状辩护的工具。葛擂硬的教育理念、庞得贝的管理哲学,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化。
狄更斯揭示了功利主义如何扭曲人性认知。当一切价值都用“有用性”衡量时,那些无法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品质——如想象力、同情心、艺术感受力——就被系统性地贬低。这种思维甚至在家庭关系中蔓延:葛擂硬将子女视为需要“塑造”的材料,庞得贝将母亲视为需要“隐藏”的耻辱。人际关系被简化为利益交换,情感联系被契约关系取代。

更危险的是,功利主义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科学”辩护。根据这套逻辑,富人的成功证明其品德与能力优越,穷人的困境则归咎于个人失败。庞得贝反复强调自己从“阴沟”崛起的神话,隐含的信息是:任何人都能通过努力复制他的成功,失败者只能怪自己不够勤奋。这种话语巧妙地将结构性剥削转化为个人责任问题,消解了集体抗争的道德基础。
斯蒂芬的悲剧彻底颠覆了这种叙事。他勤奋、诚实、熟练,却因拒绝背叛工友而失去工作,因老板的猜疑而身败名裂,最终在自证清白的路上意外身亡。他的命运证明,在权力不平等的社会中,个人美德不足以保证尊严生存,制度性不公正足以摧毁最勤劳的个体。

《艰难时世》出版于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前五年,却已敏锐捕捉到即将风靡英国的“适者生存”社会思潮。庞得贝的崛起神话、葛擂硬对弱者的蔑视、比周对汤姆的冷酷追捕,都体现了这种将自然法则简单移植到人类社会的倾向。
在焦煤镇的世界里,竞争被奉为最高美德,同情被贬为软弱缺陷。庞得贝在议会上宣称:“我们必须要有竞争,要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规律。”这种话语为剥削披上了科学外衣,将社会不平等自然化、正当化。工人阶级的贫困被解释为“不适应”竞争环境,资产阶级的财富则被看作“适者”的合理奖赏。
然而,狄更斯通过马戏团的介入解构了这种逻辑。当汤姆这个“不适者”面临毁灭时,拯救他的不是奉行竞争哲学的“适者”,而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艺人群体。这一情节暗示:人类社会如果完全遵循丛林法则,最终将丧失使人区别于野兽的文明特质——互助、同情、自我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