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长江汉水拧出来的三镇,
武昌守着城根,汉口淌着商气,汉阳烧过铁水。
1861年汉口开埠,洋行挨着货栈,江面上的船挤得连风都要侧身过,
“九省通衢”不是碑上的字,是纤夫肩上的绳勒出来的。
清晨的巷子比闹钟醒得早,面窝在油锅里转着金圈,热干面拌芝麻酱要快,慢了面就坨,
武汉人吃“过早”不挑排场,蹲在路边就扒拉,问哪家好,只说“吃了就晓得了”。

这份实在,跟1890年汉阳铁厂的钢水一样,
第一炉淌出来,比任何大话都硬气。
黄鹤楼是1985年重盖的,但李白送孟浩然的江风没散。
站楼上听江汉关的钟,1924年挂的钟敲了近百年,每一声都裹着芝麻酱的香。
三镇的历史不飘着,就混在巷子里的烟火、江面上的船影里,实在得很。
今天,小汐跟诸位聊聊武汉的小吃……

别看名字带“鸡”,里头可没半块鸡肉。
这小吃源起解放前广州夜市,后被武汉人“改刀”,
用料酒、酱油拌着五花肉丁、香菇碎,和糯米一起蒸熟,
再裹层面糊下油锅炸得金黄酥脆,外皮炸出鸡皮似的凹凸纹,才得了这名。
老武汉人管吃早饭叫“过早”,
天蒙蒙亮,巷口摊子支起油锅,糯米鸡的油香混着糊汤粉的辣味儿,能勾得人直咽口水。
这糯米鸡,外头炸得酥脆,咬开是糯米的软黏,
里头裹着肉香、胡椒香,像极了武汉人的性格,直爽中带着热乎劲儿。
糯米鸡,十几年前就上过美食频道,那团子捏得瓷实,
炸得火候刚好,外皮脆得掉渣,里头糯得能拉丝。
如今,它不光是早餐,还能涮火锅,
吸饱汤汁后,外酥里糯的口感更妙,成了武汉人冬日里最惦记的“暖胃神器”。

外地人打卡必吃的“硬核过早”。
北宋黄州府城便有甜味烧梅,形似石榴,寓“榴结百子”之吉。
清末山西人胡佑臣在汉口后花楼街开顺香居,将北方烧麦改良:
用烫面擀出24道褶“梅花皮”,裹上重油糯米馅,黑胡椒提辣,猪油增香,
蒸至“底托银菊,顶绽梅花”,油重而不腻。
老武汉人吃烧梅讲究“解腻三件套”:姜丝、花红茶、镇江香醋。
最地道的吃法是夹着油饼,糯软与酥脆在嘴里“打架”,黑胡椒的辛香直窜鼻腔。
这口“形如梅花、油润鲜香”的烧梅,不仅是武汉“过早三宝”之一,
更是街头巷尾的市井记忆,
咬开那层薄皮,尝的是历史,吃的是人情。

是武汉“过早”的魂。
清末汉口码头,商贩收鱼贩剩鱼杂熬汤,加生米粉增稠,供苦力冬日抵饿。
野鲫鱼文火炖整夜,鱼骨化汤、鱼肉融髓,配籼稻米粉细如银线,入喉顺滑。
胡椒提鲜去腥,撒把葱花,热辣鲜香直窜鼻腔,
捞根油条掰段泡汤,酥脆裹着浓稠鱼糊,一口下去,
从胃暖到脚后跟,码头工人称“听头”(武汉方言:舒服)。
这碗粉,藏着武汉的江湖气。
制作技艺已列江汉区非遗,老字号坚持“鱼骨化汤”古法,
每50碗汤用1斤鲫鱼熬6小时,滤渣后兑粉成糊,油条现炸金黄酥脆。

这口清光绪年间的“金窝窝”,是武汉人“过早”的魂。
昌智仁在汉正街集稼咀支起油锅,用大米、黄豆磨浆,撒把黑芝麻,
拿铁勺一舀一炸,边厚处松软如棉,中薄处脆得掉渣,
中间那个洞像极了老码头的船眼,透着股子江湖气。
如今的面窝,还是那股子烟火味,
铁勺往热油里一浸,米浆“滋啦”一声贴上去,中间扒个洞,炸到两面金黄,
咬一口,外酥里软,葱香、姜末、芝麻香在嘴里炸开,配碗米酒,那叫一个“虚浮”。
别小看这口锅边小吃,它串起武汉的码头往事。
外地人来打卡,得赶早去户部巷,
看面窝勺一转一抖,米浆落进油锅,瞬间腾起香气,那才是活着的武汉味道。

这口金黄酥脆的豆皮裹着软糯糯米,藏着鲜肉、鲜蛋、鲜菇的“三鲜”灵魂,
是外地人来汉打卡的“硬核标配”。
它诞生于三国时期,孙权为犒劳三军,命厨子以绿豆大米磨浆摊皮,
裹入肉丁笋丁香菇煎制,形似“豆”且外皮酥脆,得名“豆皮”。
明清时,这道军粮演变为码头工人的饱腹美食,
逐渐定型为“三鲜”之味,成为武汉早餐桌上的“顶流”。
制作三鲜豆皮是门火候与技艺的学问。
绿豆大米按2:1比例磨浆,摊成薄如蝉翼的面皮,
再铺上蒸熟的糯米,撒上炒制入味的肉丁、香菇、冬笋与豆干,最后淋上蛋液,
小火慢煎至外皮焦香。
一口咬下,酥脆的豆皮与绵密的糯米交织,鲜香的馅料在舌尖绽放,
咸香中透着豆香米香,层次分明,回味无穷。

清道光三十年《汉口竹枝词》就记过“过早”习俗,
它因形似鸡冠得名,至今仍是外地人来汉必打卡的“烟火味”。
老面发酵三四个钟头,揪剂擀皮包鲜肉葱花馅,对折捏边后“扑通”入油锅,
160℃芝麻油炸得金黄膨松,外皮脆得能听见“咔嚓”声,
内里蜂窝状面芯裹着肉香,咬一口,脆壳碎裂后是暄软的麦香与肉汁,
武汉人管这叫“靠馅香、靠边脆”。
它不似北方饺子煮得软乎,而是“炸”出来的江湖气。
华师南门、山海关路的小摊前,总围满伸脖子的食客,趁热咬开,配碗热干面或豆浆,
就是武汉人“过早”的仪式感。
如今虽拆了老摊,但街头巷尾的鸡冠饺香,仍是这座城市最实在的烟火味。

明朝时,黄陂人用早稻米、绿豆“变废为宝”,
摊成薄饼切丝,既省粮又添营养。
清道光年间《汉口竹枝词》早有记载:“切面豆丝干线粉”,比热干面还早两百年。
最出名的要数祁家湾的柴火炕豆丝,
土灶烧麦秸,大蚌壳旋米浆,摊出的饼皮微焦带烟火气,晒干后能存一冬。
老谦记1918年首创的牛肉炒豆丝更绝,如今非遗技艺仍用石磨磨浆,
米豆比例精到,多一分豆则“肉坨”,少一分则“劲道”。
这豆丝吃法百变,枯炒脆如薯片,糊汤暖胃,火龙果豆丝红得喜庆,寓意“日子红火”。
黄陂人过年必囤干豆丝,腊肉炒、青菜煮,连糍粑都能搭一锅炖。
一口下去,便是“虚浮”(舒服)了。
这味道,出了黄陂,难寻。

武汉人喊它“麻鸡蛋”,外地人打卡必吃的“甜蜜炸弹”。
清末荆州陶家战乱团聚,用糯米、红糖搓团裹芝麻炸成“欢喜团”,
取“粘如糯米永不离”的吉意,后传到武汉叫成“欢喜坨”。
如今汉阳棉花街的老手艺还在,
糯米浆吊干搓粉团,蘸满芝麻温油慢炸,出锅滚饴糖再簸芝麻,
外层酥脆“咔嚓”响,内里软糯夹着糖汁,
咬一口芝麻香混着甜润,像把团圆嚼进了嘴里。
这小吃从码头工人扛包换钱的“欢喜签”讨口彩,到2004年“大麻元”入选中国名点,
如今成了武汉“过早”的活地图。
外地人来武昌司门口、户部巷,总见着炸得金黄的欢喜坨堆在竹匾里,
热乎时圆鼓鼓的像小太阳,凉了也不馊,
揣两个当干粮,甜得扎实,香得透亮。

诞生于1922年汉口后花楼。
田玉山最初卖小笼包和葱饼,后改良镇江工艺,用皮冻调馅,
创出“汤融而不泄”的绝活。
老武汉人常说“吃汤包要配热干面,一热一鲜才过瘾”。
包制讲究“皮薄如纸,褶似菊瓣”,十八道细纹捏成鲫鱼嘴,蒸熟后汤浮馅球,
先咬小口吸汤,再蘸姜丝醋碟吃馅,鲜得人舌尖打颤。
吉庆街老四季美仍坚持“现擀现包”,蟹黄必选阳澄湖大蟹,肉冻要熬足三小时,
连蒸笼都刷着麻油防粘,
这股子较真劲,让它在百年间从巷口摊子蜕变成“中华老字号”,2020年更列入湖北非遗。
外地人来武汉,没在户部巷排过四季美的队,不算真正打过卡。

民国初年,汉口码头工人为赶工,将凉面烫热拌麻酱,既顶饱又热乎,这便是热干面雏形。
1930年李包在关帝庙卖“烫面”,因“热乎、干爽、管饱”得名,
后蔡明纬改良芝麻酱配方,1950年正式定名,2014年列入湖北非遗。
如今日均消耗超200万碗,游客来汉必吃。
碱水面煮至七成熟,过冰水拌香油防粘,
冷藏醒面4小时,复烫时在沸水翻个身,
淋上用香油调稀的芝麻酱,撒萝卜丁、酸豆角、葱花,最后点辣油。
金黄油亮的面裹着38种香气的麻酱,
第一口是焦香,第二口是麦香,第三口酸豆角刺破厚重,辣油在舌尖炸开。
武汉人吃它讲究“站着吃、蹲着咽”,
吃完抹嘴就走,这股子“不服周”的劲头,全在这碗面里了。

小汐说完这些吃食,您要问武汉的魂到底在哪儿?
它不在黄鹤楼的飞檐上,倒像这热干面里的芝麻酱,
看着粗粝,拌开了才知香。
长江水往东流,日子在油锅里滋滋响,
您来巷子口站一站,江风都带着面窝的焦香。
要不,明天过早咱们约碗豆皮……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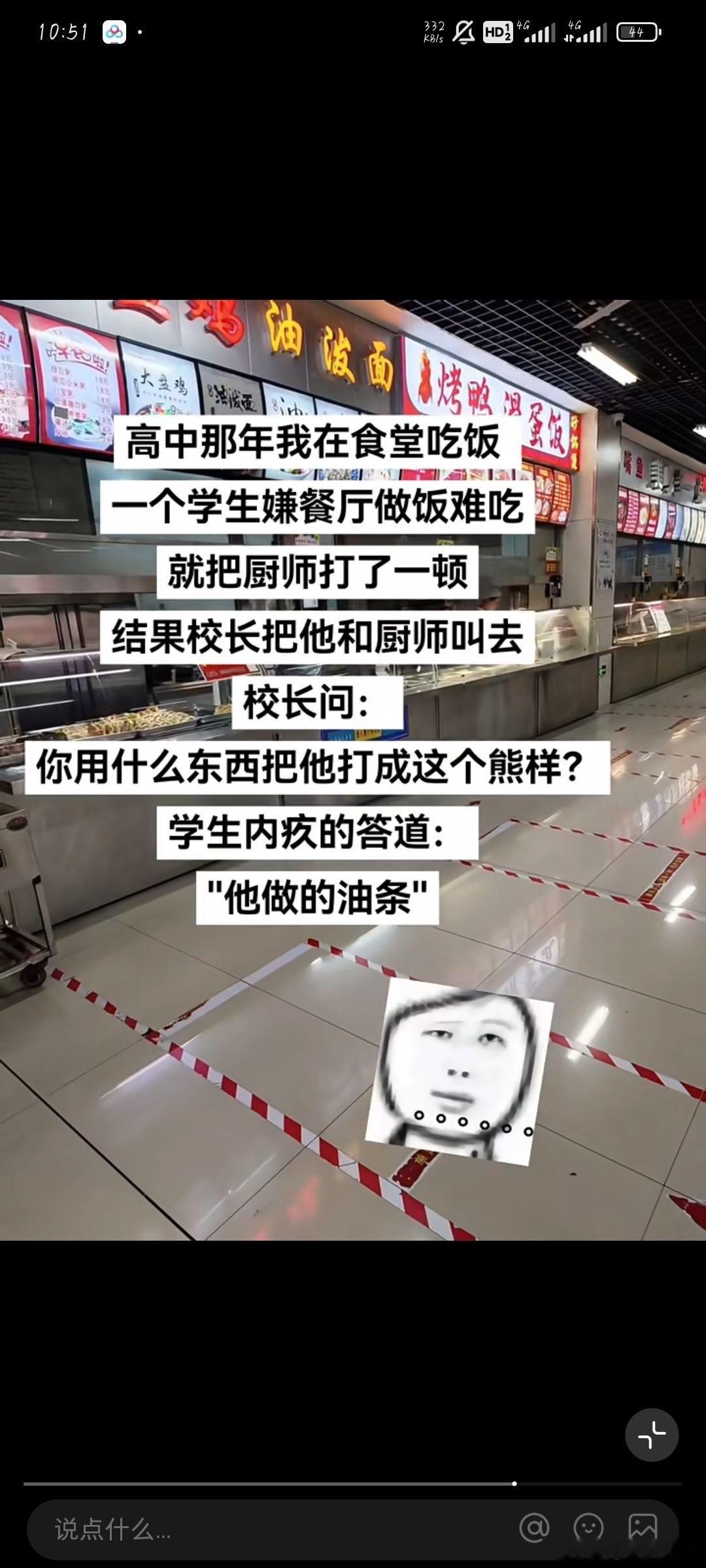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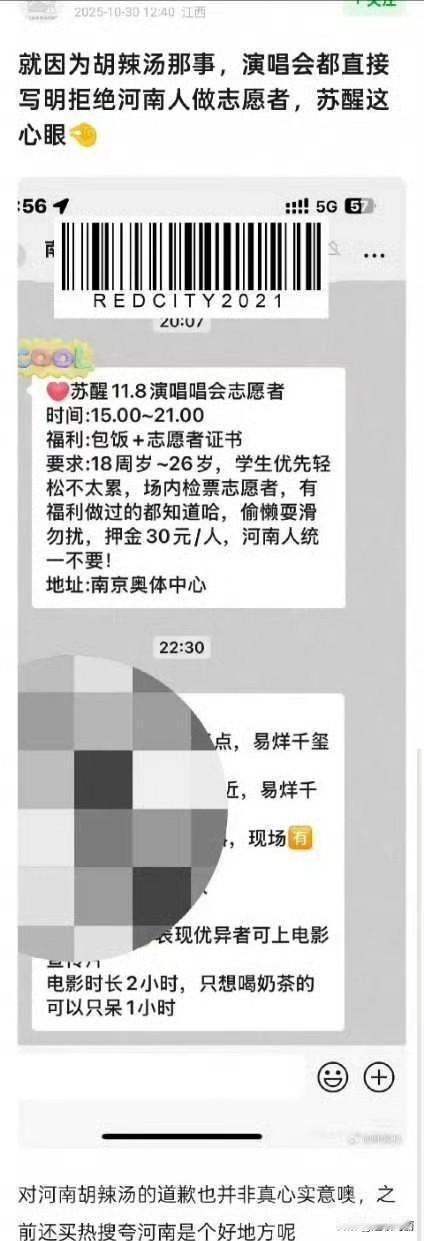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