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阴影:一个货车司机的白血病与一座村庄的迷思
山村的清晨,薄雾如纱,缠绕着远近的群山。李建国发动了他那辆十几万的东风货车,引擎的轰鸣声打破了李家坳的宁静。这声音,曾是他一家人的希望之歌,如今听来,却带着一丝沉重的悲凉
村口那栋崭新的三层小楼,瓷砖在初升的日照下闪着刺眼的光,那是他半生的心血,也是他“能干”的证明。旁边那座略显斑驳的老平房,还存放着旧时的记忆。县城里那套为儿子将来结婚准备的商品房,钥匙还没捂热。这个四十二岁的汉子,曾经是村里人羡慕的对象——有车、有楼、有眼光。可现在,这一切都被一张薄薄的、却重如千斤的诊断书击得粉碎:急性髓系白血病。
“建国,听说了吗?王老六他爹昨儿夜里走了,孝子贤孙们明天一早要去十字路口‘烧车马’。”邻居老张头隔着矮墙喊道。
李建国正蹲在门口,端着妻子桂芬熬好的中药,听到这话,端碗的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他“嗯”了一声,没再多言。那个十字路口,就在他家新楼和老房的正前方,是村里几条小路的交汇点,也是所有红白喜事的“仪式场”。每当有老人去世,出殡前的清晨,丧属必会到那个路口,为逝者的灵魂焚烧纸扎的车、马、童男童女,谓之“送行”。

桂芬从屋里出来,脸上带着愁容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愤:“又烧!这月都第三回了!那纸灰混着烟,风一吹直往家里灌,窗子都不敢开。自打咱家这新楼盖起来,正对着这路口,就没消停过!”
村里关于李建国得病的缘由,早已有了“定论”。闲坐在村头大槐树下的老人们,言之凿凿。
“建国这孩子,啥都好,就是八字太软,镇不住。”赵奶奶瘪着嘴,神秘兮兮地说,“那路口,阴气重啊!总在那儿烧东西,招惹些不干净的去处。他那新楼,正好成了‘靶子’。”
“可不是嘛!”旁边有人附和,“老话讲‘路冲煞’,他家那是正对着十字路,煞气最猛。他一个开夜车的,本身就走南闯北,气场不稳,这一冲一撞,好人也得垮掉。”
这些议论,像无形的风,钻进了李家每一个角落,也钻进了李建国和桂芬的心里。起初,他们不信,可病急乱投医,听得多了,心里也难免犯起了嘀咕。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李建国刚做完一轮化疗,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同病房的病友家属闲聊起来。
“老弟,你这病来得凶啊。家里是不是有啥说道?”一个热心的大婶问。

桂芬眼眶一红,像是找到了宣泄口,把村里的传言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大婶一拍大腿:“哎呦!这可不能不当回事!我们那边也有这么一家,就是房子盖在丁字路口,家里接二连三地出事。后来请了大师看了,挪了大门,才慢慢好转。你们也得想想办法啊!”
正来看望的村支书李为民刚好进门,听到这话,眉头皱成了疙瘩:“桂芬,建国,你们都是读过初中的人,咋也信这些?生病了咱就科学治病,要相信医院,相信医生!那些都是封建迷信!”
桂芬猛地抬起头,声音带着哭腔:“支书,我们也不想信!可这病为啥偏偏落在我们家建国头上?他身体一直那么好!你不晓得,村里人都这么说,我心里堵得慌啊!万一……万一是真的呢?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
李建国虚弱地摆摆手,声音沙哑:“支书,桂芬,别争了。我现在……只想活着。”
话虽如此,那个十字路口的阴影,仿佛真的化作了一块巨石,压在了夫妻二人的心上。
治疗的费用是惊人的。虽然李家有资产——村里的楼房、县城的房子、货车,但这些都是固定资产,而且大多欠着银行贷款。现金像流水一样花出去。靶向药、进口化疗药,很多都是医保不报销的。短短几个月,家里的积蓄就见了底。
一天夜里,桂芬握着手机,犹豫了很久,对李建国说:“建国,要不……我们把县城的房子卖了吧?”
李建国沉默了。那是给儿子准备的婚房,是他们对下一代全部的寄托。他摇了摇头,半晌,吐出一句话:“先别卖。我听病友说,可以弄那个……水滴筹。”
桂芬愣住了:“水滴筹?那……那不是家里特别困难,走投无路的人才用的吗?咱家有房有车的,去筹款,别人会不会说闲话?”
“闲话?”李建国苦笑一下,蜡黄的脸上露出一丝无奈,“命都要没了,还怕闲话吗?再说,咱们的情况,看起来光鲜,底子早就空了。活下去,比面子重要。”
就这样,一篇由亲戚帮忙撰写的水滴筹求助链接,在李家坳乃至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开来。链接里,详细描述了李建国的病情和困难,隐去了他家具体的资产情况,只强调“治疗费用高昂,家庭难以承担”。
捐款从四面八方涌来,十块、二十、一百、两百……大多是陌生人的善意。但村里人的议论,却再次炸开了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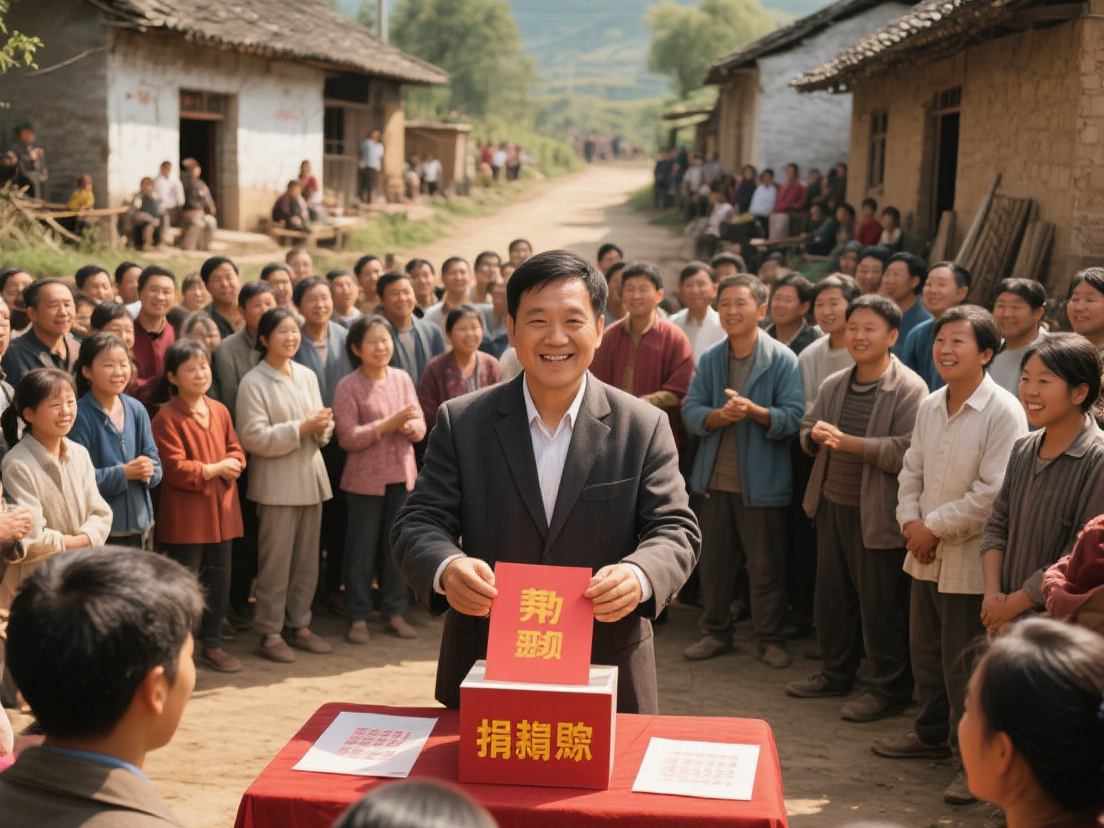
“看见没?李家都上网要饭了!”在小卖部门口,有人咂着嘴说。
“他不是刚盖了楼,还在县城买了房吗?咋还跟我们这些平头百姓要钱?”
“就是,那辆货车也值十几万呢!真要治不起,先把车卖了呗!”
“唉,话也不能这么说,得这病就是个无底洞。可能真是没办法了。”
“没办法?我看是精明!自家的不动产不动,先动用大家的善心。这算盘打得响哟!”
这些风言风语,桂芬在买菜时听到了几句,回家躲在厨房里偷偷抹泪。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和孤立。丈夫的病,家庭的困境,非但没有换来纯粹的同情,反而掺杂了这么多复杂的猜忌和指责。
儿子小李从学校回来,年轻气盛,听到这些议论,气得满脸通红:“妈!我们不筹了!我把县城的房子卖了给我爸治病!我们不用他们可怜!”
李建国把儿子叫到床前,握着他的手,气息微弱却坚定:“儿子,爸对不起你……婚房,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爸这病……是个长久战,你得留着点底子。别人的话,随他们说去。活下去,看着你成家立业,比什么都强。”
村里的小学教师,也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大学生之一李文,在网上看到了筹款链接,默默捐了五百元。他在自己的朋友圈写了一段话,没有指名道姓,却引人深思:
“我们习惯于为悲剧寻找一个简单归因,仿佛找到了‘原因’,就能获得安全感,将自己与不幸隔开。于是,疾病归咎于风水,困顿归咎于品行。我们更习惯于用‘完美受害者’的标准去衡量求助者,要求他们必须一无所有,才配得到帮助。却忘了,人性的复杂与命运的无常。当一个家庭的悲剧,变成一场关于风水、资产与善心资格的公开辩论时,我们每个人,是否都成了那十字路口旁,无声的看客,甚至,添柴加火的人?”
李建国不知道李老师写的这些话。他只是在病痛的间隙,呆呆地望着窗外。他有时会想,如果当初没有执意要盖那栋气派的新楼,如果没有正对着那个总是青烟缭绕的十字路口,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但他更清楚,真正吞噬他的,不是那飘渺的纸灰,而是血液里那些疯狂增殖的坏细胞,以及比病魔更让人心寒的、现实的无情与人心的凉薄。
他的货车静静地停在院子里,覆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那曾经承载着家庭梦想,驶向远方的车轮,如今深陷于由疾病、流言、传统迷思和现实困境交织而成的泥沼中,再也无法前行。而那十字路口的阴影,究竟是在屋外,还是在人们的心里,已然分不清。
(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 图/源自网络 ,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声明本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