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作者 |树东
本篇编辑 | 猫须
插图来源 |Ran MIYAZAKI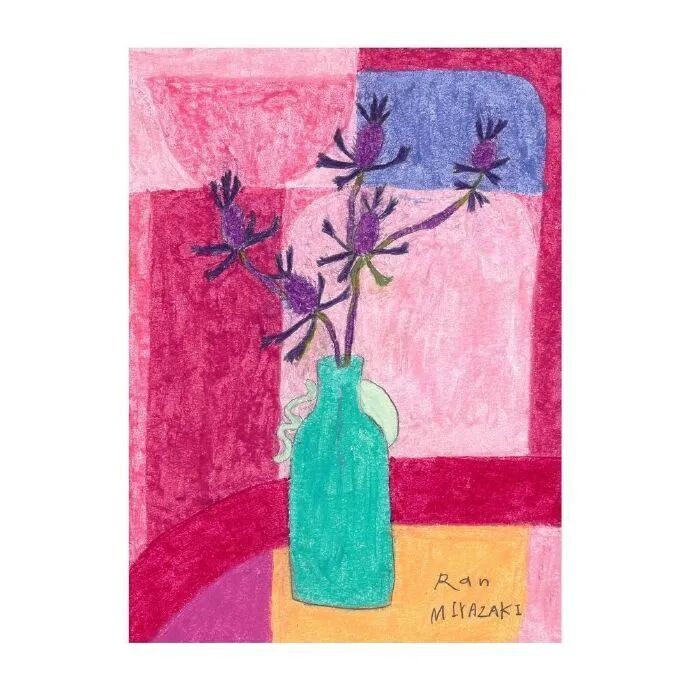
第二天,老爸和妹妹分别回了家。前夫开着车,语气罕见地带着一丝示弱,对我说:“我觉得自己肯定也有抑郁倾向,陪我去医院看看吧。” 我信以为真,甚至还生出一点“同病相怜”的错觉。
没想到,车直接开到了心理康复医院楼下。他拉着我,不是走向门诊部,而是径直走进了住院部大楼,按下了四楼的电梯。“弄错了吧,我是陪我对象来看病的。”我试图挣扎,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接诊的王大夫只是平静地看着我,说:“来了,就住段时间吧。”
我趁着手机还没被没收,用最快的速度给县里的女领导发了一条求救短信:“我是被家暴的,我是被逼住院的,我要回家,因为没有人接送孩子上学,我要回家照顾她。”我天真地以为,代表着妇女权益的“娘家人”一定会来解救我。
直到护士温和而坚定地收走我的手机,那“嘟”的关机声,像最终落下的审判槌,我才真正明白——我失去了与外界最后的联系,我又要住院了。
然而,你可能永远也想象不到,在那一刻,被剥夺了自由的我,心里涌起的,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无比的平静和喜悦。
就像一个在狂风暴雨的海上漂泊了太久的水手,终于被冲上了一座孤岛,虽然荒凉,但脚踩在了实地上。一种巨大的安全感包围了我——这里有医生,有护士,我再也不用独自面对情绪的惊涛骇浪了。
我在心里默默地欢呼:耶!我没有吃下那一整瓶碳酸锂,我终于被正式承认是个病人了!我从第一次重度抑郁就渴望得到的、系统性的住院治疗,在抗争和挣扎了16年后,竟然以这种被“骗”的方式,实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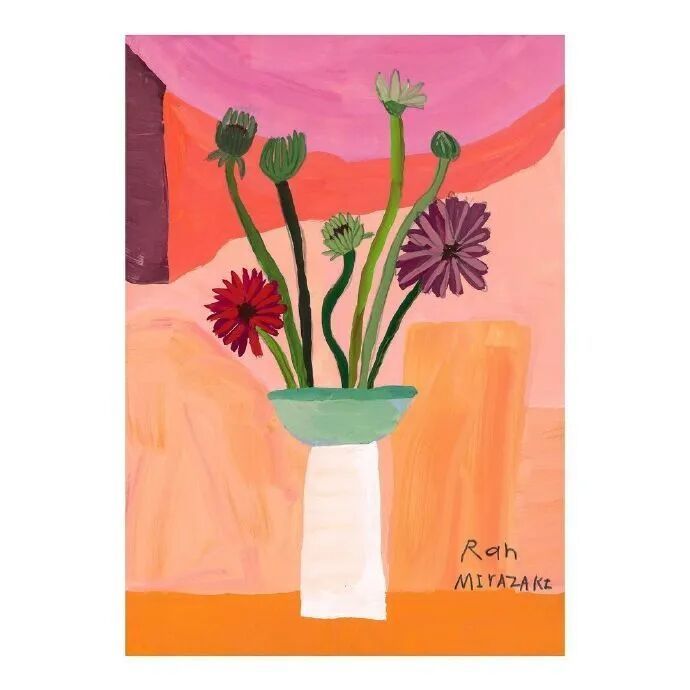
但“平静”只是暂时的,躁狂的能量还在我的血液里奔涌。住院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成了女病区的一个“传奇”。
原因是我听到了熟悉的呻吟声。循声望去,在楼道的长椅上,躺着一位瘦骨嶙峋的病友,她的双手被束缚带从背后绑住,身体扭曲着,嘴里不停地哀求:“放开我,求求你放开我……”我认识她,上次住院时,她就有抢食、捡拾地上异物吞咽的行为,护士们是为了她的安全,才出此下策。
但那一刻,那个为妇女权益四处奔走、骨子里刻着“正义”二字的我,瞬间被点燃了。我冲到护士站,对着值班的两个新护士,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把她解开!找一个空的病房,我陪着她过夜,我保证她不会出事!”
新护士不认识我,只把我当成了一个发病闹事的普通病人,厉声命令我回到自己的床上。我仗着自己认识院长和办公室主任,底气十足地跟她们对抗:“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信不信我马上给领导打电话,问问你们这样对待病人对不对?”
我的“正义凛然”,换来的却是她们手中冰冷的束缚带,和从男病区紧急借调来的两名男护士。四个人,对我开始了“围剿”。
我可是拿过“三八红旗手”和“慈善先进个人”的人啊!我明明是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壮举,凭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我内心无比确信,我是正义的一方。那一刻,我感觉内心里那一头被锁链紧紧套住、伤痕累累的母狮子,终于挣脱了所有束缚,发出震天的嘶吼,向着面前的“敌人”猛扑过去。
那个个子高高的男护士从后面死死抱住了我。但我没有束手就擒,反而借助他的支撑,猛地跳起来,用尽全身力气朝着面前的矮个子男护士身上踢去!是的,我成功踢到了!一种扭曲的快感传遍全身。
但随即,我抬到半空的腿被牢牢控制住,两边的女护士一拥而上,四个人像抬一件物品,把我扔到了一张只有被褥和床单的空床上。我的手腕、脚踝,迅速被束缚带固定在了床栏上。
我动不了了。
满头的汗浸湿了头发,我大口喘着气,浑身的细胞却仿佛都张开了,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畸形的酣畅感!活了38年,无论是在原生家庭还是在婚姻里,我从来没有如此彻底地、不计后果地为自己的权益(哪怕只是我认为的“权益”)争取过,反抗过!
这次在精神病院里的“暴力反抗”,竟然成了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我太棒了! 正是因为在这个绝对“安全”的医疗环境里,我知道无论我如何“作”,都不会有生命危险,我才敢真正地、毫无保留地做了一次自己。
不仅如此,当后来我央求放开我去厕所被拒绝时,我直接尿湿了裤子和床单。在被注射了两针镇定剂后,我带着这种混杂着屈辱、反抗和胜利的复杂情绪,沉沉地睡去了,一直到第二天下午。

我摸了摸昏昏沉沉的脑袋,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周围是二十多张空着的床铺,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窗帘,像一双双空洞的眼睛,病房也没有门,一览无余。我叫了一声护士,胖乎乎、面善的张护士走了进来。
“你终于醒过来了,头疼吗?饿不饿?正好她们在吃晚饭,你快起来进去吃吧。”
“张护士,”我羞愧地低下头,“我想跟昨晚那个男护士说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踢他的……”
“好的,我跟他说。以后可别那么冲动了,住进来了,就好好配合吃药,配合管理,这样才能快点好起来。”她温和地嘱咐。
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像個犯了错的孩子。
下床第一件事,是换了一身干净衣服。从病房到活动室,不过20米的距离,我却像走进一个新世界,第一次住院的那几天仿佛全没有发生过一样,这里的一切对我又是新鲜的了。紧紧跟在护士身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
南侧是紧挨着的四个病房,只有最里面一间有门。北侧依次经过医护室,没有门的洗刷间、卫生间、浴室。那道通往活动室的钢化玻璃门,必须有护士手中的感应牌才能打开,像一道结界,隔开了两个世界。
“来,拿个碗和勺,找这个阿姨打菜,再去那边拿馒头,找个位置坐下,吃完送回去。”护士耐心地指引。
我顺从地照做。活动室是南北向的,南边两排窗户只能打开很小的缝隙,西边的窗户可以看到壮观的夕阳。东北面是分发食品的小窗口,家属送来的零食都从这里递进来。西北面是厕所,同样没有门,只有两个经常堵塞的蹲厕。
吃饭的桌子是学校用的那种四座桌椅,不锈钢桌面,塑料圆凳。饭后,有人负责打扫,其余的人就在中间狭长的空间里来回踱步,像困兽。恢复好一些的,可以和护士打打扑克,或者叠叠“金元宝”——那是接近出院的人才能参与的“高级活动”。
这里有一个女人,其实早就达到了出院标准,但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迟迟不来接她,她只能日复一日地在这里等待,眼神从期盼变得麻木。
我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神秘的社群。这里有老有少,病情有轻有重, 性格爱好各不相同,高矮胖瘦美丑皆有。她们是全县精神类疾病最重的一群女性,是被正常世界遗忘在四楼女病区的“异类”。未来的一个月,我将与她们朝夕相处。
我甚至产生了一种荒谬的“使命感”:全县那么多妇女干部,只有我有这个机会,潜入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亲眼看看这些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那么,就让我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写一部《精神病院女病区女性权益保护调查报告》吧。这个念头,让我在绝望中,找到了一丝观察者和记录者的抽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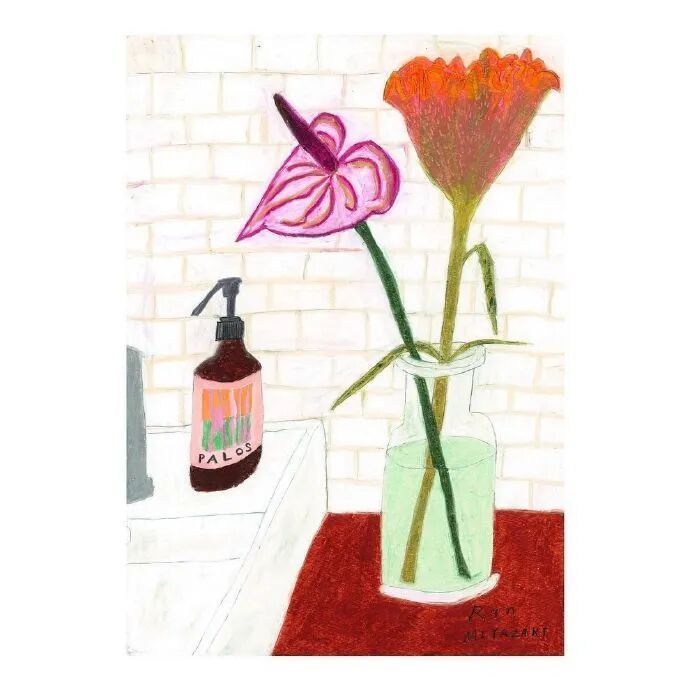
这些病友住院,最重要的原因大多是在家不肯吃药,家属无力管理。因此,每天早、中、晚三次的服药时间,就成了病区里最庄严又最紧张的仪式。护士推着装有药盒的小车,逐个叫名字。病友们排着队,端着水杯,在护士的注视下仰脖吞药,然后抬起舌头,证明没有藏药。
总有几个“特殊分子”。有一个接近一米七、双眼皮大眼睛的姑娘,重度抑郁伴有严重幻听幻视。一发病,她就脱光衣服,或者猛地撞向墙壁。给她喂药,是一场战斗。需要几个护士合作,先让她躺在地上,把药塞进她嘴里,然后灌水,用手捏她的喉结帮助吞咽。她常常被呛得剧烈咳嗽,水从嘴角流出来。起初,我非常反感这种看似“野蛮”的方式,但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护士们的无奈。在“生存”和“尊严”之间,为了前者,有时不得不暂时牺牲后者。
还有喜欢藏药或吃完偷偷抠喉吐掉的,护士会对她们格外“关照”,反复检查。最让我动容的,是那两个患有唐氏综合症伴精神分裂症的小矮人。她们都口歪眼斜,说不清话,走路蹒跚。其中年长的那位,已经50多岁,个头不足一米四,视力极差。你猜,是谁在一直照顾她?
不是护士,也不是病情较轻的我们,而是另一个比她稍微年轻些、患同样病症的小个子女生!她会牵着“姐姐”的手,帮她拿水杯,喂她吃药,给她打饭,甚至早上帮她穿衣服。这份 “弱者对弱者的守护” ,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演讲都更具震撼力。它完美地诠释了那句话:“因为我淋过雨,所以想为你撑一把伞。”在这片精神的荒原上,我看到了人性最本真、最坚韧的光辉,熠熠闪耀。
也许是因为躁狂期的能量无处释放,刚入院的前两周,我特别喜欢“多管闲事”。在这个50多人的群体里,我算是“强势群体”。我自觉承担起照顾弱者的责任。
比如,那位视力极弱、不会说话、又矮又瘦的50来岁女患者。有一次在厕所,她拉稀了,却没带纸,情急之下竟想用手指去擦。我当时正等在旁边,见状一个箭步冲上去阻止了她。我忍着不适,用手中的卫生纸仔细为她清理干净,帮她提好裤子,又搀着她到水池边,把她的手仔仔细细地洗干净。她浑浊的眼睛看不清我的模样,喉咙里也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无法表达感谢。
但那一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巨大的满足感和道德优越感。我在心里默默为自己加分:“看,即使在这里,我依然是一个善良的、能给别人带来温暖的好人!”这种价值感的确认,对于当时自尊低落到尘埃里的我来说,是一剂强效的强心针。

一个标准的治疗疗程是三个月。但因为我的恢复速度较快,也因为前夫和我爸频繁打电话来,强调孩子需要人照顾,在第29天,医生批准我出院了。
出院时,医生叮嘱我:每月必须回来面诊一次,拿足一个月的药量,回家按时服用,尽量避免刺激。
我带着厚厚的住院病历,成功办理了“慢性病”报销手续。这意味着,我以后每次拿药,可以报销80%的费用,每年的经济压力瞬间小了很多。而且,凭借这个“慢性病”证明,我每年还可以享受法定的病假,工资待遇不受影响。
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对我来说,简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感觉自己没有被社会抛弃,反而被一张温暖的安全网稳稳地托住了。我不是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我是一个被制度关怀和爱护着的公民。
带着这份新生的底气,我从出院那天起,就告诉自己:必须学会在前夫身边的生存之道。硬碰硬只会头破血流,我要学会“以柔克刚”,像水一样,看似柔弱,却能穿石。我要默默地蓄积力量,为了女儿,也为了自己,总有一天,我要彻底好起来,给她一个真正安全、温暖的港湾。
我开始学着温柔地说话,对于他的种种缺点选择视而不见。他不去做的事,我就自己默默地去做。不抱怨,不埋怨。在精神病院被世界“遗忘”的一个月,地球照样转动,太阳照常升起。
这让我深刻地领悟到:个体的生命在宏大的世界里,真的太渺小了。既然如此,何不选择留下那些快乐的记忆,果断删除那些不开心的片段,大胆地、勇敢地向前走呢?让生命,在每一个当下,都更“精神”一步!
以往,因为生病,家里的大事小情,我都没有发言权和决定权。在我坚持服药、每月复诊,状态日趋稳定后,我对家庭的贡献也开始被看见,被认可。我也开始敢于为自己争取权利了。过年时,我给自己买了一条价值上万的碎银子手链,那是送给自己新生的礼物。当年家里攒下的4万元存款,也第一次写上了我的名字(家里的钱以前都存在前夫一人名下)。这些在当时看似微小的经济独立,都在为一年后的那场决裂,默默地积攒着底气与资本。
(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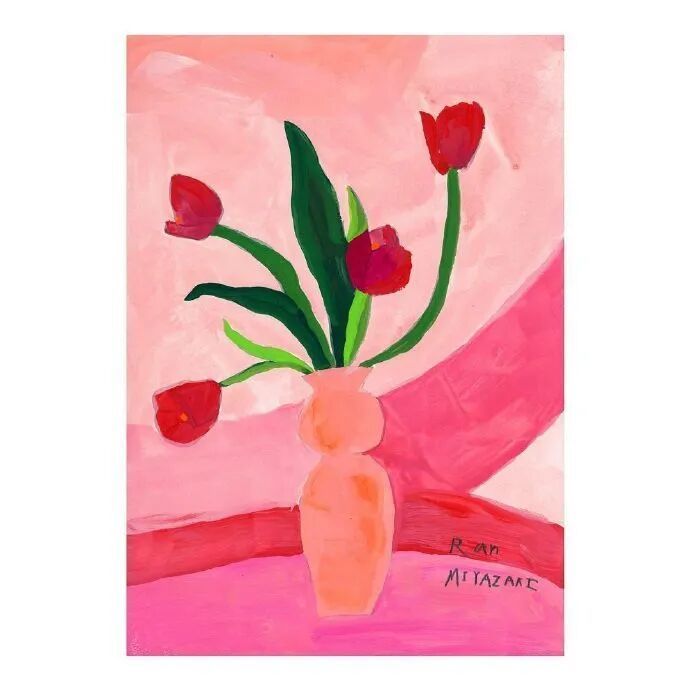
备注:每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情况都不一样,因此,文章中的分享,仅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