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痴情。
贾宝玉和林黛玉虽然也是出身豪门贵族,但也是如此,两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屋睡,一桌吃,平时走的近,交往不设防,最终出现了共读《西厢记》,共说“西厢话”的情况。
《西厢记》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书,也是一本引导少年男女冲破世俗的书,更是一部充满浪漫情话的书。
贾宝玉和林黛玉读完书后,在不同场合用书里的话进行交流,前后共有三次,每一次都有深意,最后一次最精彩。

第一次,大观园桃花树下,两人共读《西厢记》。
贾宝玉搬进大观园,百无聊赖,茗烟私下买了许多杂书供他阅看。
为了避人耳目,贾宝玉没有屋里偷读,而是独自一人到了桃花树下。
无巧不成书,就在他看得入迷时,林黛玉葬花路过。贾宝玉心虚,匆忙藏书之际,被林黛玉抓了个正着。无奈之下,贾宝玉只好将书借给林黛玉。
林黛玉天生敏慧,又值青春年少,看书之后爱不释手。读到兴头处,贾宝玉情不自禁地说出那句经典名句“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贾宝玉此语绝对不是冒犯,而是情难自禁,情窦初开之际借张生之言,说出了对黛玉最美的赞誉。
林黛玉听完后内心震动,但是少女之尊让她表面“微腮带怒,薄面含嗔”,但是羞涩也难以抵挡内心的波澜,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接收到如此直白的爱慕信号。
贾宝玉大惊失色之际,林黛玉又巧借苗而不秀、银样蜡枪头的说法让他释怀。
红学家蒋勋在《微尘众》中分析:“在礼教森严的贾府,《西厢记》成为宝玉情感启蒙的教科书。他需要借助张生的语言,才能表达对黛玉的爱慕。”
所以,一本禁书,几句经典,成为宝玉正式追求林黛玉的“开幕式”。
第二次,在林黛玉的卧室里。
贾宝玉中午到潇湘馆里串门,屋外听到林黛玉在吟说《西厢记》的词话。进屋过后,宝玉让丫环紫鹃前来敬茶,林黛玉假装生气让她去打洗脸水。紫鹃知道两人在弄小性儿,当即说宝玉远来是客,所以先去给宝玉倒茶。
贾宝玉高举之余,说道:“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
脂砚斋在此留下批注:真正无意忘情冲口而出之语。
意思是宝玉忘情后的心里话。但是这句话却太过于大胆,林黛玉当即哭着说道:“如今新兴的,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看了混帐书,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了爷们解闷的。”
林黛玉此举出乎意料之外,贾宝玉顿时手足无措。
贾宝玉不明白林黛玉为何会这样?其实很简单。林黛玉认为《西厢记》里的话是两人的专属,不能用在其他人身上,即使是紫鹃,也不能用。
红学家张锦池在《红楼梦考论》中强调了林黛玉的“情之洁”。他认为,黛玉的爱情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和纯粹性,她要求的是对方整个心灵的投入,不容丝毫的旁骛与亵渎。
所以,情至深处,容不得半粒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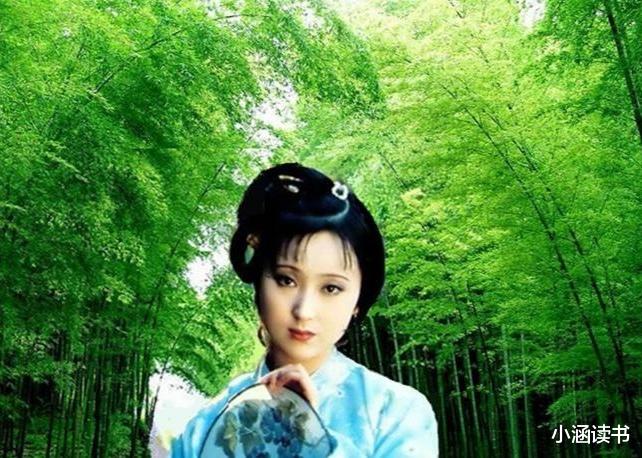
第三次,在林黛玉的房里。
林黛玉和薛宝钗的关系缓和之后,两人情同姐妹,这让贾宝玉大为不解。于是找到林黛玉,借用《西厢记》中话询问心中疑问,原文如下:
“那《闹简》上有一句说得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这‘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你说说我听听。”
宝玉问得很妙,他绝不是想问典故,而是想问林黛玉和薛宝钗什么时候冰释前嫌变成姐妹了。
这一问的精彩在于,从《西厢房》中儿女情长的局限里跳出来,不在把禁书看成一本普通的言情小说,而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为何说这一次比前两次都更精彩呢?
首先,话题升级了。从“我俩谈恋爱”变成了“咱俩聊聊你的人际关系”。说明他们的关系不再是封闭的小圈子,而是一起面对和讨论更复杂的世界了。
其次,默契到位了。大黛玉一听就懂,根本没生气,还笑着把前因后果都告诉了他。这说明他们之间的“脑电波”已经完全对上了,一个眼神就懂。
还有,书用活了。他们不再是死记硬背书里的情话,而是把书里的智慧当成一种“内部语言”,用来高效地交流更深刻的事情。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启祥在《红楼梦寻味录》中提出,“共读《西厢》是知音的序曲,而后来以《西厢》等为媒介的深谈,则是知音乐的正式奏响。他们谈论的已不仅是二人之情,更是对周遭人情的共同感知与评判。”
用大白话来说,前两次是两个孩子跟着禁书学谈恋爱,第三次是两个真正成熟的人,用独有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懂彼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