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破时,我的驸马杀了我,从城墙上扔了下去。
与我斗了一辈子的敌国质子,却接住了我的尸首。
他看着我的脸,神情颤抖,脸色惨白:
“宇文诺,你醒来看一看我。”
众人只知道,敌国的质子是条疯狗,和我斗得不死不休。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条疯狗年少时,也曾笑着当街拦下我的马,说他喜欢我,喜欢很久了。
一
闫信的匕首刺入我心口时,我还懵着。
我在十七岁那年嫁给闫信。
他是我的夫君,我的驸马。
这些年来,他对我虽不算浓情蜜意,可也是言听计从。
城破亡国时,也是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张皇逃命的闫信,拉了他一把。
我以为,这就该是亡命夫妻了。
却没想到,他从背后拔出匕首,毫不犹豫刺进了我的心窝。
灭顶巨痛中,我按向身侧刀柄的手无力垂下。
我连站都站不稳,跌跪在地,却竭力撑起头看他:
“为什么?”
是怎样的深仇大恨,要对自己的枕边人,自己的妻子下手?
闫信看着我,满目恐惧,拿着匕首的手都在抖。
他神情扭曲,颤抖着咬紧牙关:“嘉乐告诉我……你死了,叛军就能放她活着。”
嘉乐。
嘉乐公主,宇文嫣。
我的妹妹。温柔娇俏,美丽天真,乱世中的富贵花。
闫信少年时曾倾慕她。原来……他爱了她一辈子。
我仰头看自己的驸马。许久后,我轻声道:“可你知道吗……我有孕了。你的骨肉。”
闫信的神情空白了一瞬。
他满目难以置信:“不……不……我的孩子……”
他俯身靠近我,颤抖着手伸向我的小腹。
越来越近了。
就是此刻!
我尽了全力,暴起拔刀向他的脖颈。
可惜。
我已是强弩之末。刀偏了。
闫信躲开了。他的脸上被我划出一道狰狞伤口,血花四溅,穿过了眼睛,却没伤及命脉。
他在惨叫中,将我一脚踹飞了出去。
我,宇文诺,乱世帝京中大权在握的永宁公主,皇帝亲封的皇太女,就这样狼狈地摔在地上,没了声息。
魂灵游离躯壳,在半空看着这一幕,都觉啼笑皆非。
我的魂灵就这样看着闫信带着瞎了的一只眼睛,摇摇晃晃地拖走我的尸体,悬在城墙上。
他对着城下叛军喊话:“前朝皇太女已被我斩杀,尸首在此!求新皇饶我一命,饶嘉乐公主一命!”
最前面的叛军之首,摘下了自己脸上的巫蛊面具。
刀刻斧凿似的一张脸。野气又危险的俊美。
百夷质子,池钰。
他手中短刀,原本悠闲地抵在嘉乐颈间。
只是在看清城墙上朱色绣金蝶的纱罗宫装时,他的瞳孔骤缩,指节攥得比嘉乐的脸还惨白。
池钰哑声道:“宇文诺……死了?”
二
闫信的手一颤,朱色纱罗霎时从他手中滑脱。
我的尸首自城墙疾速坠下。
叛军中,池钰策马疾奔而出。
堪堪接住了我的尸首。
他的战马佩着青铜鎏金的当卢,神气地打了个响鼻。
池钰却面如金纸。
他盯着我的脸,怔忡盯了许久,才哑声道:“宇文诺,你醒来看一看我。”
帝京与百夷都知道,池钰和我,斗得不死不休。
他够疯。
而我够狠。
这些年来,有胜有负,没有谁能真的赢。
只此一役,我却是输得彻底。
池钰抱着我的尸首脸色苍白周身颤抖,片刻后嘶哑地笑了一声,话尾全是讽刺:
“宇文诺,这就是你不计代价护着的臣民,无论如何也要嫁的驸马……值吗?”
他倾身靠近我的脸,额头相抵,呢喃了句什么。
我想凑上前去听。
魂灵却在一刹那如同上了锁链,动弹不得。
我仿佛跌入一片虚无,五感皆失。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便不知道了。
我似乎混沌良久。又似乎只是弹指间。
再醒来时,是被宫人的耳边私语叫醒的:
“殿下,醒醒,陛下在问你!”
我霍然睁眼。
然后本能地一偏头,躲开了凌空砸向我面门的砚台。
下一刻,父皇威严震怒的声音响起:
“听训也能睡着,不愧是你母后生出来的下贱东西!”
三
我抬起头,看到了父皇盯着我、满是厌恶的脸。
腿比心软得快。我在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端端正正跪好叩首:“父皇恕罪!”
膝上传来锥心剧痛。
牵扯着周身伤口。
我眼前一黑,险些痛晕过去。
我咬紧牙关,盯着脚下的紫花御石地面,飞快思索——
父皇的脸,比亡国时年轻了一些。
我受伤了——刚刚不是睡过去了,而是疼晕过去了。
可我自小挨打的时候不计其数……这是今夕何夕?
父皇森然道:“你可知错!”
我咬着牙,垂着头沉默。
我要先知道自己又犯了什么错,才好决定要不要认。
丽妃侍立在父皇身侧,声音颤颤响起:“永宁这说的是什么疯话……百夷的圣坛都被屠了,所有精通巫蛊术之人被杀了个干净,唯一的皇子在我朝为质,如何能制作人牲?如何卷土重来?”
百夷。
人牲。
我心下一沉。难怪父皇疯了似的打我。
我重生了,回到了亡国的开端。
就是在这一年,我发现了边境大批百姓离奇失踪,疑似被做成了百夷的巫蛊人牲。
可我将此事禀报父皇时,话都没说完,他就疯了似的砸了半个御书房。
——父皇畏惧百夷。
他曾因忌惮百夷的巫蛊之术,大肆屠戮百夷,歼灭王室,毁尽了百夷巫蛊术的根基。
可“百夷”二字,也因此成了父皇的心病——没有哪个屠过城的人,能在长夜中高枕安睡。
他掐住我的脖子,将我生生从地上提了起来:“你是来吓唬朕的?威胁朕的?替百夷,替你那小情儿来报复朕,是不是!!”
父皇盯着我的眼睛,像嗜血的兽类:“你心里始终有他,对吗?”
我脸色涨得青紫,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只能艰难摇头。
我知道父皇说的是谁。
父皇知道,也只有父皇知道……百夷质子,池钰,他的命,是我几乎赔上自己的命保下来的。
父皇松了手,却一脚将我从御书房踹了出去。
“滚!!再提一句百夷,朕就送你和你那个不知廉耻的母后团聚!”
我一身血污,狼狈地摔在地上,呛咳不止。
宫人们低着头不住地抖,知道我此刻颜面尽失,不敢看,更不敢上前来扶。
一双缀宝珠的绣鞋停在我脸前。
嘉乐娇娇软软的声音响起:“姐姐,怎么又惹父皇生气啦?”
四
嘉乐笑眼弯弯,满眼的幸灾乐祸。
“若不是我弟弟早夭,想也轮不到你做储君,”嘉乐鄙夷道,“这太女之位,是我不要了才让给你的……你还真把自己当未来的一国之主啦?真是贻笑大方!”
她嗤笑一声,宝珠摇曳的绣鞋从我手上踩了过去,自顾自进了殿。
我爬起来一步一挪地向外走时,回头看了一眼。
嘉乐正伏在父皇膝头撒娇,拍他的胸口顺气。
而我恍惚想着,这样的伤……前世我躺了多久来着?
父皇不肯信,我却是知道的,要不了多久,百夷就会从边境寸寸逼近,破一城屠一城,最终挟持嘉乐公主,大破皇城,血债血偿。
我闭了闭眼,竭力让自己不去想那时血流成河、百姓哭喊的惨状。
再一睁眼,我却险些撞上一个人。
我抬眸看到那人的脸,动作一滞。
正华年的百夷质子池钰,有着近乎妖异的锋利颜色。
前世就是他屠了皇城灭了国,面无表情将一个个大臣的头颅悬在城门上放干了血。
那样冷、那样疯的一个人。
而今他打量着我一身的伤,唇角噙着一抹笑:“公主殿下,多管闲事不好玩,对吧?”
我看着池钰,恍惚想到的却是他在乱军中接住我的尸首,苍白着脸的样子。
我死了……他不应该开心吗?
我问:“你恨我吗?”
池钰盯我半晌,忽然笑了。
“不恨啊,”他轻笑,声音里有绵软丝线似的杀意,“我喜欢你,从我在帝京见到你第一眼就喜欢你,即使你父皇屠尽了我的家人师友,长钉寸寸凿进我的经脉——我也还是喜欢你。宇文诺,我这样说,你相信吗?”
五
池钰在少年时,的确说过他喜欢我。
可如今不是少年时了。
如今他眼中已没了飞扬的神采,只有泠泠的森然。
他的手腕脚腕处皆有暗红色的符篆蜿蜒,时有寒芒一闪,露出嵌进了血肉的银钉。
那是我求父皇,亲命术士打进去的禁制。
我不忍再看那些伤口。那时他得有多疼。
“你后悔吗,宇文诺?”池钰轻声道,“我国破家亡,最绝望的时候,想见你一面,却听说你要和旁人成亲了,将我弃如敝履。
“你对我唯一的回应,就是命人在我身上钉下禁制,变成一个废人……此后派人密切监视,生怕我要造反复国。宇文诺,这样对我,你后悔过吗?”
我后悔吗?
我想起腿骨都被生生打断的锥心痛楚,却还是咬牙扯住父皇的战袍一角,不准父皇去杀昏迷的池钰,声声哀求,求您放过他,父皇,儿臣知晓百夷秘术能封禁他的巫蛊之能,求您放过他,让他活着。
——让他活着。
可如果让他活着会在日后死伤更多的无辜,我不知道自己后不后悔。
“我父皇欠你,欠百夷无数性命,”我哑声道,“若你要杀他,我不拦着。”
“你恨我、要杀我,我也没有二话。只是我中原的百姓无辜,”我喉间发干,“父皇的孽债,不该让他们去还。我不能……眼看着他们被活生生做成巫蛊的人牲。”
池钰盯着我,面无表情。
片刻后他冷冷一笑:“公主殿下还真是心系众生。三两城池、千百庶民罢了,你妹妹可比你大方得多。”
六
我心头一骇。
嘉乐。
人牲的事和嘉乐有关系?
“不该管的不要管,否则想要殿下死的,可不止是我百夷。”
池钰靠近我耳边,森然道:
“——到时候,我想亲手杀了你,怕是都抢不过旁人。”
他瞥一眼我身上渗血伤口,讽笑一声,扬长而去。
我怔在当场。
直到恍恍惚惚回了东宫,我还在思索。
前世我不计代价地防着百夷屠戮臣民,却独独没想过怀疑身边人。
最终却也死于身边人。
我的驸马杀了我,匕首穿心。
“殿下可是还在疼?”闫信的声音猝不及防在耳边炸响,“这伤得也太重了些……”
我只觉得毛骨悚然头皮发麻,霎时暴起,掐住他的脖颈:“你竟敢!”
闫信被我扑得摔在地上。
托盘瓶盏砸落一地,他涨紫着面孔挣扎,说不出话。
闻声赶来的宫人骇然:“殿下……驸马是来为殿下看伤的……可是冲撞了殿下?”
我脑中一冷,逐渐平静下来。
我已经重生了,回到了很久以前。此时他并未要杀我。
闫信的面孔已经涨出了青灰色,几乎现出死气。
我松开他,低声道:“做了个噩梦魇着了,一时失态。”
闫信连连呛咳,匀过气后却张皇跪下,眼都不敢抬:“是臣失职。臣这就为殿下开个安神的方子……”
卑躬屈膝,如我在父皇面前一般。
这扭曲的权势和皇室。
我挥退宫人,盯着地上瑟瑟惶恐的闫信,突然道:“当初逼你娶我,你怨不怨?”
七
想要做储君,我和池钰便注定陌路。
父皇一贯多疑。我需要一个驸马。
我就是在那当口遇见的闫信。
彼时我路过殿外,见到一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小太医正要被杖杀。
他初见嘉乐公主,惊为天人,看痴了。
冒犯了贵人,当杀。
我拦下了行刑的人。问他:“你想活吗?”
想活,就得做我的驸马。一生一世,与一个不喜欢的人日夜相守。
我喃喃道:“那时年纪小,以为无情也能做夫妻。”
我以为,没有情,有义也可以。
天下夫妻,真正的有情人又有多少呢?
可我忘记了,恩爱夫妻尚能反目成仇,更遑论闫信从未爱过我。朝夕相处,仰我鼻息,反而更易心生怨怼。
所以城破兵败,他暗算我时,没有一分犹豫。
闫信跪伏在地,磕磕绊绊道:“臣……臣不敢怨……”
他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笑了。
幸好此刻他还算对我诚实。不敢怨,不是不怨。
纵使我救了他的命,他也始终记恨我断了他的姻缘。
我亦不能再放任会暗算我的人在身边。
“毕竟夫妻一场。你若安分,我自会保你下半生衣食无忧,”我说,命宫人进来,“即日起,驸马禁足东厢静室,非死不得出。”
闫信骇然抬头。
这是要将他困死一辈子。
他张皇得红了眼:“殿下,臣只是如实作答,何至于此……”
我打断他:“你是想现在死,还是安安静静在我东宫的内殿里老死?”
蝼蚁如何质疑肉食者。
就如同我早早学会了,不再质问父皇。
闫信再没了话,无力瘫坐在地,被宫人搀了出去。
我召来暗卫:“派两个人盯紧他。如有异动,随时可杀。”
“再派个人在宫中扮成我养伤,闭门谢客。
“其他人,随我潜去边境几城。我要亲自看看是怎么回事。”
前世,我因伤势严重在府中躺了许久,这件事是交给闫信去办的。
结果那一次,我悉心培养的暗卫尽数殒命,只有闫信一身是血地爬了回来,却浑浑噩噩晕了许久,对那些天发生了什么,一问三不知。
今世我不信他了。
我要自己去看看,成百上千好端端的百姓,怎么就无声无息地失踪了。
八
边境小城中,竟是嘉乐在施粥。
面黄肌瘦的贫民一边狼吞虎咽地喝粥,一边赞嘉乐公主爱护百姓,是女菩萨下凡。
我盯着城中粥铺:“她是这样心慈的人吗?”
“嘉乐公主胭脂钗裙的奢华程度,陛下若过问,怕是都要咋舌,”暗卫回禀,“她时常向皇帝抱怨手头不宽裕,不像是有银钱做善事的样子。”
当月初五子时,响起了悠扬得有些诡谲的笛声。
所有在粥铺喝过粥的贫民,脸上扬起了一模一样的微笑。
他们排着队走出城外,已有一支百夷车队在等候。
笛声中,这些贫民乖觉走入等待的百夷车队,如同刚做好的木偶被装进了匣子。
我心口一寒。
这是已经炼成的人牲。
“五百个人,这些还不止,算送你的,”嘉乐在一旁含笑看着,红唇勾起,“我要的东西呢?”
立在她身侧吹笛的人,正是池钰。
他看着这些行尸走肉一般的贫民,神色淡淡。
领着车队的百夷人向嘉乐奉上一个精致的匣子。
“百夷特制的红颜胭脂,千金一钱,嘉乐公主的妆奁中倒是从没缺过,”池钰瞥了一眼,“您出手这样大方,朝中不过问?”
嘉乐的笑容僵了一僵。
我在查百夷。这不是什么秘密。
“这天下到底是我父皇的天下,还不是她宇文诺的!”想到我,嘉乐脸上涌上一丝厌恶,“既然早晚要传给宇文诺,我现在败一败又怎么了?”
我心头涌上悚然。
她尽可以挥霍钗裙锦绣,可百姓不是用来交易的银钱。
百夷领队向嘉乐奉承道:“若日后继位的是殿下您,我们的生意会好做得多。”
嘉乐嗤笑一声,摆摆手:“我可不要那治国的苦差。
“呕心沥血战战兢兢,转头还可能被父皇和言官骂得狗血淋头……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交给宇文诺就好了。”
她施施然翻拣着匣子里精致的胭脂:“父皇那边我会压下来的。上次不知死活去给宇文诺报信的知县,我已将他一家老小都埋了……就是可惜,慢了一步没拦住消息,让宇文诺那狗鼻子嗅到腥气了。”
我不觉握紧了拳。
难怪我顺着消息去查,所有相关的人都死无对证,我还当是百夷在灭口。
——原来是嘉乐。
我打量着此处的局势。
这些百姓或许已经成了池钰的人牲,会听令暴动杀人,无知无痛无惧。
五百多巫蛊人牲,加上一支不知底细的车队,嘉乐身边也有好手。
我向暗卫打了个手势。
先撤,从长计议。
“我们走不了了,殿下,”暗卫看着池钰的方向,脸色发白,“他发现我们了。”
百夷领队与嘉乐交谈其间,笛声不知何时已停了。
池钰看向我的方向,冰冷声音带着杀意:“不是在东宫养伤?太女殿下,这心散得太远了吧。”
九
五百人牲齐齐随着他转向我们。
老幼妇孺,皆是如出一辙的木然微笑,颇为可怖。
这一刻,我却恍惚想起,前世所有暗卫,在此死无全尸。
不至于。以她们的身手,最多两败俱伤,何至于全军覆没?
——可带她们来查探的是闫信。此情此景,闫信定是吓尿了裤子。
他会如何做?
电光石火间,前世今生的线索,忽然就串在了一起。
我咬紧了牙。
他会……他会出卖我所有的暗卫,换取嘉乐的信任,最后自己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保全一命。
我将牙咬得咯咯作响:“是我失察。”
没有发现闫信早有异心。
更没有想到,嘉乐身为公主,会为几盒胭脂卖了相信她的百姓。
嘉乐听到我来了,原本喜悦的脸沉了下来。
“姐姐,你开心了,是不是?”她轻声道,“拿了我的把柄,你要去向父皇告状了,是不是?”
我从藏身处走出来。
我说:“被你卖掉的是你的臣民。他们相信皇室,相信我们。”
“父皇又不在,你装贤德给谁看?”嘉乐的鼻子厌恶地皱了起来,“少用这些圣贤道理压我。”
她说:“你便是这天下最爱世人的公主,父皇就喜欢你吗?别忘了,你有个与人私通的娘——啊!”
话音未落,嘉乐一声惊叫。
她身边的好手,险而又险地为她挡掉一枚暗器。
嘉乐的鬓发有些乱,狼狈又恼怒道:“池钰,你是死的吗!宇文诺她暗算我,你为何不护着我!”
“她暗算的又不是我,”池钰凉凉道,目光扫过我的脸,忽地一笑,“不对……她早已暗算过我了。”
“你与她有旧怨,她又处处针对百夷,你也想杀了她的,是不是?”嘉乐急切道,“我们一起杀了她——毁尸灭迹,就只当她失踪了,行不行?”
十
我看着嘉乐毫无愧色地筹谋,指尖冰凉。
暗卫们不动声色地握紧了兵刃。
“嘉乐,你我从来没有手足之情,我也不提这个,”我说,“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卖国?凭我储君的身份,就可依国法治你。”
嘉乐毫不畏惧,反而咯咯笑起来。
她说:“你不敢。
“就算事情败露又如何?无论我是杀了你,还是卖国……父皇至多罚我一顿,禁足几个月也就罢了。
“——可是姐姐,若你杀了我,无论什么缘由,父皇一定会要你的命。”
想到父皇,我心底一寒。
她说得没错。
父皇从来不是公允的人。偏偏嘉乐,又是父皇的心头肉。
嘉乐睥睨着我,一脸志在必得:“没办法呀……父皇疼爱我,我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姐姐,别怪我,要怪就怪自己是贱人所生——”
我攥在身后握成拳的手一松。
嘉乐脚下,刚刚被挡掉的暗器突然炸开。滚滚浓烟升腾上来,带着刺鼻的硫磺气息。
“我的脸!!”嘉乐尖叫道,“我的脸伤了——”
对面视线一时受阻,骚乱之中,我和暗卫拔足狂奔。
“机关不错,”我向身边名为十七的暗卫道,“还有毁容的功效?”
“原本只是毒烟筒,让人暂时无法视物的,”十七侧脸清冷,淡淡道,“嘉乐公主离得太近了,碎片溅到脸上,实是无心插柳。”
我大笑出声。
“别笑了,”十七神情紧绷,“殿下身上好重的血腥气……伤口是不是裂开了?您的腿!”
十一
暂避的驿站厢房内,暗卫撕开了我裹在腿上的纱布,鲜血和未长好的皮肉粘连。
“您腿上本就有旧伤,”暗卫们神情凝重,“如今伤口崩裂,万一长不好……”
腿就废了。我知道。
“我去找车,”十七咬牙道,“马车,运蔬果的驴车,哪怕是伪装成出殡的灵车……殿下不宜再赶路了。”
“嘉乐和池钰,不会让我有机会回帝京的,”我说,“若是他二人联手……你们怕真的要扶我灵柩回去了。”
自小贴身护着我的十五,踟蹰半晌道:“您和百夷质子的年少情分,不作数了嘛?”
我没否认,却也没点头。
少年时的喜欢能作多少数呢?前世我死的时候,他痛得发抖,可我活着的时候,他也没留过手。
“我不能用这个去赌。”我说。
我背后还有数十个暗卫性命,还有朝中半数盘根错节的暗子。那是母后留给我的东西,比我的感情和儿女心事来得珍贵。
我垂眸想了想:“明日起,你们所有人离开我身边,另有任务。”
“殿下您疯了?”十七脸色煞白,“便是我等拼上全部性命,难道不能护送殿下安全回帝京?莫说五百人牲,就是成千上万个——”
“也不及一个昏君可怕,”我说,“你们拼着死伤过半,护送我回帝京,然后呢?”
父皇就会处置嘉乐?
有丽妃求情,父皇宠爱袒护,嘉乐死不了。
“我们分头,”我说,“嘉乐一旦发现我的踪迹,定会不顾一切地抓我。十七,峡关是回帝京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孤身能逃的最远距离。你带人在此设伏,非我号令,不得擅动——无论你们看到什么。”
“十二,你拿我令牌,去周边几城的布政使司,严查失踪又去而复返的人,集中关押。此举未必能挽大厦将倾,但是能引开池钰——嘉乐没脑子,只会追着我跑,可池钰没那么蠢。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人牲放出来。”
“十五擅乔装隐匿,带着剩下的人,潜去百夷。我要你们去找一个人。”
所有暗卫听我派遣四散。
十七走在最后,临走时,回头看了我一眼。
她年岁最长,性子最冷,是我母后养大的,我小的时候叫她姐姐。
“娘娘若是还在,看到殿下这样受苦,会哭的,”她说,“您小的时候也是金枝玉叶,记得吗?”
我将烈酒从流血的伤口上浇下去,一声未哼。
“不记得了,你也忘了吧。”
十二
我是在峡关数十里外被嘉乐逮到的。
如我所料,嘉乐一发现我的踪迹,便一门心思追着我来了。
可我低估了自己的伤势。
还未到峡关,她身边的高手便已咬上了我,紧追不舍。
更可怖的是——
前方本该空无一人的路上,一个又一个人牲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他们咧着嘴,齐齐拉着手成一堵人墙,生生拦下了狂奔的马。
马车翻倒。
我狼狈地从里面滚出来,看到了前方不远处,冷眼盯着我的池钰。
我的心狠狠一沉。
嘉乐大笑:“想不到吧,姐姐?池钰虽有要事,可他到底放心不下我,提前赶了回来。”
嘉乐走近我,一脚踩在我的伤腿上。
她撩起面纱:“宇文诺,你这贱人生的贱种,下手可真狠哪,竟敢把我的脸伤成这样。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才好呢?”
她的鞋尖在我的伤口上碾来碾去,面容扭曲:
“若痛快杀了你,真是难解我心头之恨。”
嘉乐命人将我的双手绑了,拴在马后拖行。
她将马鞭抽下去,尖声道:“快些,再快些!”
我被疾奔的马带倒,狼狈得爬都爬不起来,不止伤口,周身都被磨得血肉模糊。
嘉乐咯咯直笑,花枝乱颤。
而我在飞速后退的风景里看到了池钰。他泠泠看着前方,面无表情,仿佛事不关己。
当夜,伤口溃烂,我发起了高烧。
意识模糊间,我却见到了年少时的池钰,将我悄悄带到无人的桃花林,花树下拴着一匹胭脂色的马。
他的双眼亮得如同星子:“这是我辗转许久才寻到的,喜欢吗?”
那匹马叫丹璃,是我年少时最喜欢的一匹马。
后来我当着池钰的面,一刀捅进了它的咽喉。
我说:“从此你我桥归桥路归路,各不相干了。——池钰,别挡我的路。”
丹璃四蹄挣扎,发出濒死嘶鸣。
我在噩梦中骇然惊醒,腿痛得钻心,额上冷汗涔涔。
此处是夜雨中暂避的山洞。
我的脚踝,正被池钰握在手里。
他敛眉眯起眼:“你的腿断过……什么时候的事?”
十三
嘉乐也在一旁避雨,在火堆旁,烘烤自己沾湿的发梢和裙摆。
“你不知道?”她施施然道,“这贱人的腿骨早年断过,算半个残废了。好像就是百夷大战的时候……她为了护着一个百夷的小情儿,拖着父皇的战袍,腿被打断了都不肯松手呢。”
我眼见着池钰的脸霎时惨白。
嘉乐并未发现,心不在焉地咯咯笑:“那次之后,她就再也骑不了马了……可怜她随父皇鞍前马后才学会的精湛骑术,就这么废掉了。
“偏她还不死心,还成日里命人牵着她那匹胭脂马去散心,生怕那畜生闷坏了。——我看得心烦,就给那畜生灌了点东西。”
火苗摇晃,衬得池钰的脸明明灭灭。
他背对着嘉乐,神色惨白,近乎带了森然鬼气,声音里有不易察觉嘶哑:“后来呢?”
嘉乐无知无觉,托腮想了想:
“后来?死了吧。那可是剧毒来着,那畜生不死也会活活疼疯的——”
而我余光瞥见,原本在角落里木偶似坐着的人牲,不知何时无声无息地站了起来。
他们团团围在了嘉乐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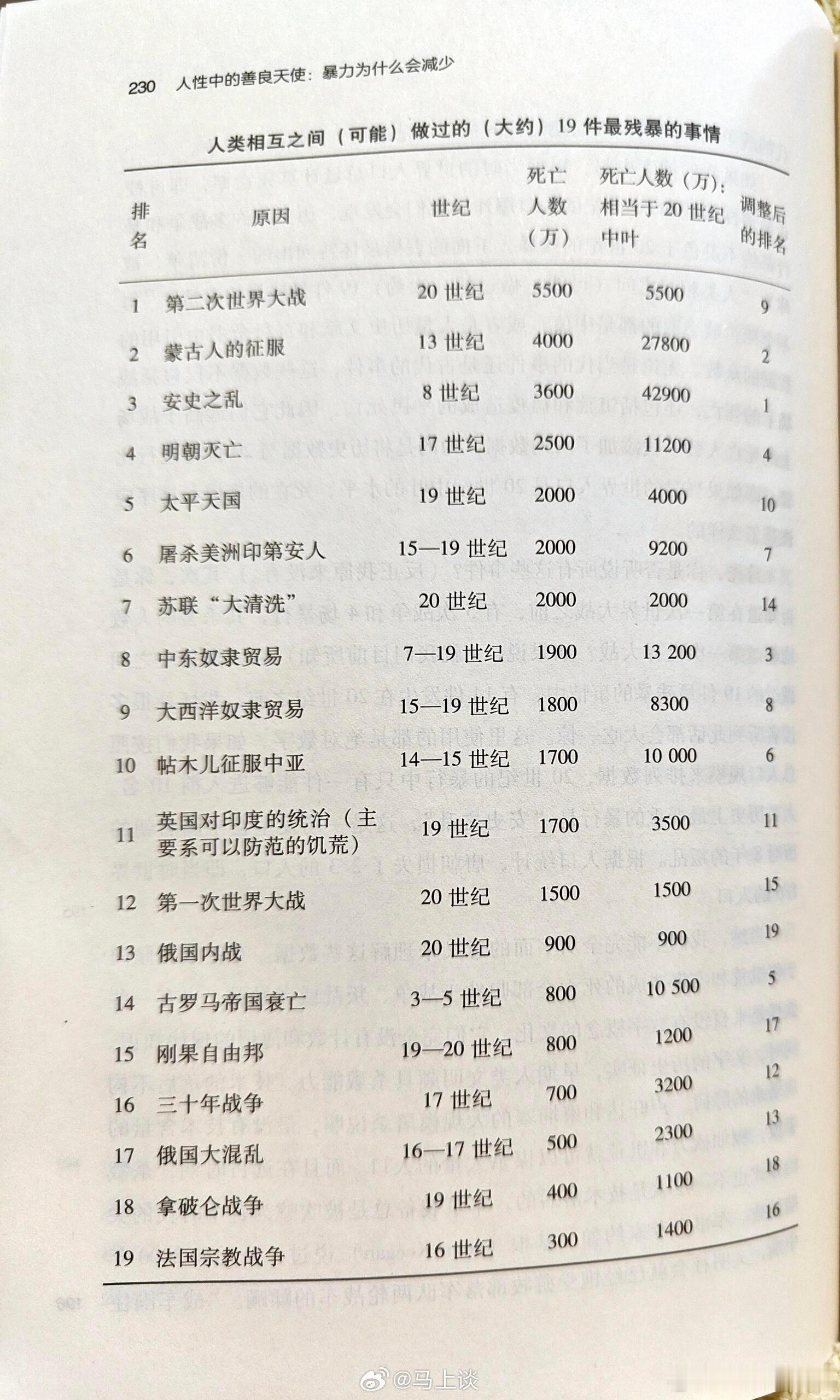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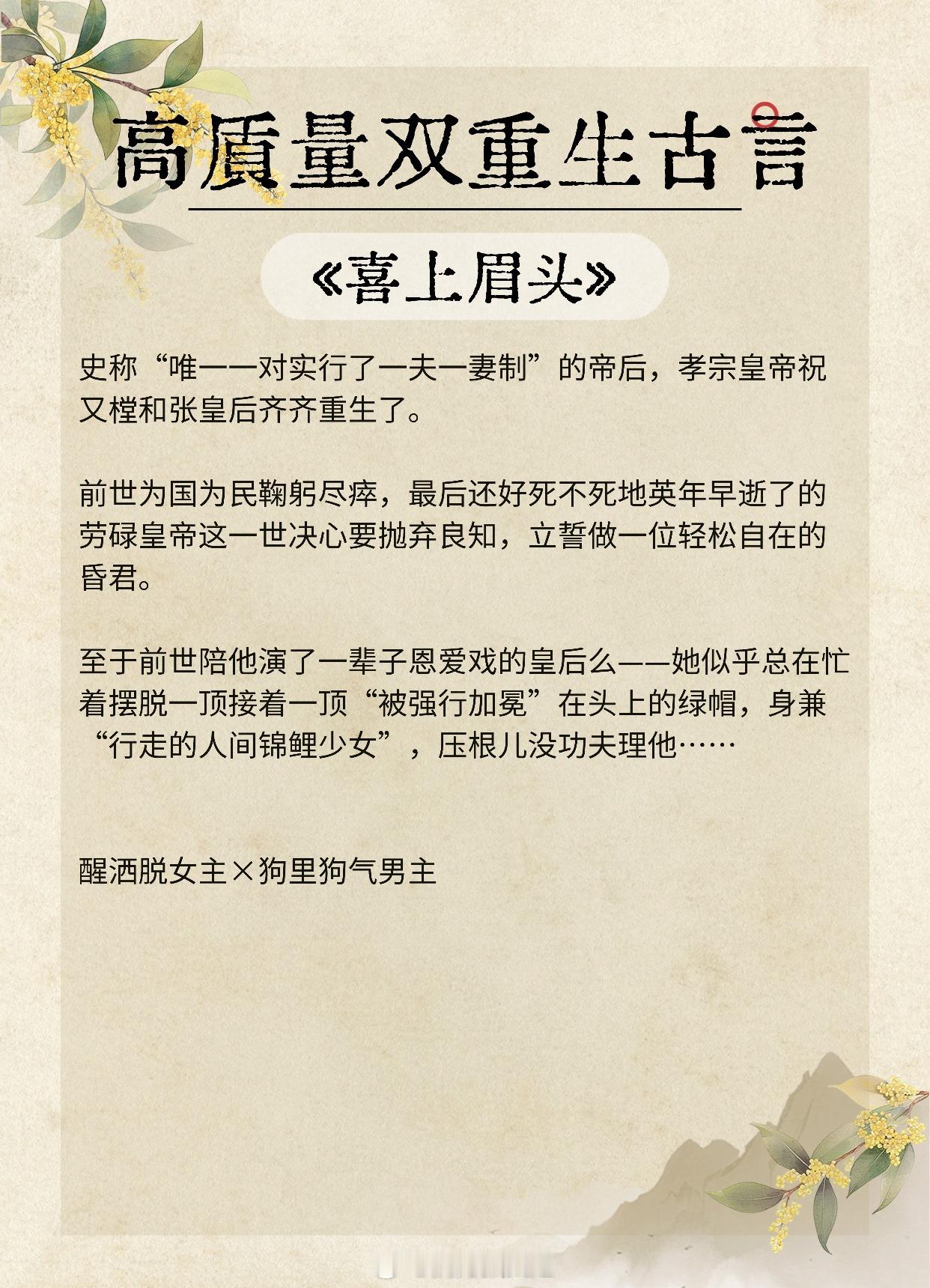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