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楚风语语
秋景暮晚,寒露为霜。
当第一缕薄霜悄然覆上草木,霜降,就这样带着岁月的清寒,踏入了季节的门槛。它是秋天的最后一次回眸,是冬的序曲前的低吟浅唱。
霜降,这个名字念在唇齿间,便自有一股寒气。它不是“白露”,那还带着少女晨泪般的清柔;也不是“寒露”,只是预告着凉的消息。它是“降”,是“肃”,是来自高天的一种判决,一种执行。是天地间那股蒸腾的、活跃的阳气,终于收敛到了极处,而阴冷的、沉静的寒气,开始君临大地。
“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一个“凝”字,道尽了此中神髓。风似乎凝住了,不再那般飘忽不定;水也凝住了,溪流变得分外瘦削清浅;连时光,也仿佛在这寒意的浸透下,流速迟缓了下来,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果冻般的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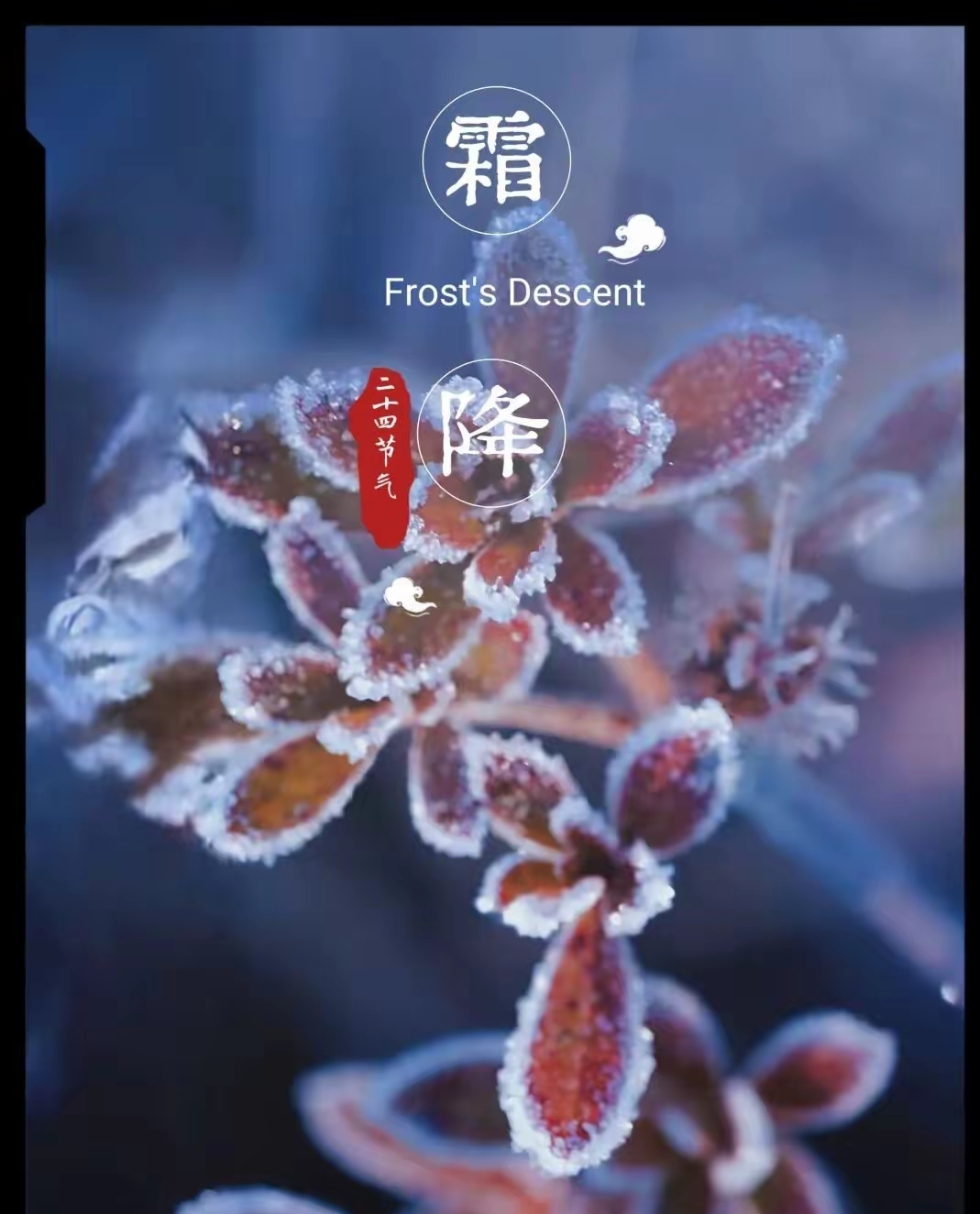 01
01《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凶猛的豺狼为过冬储食,开始大量捕获猎物并把吃不完的猎物摆起来,在古人看来,就像是在“祭兽”。二候草木黄落,气候逐渐寒冷,花草、树叶枯黄掉落。三候蜇虫咸俯,“蛰虫咸俯”是什么意思呢? “咸,皆也;俯,垂头也。此时寒气肃凛,虫皆垂头而不食矣。”蛰虫在洞中不动不食,垂下头来进入冬眠状态中。此时的大自然,是一种寂静的美。
轻霜落下,俯仰皆寂静。霜降,不像“立春”那样,带着些初来乍到的腼腆与生机;也不似“夏至”,那般热烈到不留余地的坦荡。霜降是幽峭的,是内敛的,是一位从水墨画最深最远的背景里,缓缓走来的、眉目清冷的隐士。他一来,天地间那场喧哗了整季的秋的辩论,便霎时安静了。不是戛然而止,而是声音渐渐地、渐渐地沉了下去,像一滴浓墨落进清水中,初时还有丝丝缕缕的游走,终至于完全的、化不开的静默。

秋深了。时间踩着它无声的疾步,走过柳暗花明,走过山关万里,走到晚秋的简净与沉敛处。黄叶翻飞,树木渐渐露出风骨。锐利的风,有横扫一切的气势。
霜落的脚步,原是听不见的。直到某日清晨推窗,一股清冽如薄刃的风迎面而来,人不自觉地一凛,才恍然发觉,时节已深了。这风里带着一种干净的、属于霜与露的气息,与夏日那黏腻湿重的暖意全然不同。它拂过面颊,并不使人觉得萧索,反倒像一种郑重的提醒,告诉你那真正值得眷恋的温暖,正在人间烟火里,静静地升腾起来。
 02
02风掠过发梢,带来凛冽的清甜。我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霜花,在掌心化作晶莹的水珠,这是大地赠给天空的礼物。霜降从来不是萧瑟的注脚,而是生命在沉潜中写就的诗。银箔般的霜色覆满枝头,是岁月为万物镀上的智慧;清冽的空气涤荡心尘,是时光教会我们在寂静中聆听成长。
风掠过山谷,把松涛译成梵文。野径上铺满的不是落叶,是王维诗里未扫的禅意。当暮色漫过第七十九道山梁,归鸟驮着最后一缕暖光,将整个秋天的重量,都压在枝桠微微颤抖的叹息里。

在这个霜色浸染的清晨,银杏叶如金箔飘坠,铺满小城街角。那不是凋零,是时光在低语,是岁月在作别。一片叶子的落下,带走的不只是枝头的温度,还有整座城市未曾说出口的眷恋。在凋零处看见新生,在寒冷里拥抱温暖,在时光的褶皱中,拾起那些被霜花照亮的永恒。此刻的霜,是岁月捎来的信息,提醒我们,该收拾心情,备好行囊,以最美的姿态,等待寒冬的到来,期待着春天的归来。当春风融尽残雪,我们会记得这个清晨,那些被霜吻过的日子,终将在记忆里闪着珍珠般的光。
 03
03阳光,也失了夏日的骄纵。它变得分外地客气,斜斜地照过来,像一层薄薄的、金黄色的蜜,涂在斑驳的墙壁上,铺在零落的落叶间。看那街角卖烤红薯的摊子,那热腾腾的、带着焦糖香气的白雾,在这蜜色的光里缠绕、升腾,便觉着那暖意不是虚的,是看得见,也闻得着的。那红薯捧在手里,是一块沉甸甸的、滚烫的慰藉;掰开来,里面是金黄而糯软的芯子,一口下去,那甜与暖便从喉间一直落到心里去,将那一丝从外面带来的寒气,熨帖得服服服帖帖。这大约便是人间烟火最初的模样了。
霜降,是草木摇落的一地清凉。这时候的草木,是最懂事的。它们不再争抢阳光的恩宠,只是默默地、将自己夏日里积蓄的、那一点过于饱满的生命的汁液,悄悄地收回脉络的深处,藏进泥土之下的梦里。于是,叶子便黄了,便红了,那是一种殉道者般的、悲壮而静美的颜色。
走在一条落满梧桐叶的小径上,脚下是沙沙的、脆裂的声响,像是时光本身在脚下叹息。每一片叶子,都带着一整个夏天的记忆,那些暴雨的洗礼,那些烈日的灼烧,那些月夜的静谧,此刻都凝成了叶脉间一道道错综的、金色的掌纹。它们飘然而下,不是死亡,而是一种庄严的交付,将一身的热闹,还给沉寂的大地。
这景象,总让我无端地想起李商隐的诗句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那是一种何等的、耽于颓唐之美的境界!他不要看那接天莲叶的无穷碧色,偏要守着那一池衰败的枯荷,在寒冷的秋夜里,听雨点敲打在上面的、清越而寂寞的声响。这霜降时节的万物,便都成了这样一池“枯荷”,它们褪去了所有浮华的装饰,只留下筋骨,在愈来愈薄的日光下,预备着领受那一场宿命般的、名为“霜”的加冕。这“霜”,便是我心里顶顶奇绝的一种物事了。它不是雪,那般铺天盖地,以势压人;它也不是露,只在清晨怯怯地逗留片刻。
霜是夜的精灵,是寒气的笔墨,趁着万物沉睡,于无声无息间,便完成了它对大地的写生。翌日清晨推窗望去,瓦上,草尖,田垄的土块上,都敷着一层匀匀的、松软的白色。那不是单纯的白色,细看时,竟有着珍珠般柔和而又清冽的光泽。它让粗糙的世界变得精致,让纷杂的颜色归于统一的、高级的灰白调子。脚下的草,踩上去不再是绵软的,而是发出一种极细微的、如同碎玉的声响。这时的空气,吸进肺里是清甜的,带着一种薄荷的凉意,却又无比地干净,仿佛能将人五脏六腑里的浊气都涤荡一空。

而最妙的,还是在将夜未夜的黄昏。天色是那种混沌的、青灰里透着些微紫的调子,远处的楼宇已亮起三三两两、温润的灯火。这时候,若在屋里,便听得见邻居家厨房里传来的、隐约的炒菜声,嗅得到那随着油烟机飘出的、带着葱姜爆香的家常气味。这气味,比任何高妙的音乐都更能抚慰人心。它告诉你,在这广大的、渐寒的天地间,有无数个小小的单元,正点起灯,生起火,经营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热乎乎的悲欢。
于是,自己也便忍不住想动手做一餐饭。不必是山珍海味,只一碗清粥,一碟小菜便好。看那米粒在锅中慢慢地翻滚,溢出质朴的香气;看那水汽氤氲着,模糊了厨房的玻璃窗。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外头或许有风在呼啸,有霜在凝结,但这一方小小的天地里,却只有安稳的、属于“此刻”的温暖。这温暖,是自己给予自己的,它不假外求,因而也格外地牢靠。
 04
04夜来,霜,大约已经悄悄地降下来了吧,正一丝丝地,将它那冰冷的、洁净的吻,印在每一片安睡的叶子上,印在每一寸毫无防备的土地上。它要将这世界,暂时地封存起来,像一个美丽的、透明的蛹,里面睡着的是一个关于春天的、遥远的梦。
霜落无声,却压弯了秋的脊背。草木低头,虫鸣渐歇,天地间弥漫着一股肃杀之气。这不是悲,而是静;不是终结,而是沉淀。万物在寒凉中收拢羽翼,把喧嚣还给过往,把热烈藏进根脉。人亦如此。走过半生,才懂得繁华终将褪去,喧嚣终会归于平静。那些曾让你辗转难眠的争执,让你心潮澎湃的追逐,终究会在某个清冷的月下,化作一声轻叹,随风散去。
月光如霜,静静流淌在青石板上。那光不暖,却清亮得刺骨,照见墙角斑驳的苔痕,照见屋檐下悬着的旧灯笼,也照见了谁家窗前,一剪沉默的身影。雨巷空寂,仿佛千年前的丁香姑娘仍未走远,只是把心事藏进了更深的夜。
夜,愈发地深了。我仿佛能感觉到,那无形的、精纯的霜华,正在窗外静静地编织着它的素锦。它会使草尖僵直,会使瓦楞发白。这是一种温柔的杀伐。它终结了众多柔弱生命的旅程,却也用这终结,换来了大地的洁净与安宁。

我想起乡村的童年,霜降之后的清晨,总是格外令人兴奋。田埂上,枯草的边缘,都敷着一层薄薄的、亮晶晶的银屑。我们用手去触,那冰凉的感觉瞬间传到指尖,随即,那完美的结晶便在我们的温度下,融化成一颗小小的水珠,仿佛一个微型的梦的破碎。那时只觉得好玩,如今想来,那是一种最初的、关于“美与逝”的教育。霜的美,是瞬间的,是脆弱的,是必须依托于寒冷而存在的。它不像雪,可以覆盖一切,营造一个持续的童话世界。霜的美,更清醒,更冷静,也更哲学。它告诉你,所有极致的美,或许都邻近着消亡,都要求一种牺牲的温度。
昨夜的风,今夜的月,等不来故人相约,等来了愁绪添堵。寂寥心事晚,寒山忽明暗。或许生命原本就带着伤感的色彩,蕴含残缺而荒凉的缺憾。此生,相遇的人太多,留下的却太少,相识的人太多,相知的却太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那一段白衣胜雪的青春,痛而甜蜜的往事,在苍翠里缱绻,在荒凉里狼狈。光阴吞噬了鲜衣怒马的念想,命运磨去争胜好强的棱角。不曾老去的,唯有远方的诗和梦想。一缕秋风一往事,一片落叶一念想。
 05
05一夜西风紧,叶落叠成诗。霜降,也是一个充满诗意与思念的节气。古人云:“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在这秋暮寒深的日子里,游子们望着远方的天空,心中涌起对故乡的深深眷恋。那一抹薄霜,仿佛是亲人的牵挂,落在心头,化作无尽的温暖。
南宋的诗人范成大曾写过这样的句子:“饱谙世味,一任覆雨翻云,总慵开眼;会尽人情,随教呼牛唤马,只是点头。”这自然是阅尽沧桑后的旷达。然而对于我们这般寻常人,或许还达不到那样的境界。我们的慰藉,不在高远的云端,而就在这俯拾即是的人间烟火里。它是寒夜里一碗热汤的滚烫,是归家时窗口一灯如豆的等候,是友人相聚时一壶粗茶的闲话。

在民间,霜降有着独特的习俗。霜降时节正是秋菊盛开的时候,中国很多地方在这时要举行菊花会,赏菊饮酒,以示对菊花的崇敬和爱戴。霜降期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寒衣节,又叫祭祖节,与清明节、中元节并称“三大鬼节”。这天,人们会祭祀逝去的亲人,除香烛、食物等一般的祭品外,还会为他们“送”去御寒衣物,叫作“送寒衣”。人们会吃柿子,据说这样可以御寒保暖,补筋骨。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寓意着日子红红火火。还有些地方会举行霜降会,祭祀旗纛神,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6
06一露一霜花,心安才是家。古人对于节气的变换,是怀着一种庄严的体贴的。他们说“霜降腌菜,立冬蓄水”,在万物收敛的时节,为漫漫冬日预备下一份安稳。这使我想起童年在外婆家的光景。秋深了,她总要买回许多雪里蕻与大白菜,在院子里一一地晾开。她坐在小凳上,不紧不慢地收拾着,那菜叶子在她手里发出清脆的声响。然后是下缸,一层菜,一层粗盐,她用手细细地揉搓、压实,那动作里有一种承袭了千年的、对于生活的耐心。那时的我,只觉着好玩,而今回想,那瓦缸里封存的,何止是几棵青菜?那是一整个冬天安稳的底气,是日子得以从容延续的智慧,是一种将光阴的流逝亲手腌制、发酵,最终转化为醇厚滋味的过程。这烟火气里,便有了文化的厚重。
记忆里的霜降,还总是和祖母连着的。天还墨黑着,她就窸窸窣窣地起来了。院里的青石板,一步,一声清冷的响,像敲着什么古老的磬。我赖在暖被窝里,耳朵却跟着她的脚步声,直到那一声“刺啦”——是猪油下了热锅。这声音,比什么鸡鸣钟响都来得实在,它一下就把个虚空寒冷的晨,给填满了,给熨帖了。接着,便是那熬猪油特有的、混着焦香的暖意,丝丝缕缕地从门缝里钻进来,盘绕在帐子周围。这暖是有分量的,它压得住满世界的清霜。那时候觉得,日子就是这样了,永恒的,坚实的,像祖母那双结着老茧的手。
 07
07风动寒气重,秋深岁将暮。窗外的悬铃木忽然就瘦了。枝桠间漏下的阳光带着毛玻璃的质地。信箱里远方寄来的明信片,邮戳那小片湿润的秋像某个人欲言又止的停顿。
风冷一夜寒,露结一朝霜.时光的落笔,是发间的霜,花落的痴。这一季清秋,你若安好,我亦无恙。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总有一刻心动,掉落黄昏的诗行,不在秋声里承欢相见,就在落叶岸边吻心相别。
一枚叶,落下了三千繁华,一夕月,凉透了千年雨巷。捡拾一片秋叶,红一句,黄一句,写下时节的痴缠;听闻雨打残荷,轻一声,重一声,枕落清凉新梦。时光的脚,走出微凉的诗行;落叶的静,荒凉了多少草木摇霜。
“萌生和盛开不再会与今天有关,今天只合苍凉到老。”随着落叶飘零、万物萧落,当秋天逝去、冬天来临时,生命也慢慢归于沉寂。秋去冬来中,生命在凋零之际迎来最后的绚烂,也将在沉寂里孕育新的轮回。
而我,便在这蛹中,守着这一盏渐凉的茶,一片清寂的心,觉得自己也成了这霜降时节的一部分——沉寂着,却也孕育着;凋零着,却也希望着。
岁月如诗,如画,霜色染尽千山,人间最美是秋光。

—End—
我是楚风语语,原创作品,感谢阅读!欢迎大家走进我的文字,感受心灵的温暖。承蒙抬爱,若你喜欢,转发,收藏。期待您的留言。
(创作不易,全网维护中。)
图片来源于网络,感谢!侵权之处,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