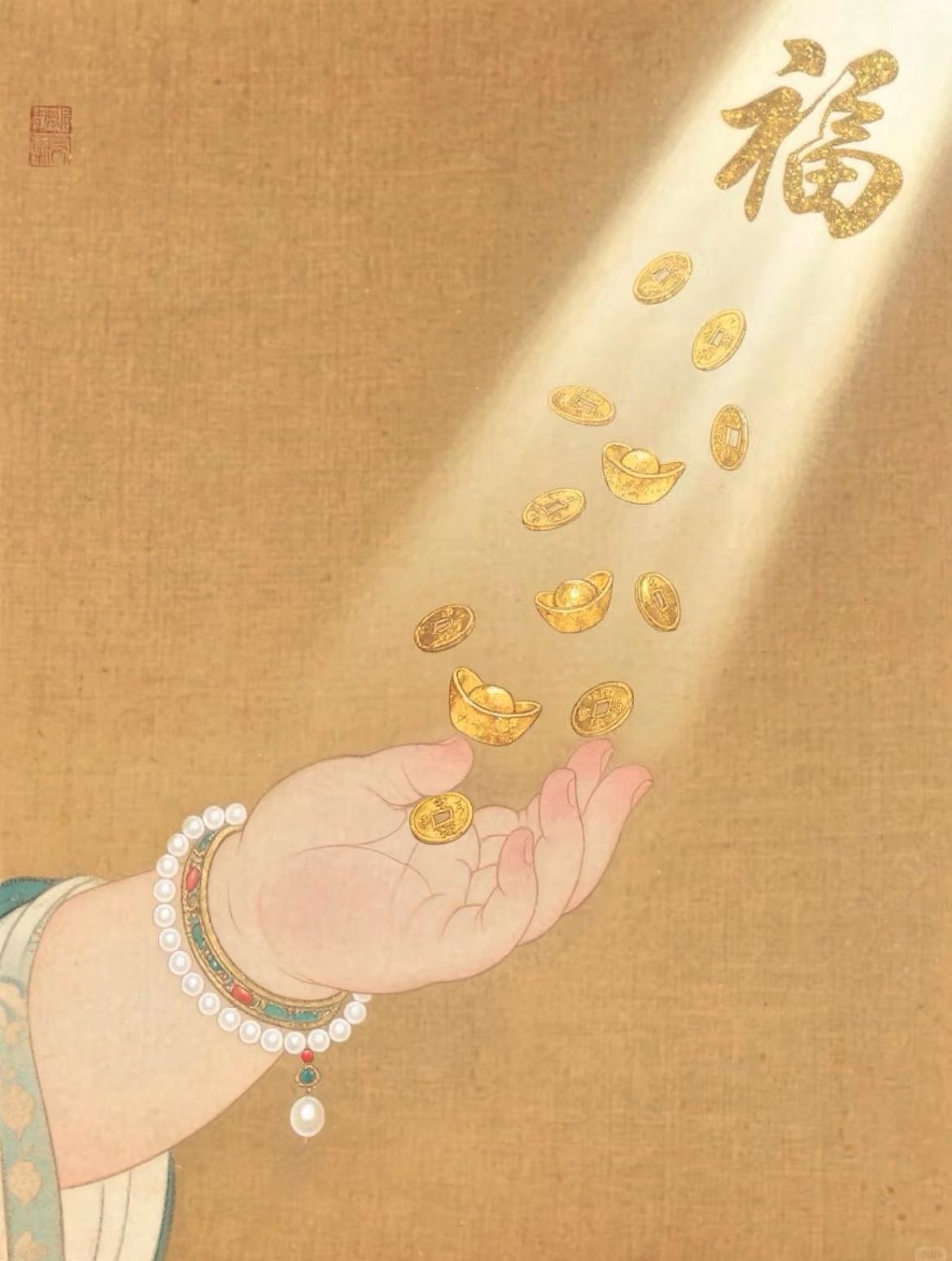在《红楼梦》第五回的太虚幻境中,贾宝玉聆听的《红楼梦》十二支曲,是全书的命运总纲。然而,关于第二支曲《枉凝眉》的归属,却在红学界掀起巨大波澜。以刘心武先生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此曲咏叹的是史湘云与妙玉,而非贾宝玉与林黛玉。此论虽新奇,但细加推敲,却与曹雪芹的文本结构、人物塑造和核心意象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本文将层层剖析,证明一个最符合曹公原意的结论:《终身误》是薛宝钗的婚姻悲歌,《枉凝眉》是林黛玉的爱情挽歌。 这两支曲子,如同“怀金悼玉”的一体两面,共同为书中两位最重要的女主角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悲剧基调。

这是驳斥“史妙说”最根本、最有力的一点。
曹雪芹构思《金陵十二钗》正册,并为之配以十二支曲,其结构意图清晰严谨:一人一曲,命运各表。 我们来看明确的序列:第三曲《恨无常》属元春,第四曲《分骨肉》属探春,第五曲《乐中悲》属史湘云,第六曲《世难容》属妙玉……以此类推,直至李纨、可卿,秩序井然。
若按刘心武先生所言,《枉凝眉》是史湘云与妙玉的合咏,那么请问:
史湘云已拥有专属的《乐中悲》,妙玉已拥有专属的《世难容》,为何要在此处再为二人合咏一曲?
如此一来,史、妙二人在曲中独占三席,而元、探、迎、惜等其他正钗仅有一曲,这在结构上岂非严重的重复与失衡?
薛宝钗与林黛玉,作为全书并列第一的女主角,若在最重要的开篇两曲中均被模糊处理(《终身误》为合咏,《枉凝眉》与之无关),其核心地位又如何体现?
反观“钗黛主体说”,则一切豁然开朗:《终身误》是薛宝钗的判曲,《枉凝眉》是林黛玉的判曲。 这不仅完美解决了“黛玉被咏两次”的困境,更使得十二支曲的布局工整对称,轻重得宜。这无疑是更符合曹雪芹结构美学的解读。

刘心武先生认为“阆苑仙葩”指史湘云(因其象征海棠),“美玉无瑕”指妙玉(因判词有“无瑕白玉”)。此论看似有据,实则是对文本意象的误读。
首先,“阆苑仙葩”非林黛玉莫属。
神话原型定论:第一回中,点明黛玉前世为“绛珠仙草”。而在此处,脂砚斋有批语:“一花一石如有意,不语不笑能留人”。这已权威地将神话中的对应关系点明:绛珠是“花”(仙葩),神瑛是“石”(美玉)。
诗词自我指认:黛玉的《葬花吟》是“葬花”还是“葬草”?她为何自称“花魂”(“冷月葬花魂”)?书中多次出现的“花魂”意象(如第26回)皆与黛玉息息相关。她不是“仙葩”,谁是“仙葩”?
其次,“美玉无瑕”正指贾宝玉。
“赤瑕宫”是宫殿名,并非对神瑛侍者本人的形容。“瑛”字的释义是“似玉之美石”,其本质是石,但其品相如美玉。这块“通灵宝玉”即是贾宝玉的命根与本质的象征。
“美玉无瑕”在此是一种理想化的歌颂,歌颂的是宝玉对黛玉情感的纯洁与真挚,是其“赤子之心”的体现,与世俗判词中的“行为偏僻”并不矛盾。后者是世人的评价,前者是情感的理想。
最后,“眼泪”的时序唯属黛玉。刘心武先生质疑黛玉还泪并非从秋天开始,此论亦不成立。文本多处暗示,黛玉自秋天离乡入京起,便已开始“一年一月”的流泪生涯。紫鹃说她“无事闷坐,不是愁眉,便是长叹……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宝玉也劝她“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寻烦恼,哭一会子,才算完了这一天的事”。“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正是黛玉还泪历程的诗意写照,精准无比。

曲牌名“枉凝眉”——“白白的皱眉”,这是解开此曲归属的又一钥匙。
在第三回,宝玉初见黛玉,见她“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当即送字“颦颦”。“凝眉”即是“颦颦”,这是黛玉独有的容貌与神态符号。
在第二十八回,宝玉所唱的《红豆曲》中,正有“展不开的眉头”一句,正是“枉凝眉”的生动演绎。
若将此曲冠于史湘云或妙玉,则“枉凝眉”三字失去了其最直接、最深刻的文本依托,成了无根之木。
结论:一曲定音,怀金悼玉综上所述,无论从全书结构的宏观考量,还是具体文本的微观分析,《枉凝眉》都只能是林黛玉与贾宝玉爱情悲剧的专属挽歌。
《终身误》:以宝玉的口吻,痛陈“金玉良姻”对薛宝钗终身幸福的贻误,曲中纵然有黛玉的影子,但悲剧的焦点和承受者,是薛宝钗。
《枉凝眉》:同样以宝玉的视角,哀叹“木石前盟”的幻灭,从“阆苑仙葩”与“美玉无瑕”的相逢,到“水中月”、“镜中花”的虚空,再到泪尽而逝的漫长煎熬,其情感核心始终紧扣宝黛二人。
这两支曲子,一婚一恋,一误一枉,一金一玉,以对仗般的形式,在卷首便奏响了“怀金悼玉”的悲怆主旋律。强行将史湘云与妙玉代入《枉凝眉》,不仅破坏了曹雪芹精心设计的艺术结构,更模糊了全书最动人的情感主线。回归文本,尊重原著的内在逻辑,我们方能听懂这首为黛玉和宝钗,也为天下痴情儿女所唱响的旷古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