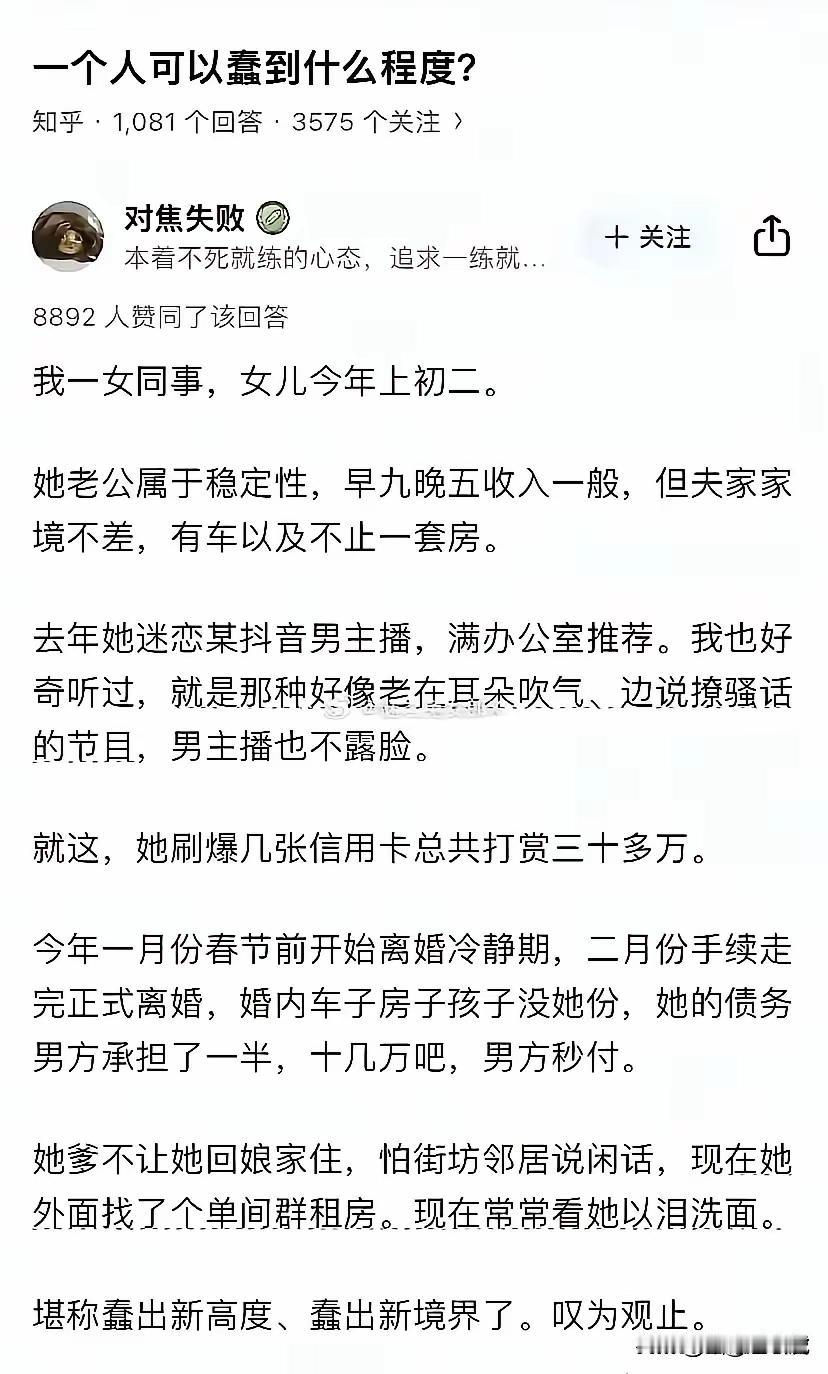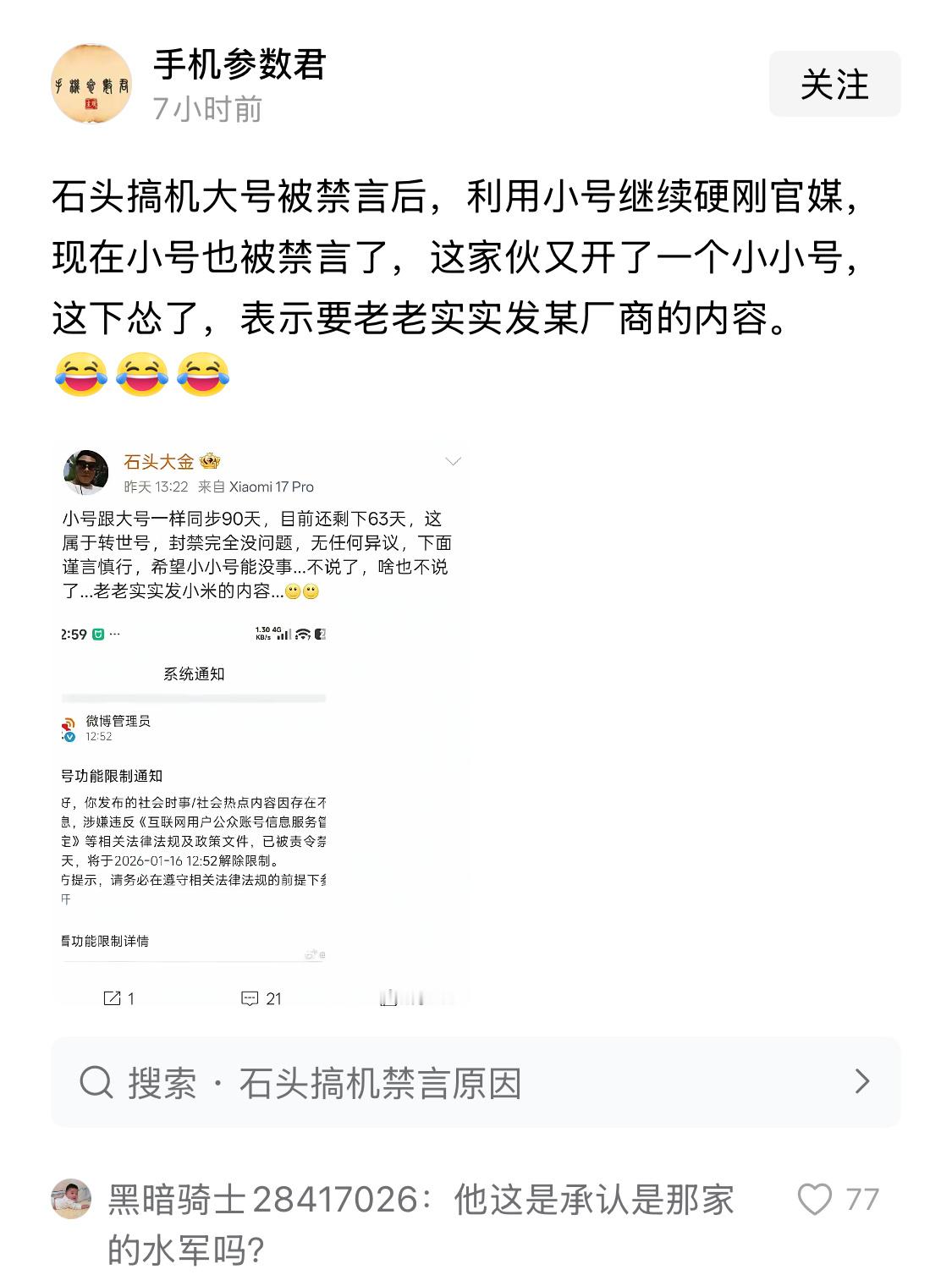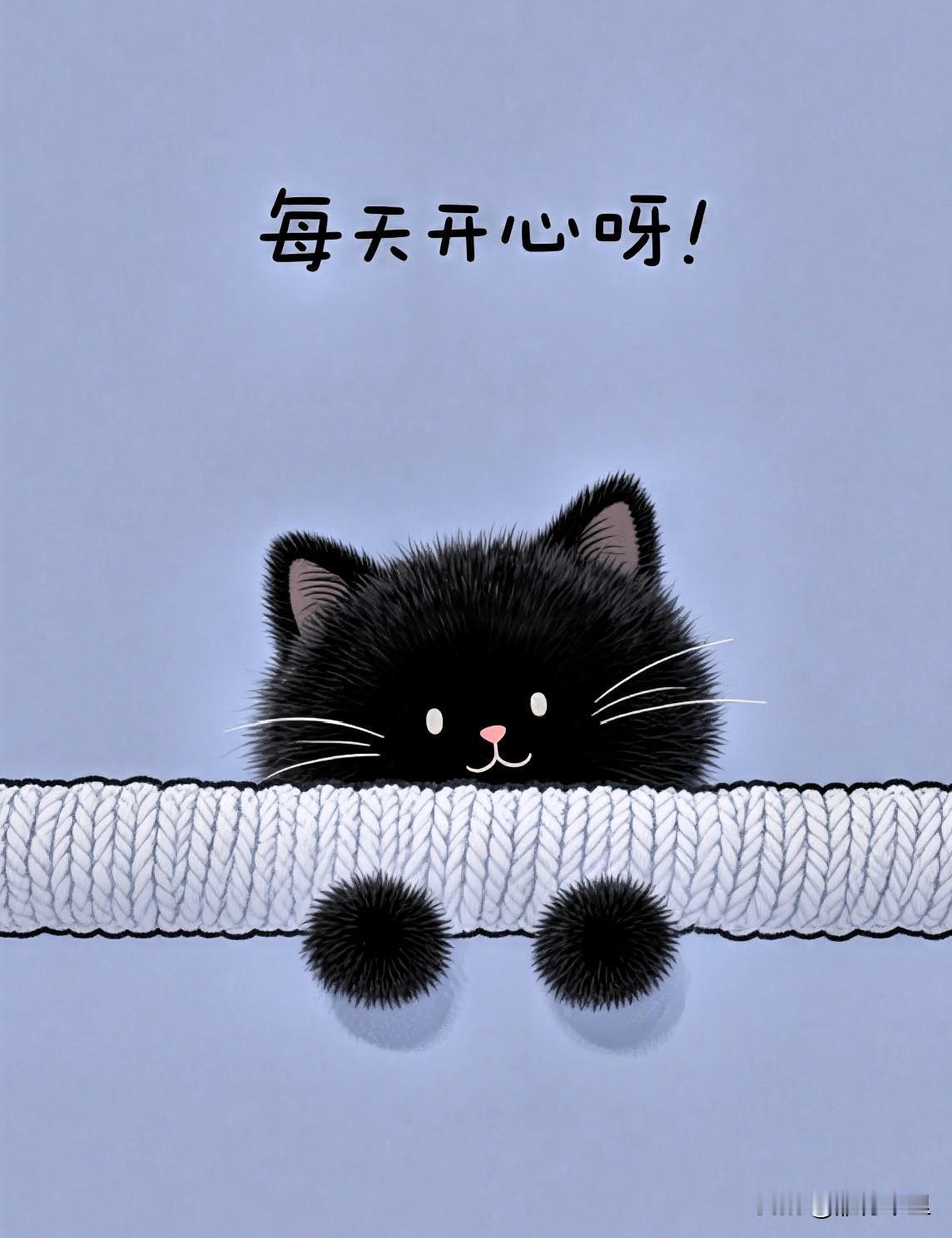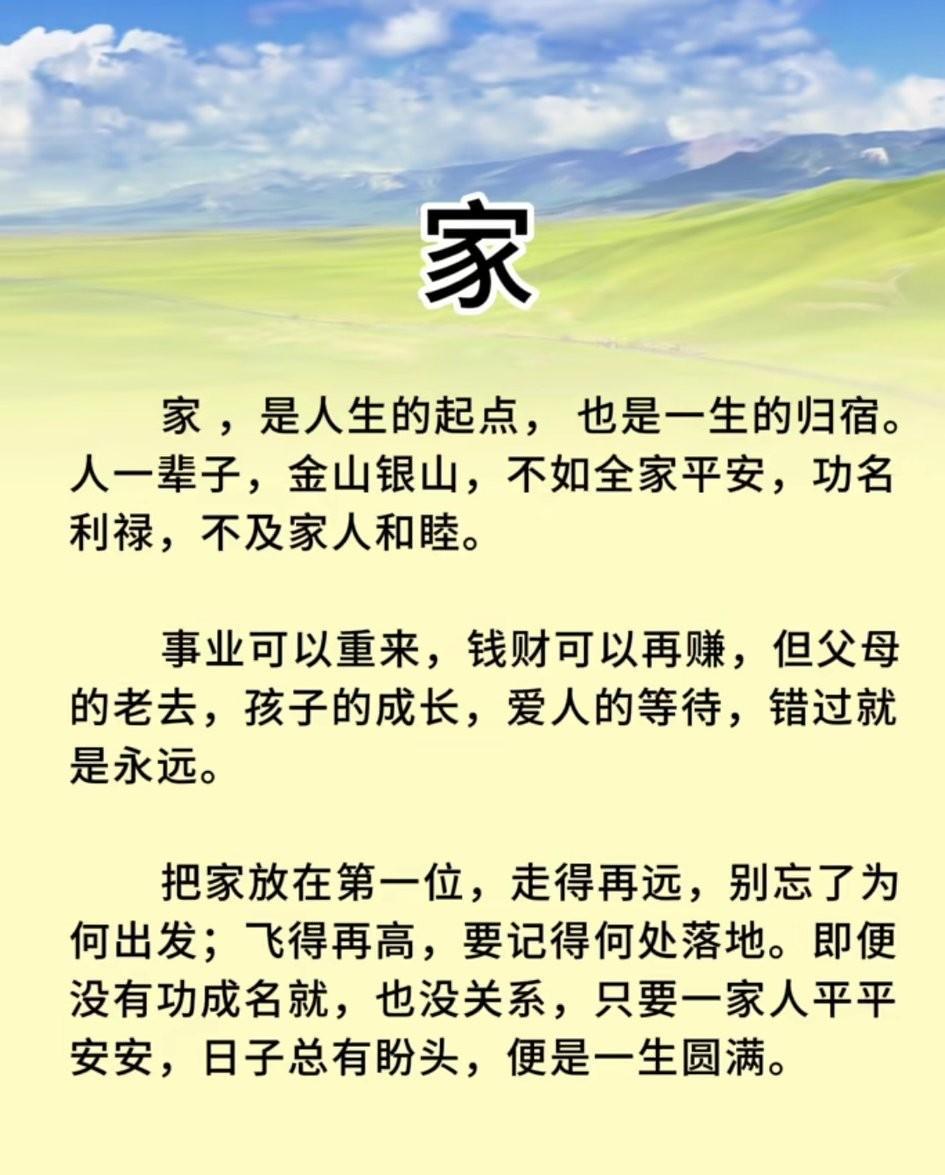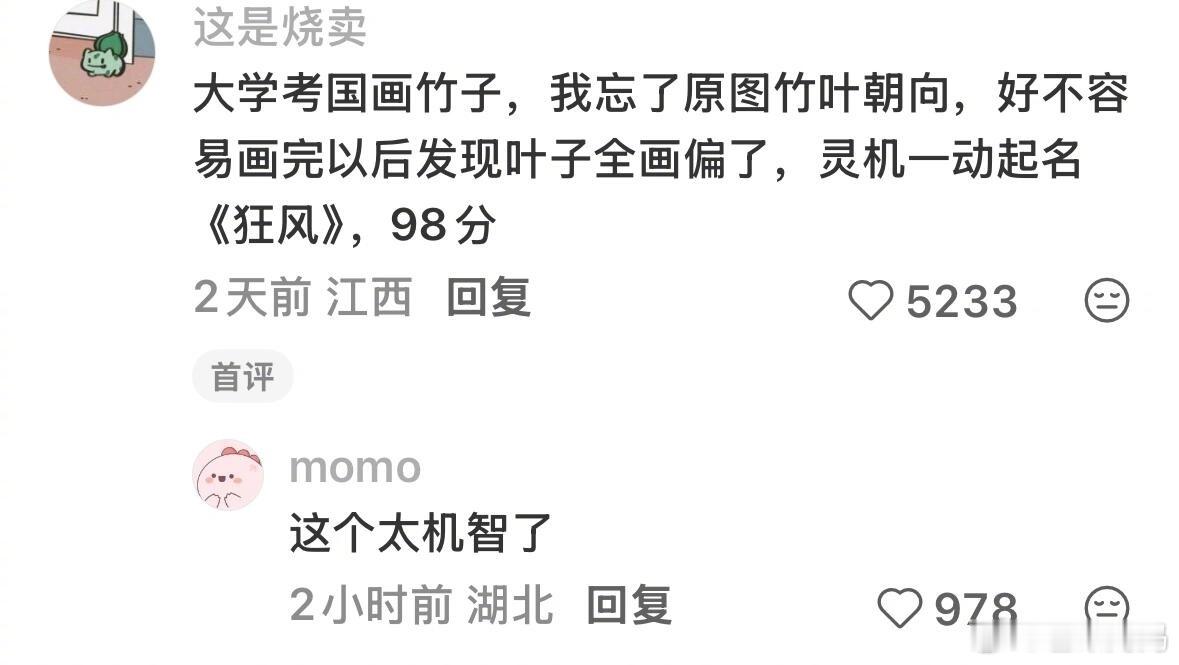文|幸福娃

这世间唯有两样东西不可触摸:一是记忆,二是思念。记忆无花,永远盛开;思念无用,永远清晰。
不要把过去拥抱的那么紧,否则你怎么去拥抱未来呢。人要学会断去无能为力之事,舍去缘分浅薄之人,你断的是内耗,得到的却是新生。
有些事情,初看是失去,再看是获得。人生苦短,不妨把剩下的时间留给珍惜你的人,和他一起去攀一座山,去趟一条河,去追一个梦。
时间淘汰的永远是不坚定的东西,待人如初是件很难的事。
我们总以为不忘初心是守着最初的炽热,可真正经历过岁月打磨的人都明白,时间从来不说谎,他只是安静的证明一切。
被淘汰的从来不是改变,而是那些本就摇摇欲坠的承诺,那个渐渐疏远的朋友,或许不是在忙碌中走丢,而是在你人生的重要时刻选择了缺席。
那段淡去的爱情,可能不是败给新鲜感,而是在风雨来临时松开了交握的手。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改变的交给岁月,把不变的留给选择。
记忆和思念,都像是隔着薄雾看花,明明知道在那里,伸手去碰,却只剩下空气从指缝间流过。它们没有实体,不占地方,却比任何实实在在的东西都更有分量。
记忆这东西,怪得很。它不似花朵,无需浇水施肥,却能在心里常开不败。
有时候,甚至我们自己都忘了它还在那里,它却忽然在某个安静的午后,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刻,悄然绽放。
突然间,多年前的一个场景浮现眼前——或许是母亲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或许是童年玩伴一声清脆的呼唤,或许是第一次独自远行时的那片天空。
这些记忆没有预告,说来就来,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记忆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它的不可磨灭性。即便是那些我们刻意想要忘记的往事,也只是暂时被埋藏,从未真正消失。
它们在那里生根发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塑造着我们的模样。
有人说记忆不可靠,会随着时间褪色、变形。这话不假,但记忆的价值本就不在于它是否精确地复刻了过去,而在于它如何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
就像一本被反复翻阅的书,书页会发黄,边角会磨损,但书中的精髓却越发深刻地印在读者心里。
思念这东西,看似无用,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可人就是这样奇怪,明知道思念换不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却还是忍不住要去想,要去念。
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是满的,又是空的。满是因为那个人占据了你的思绪;空是因为那个人不在身边。
这种满与空的交织,构成了思念特有的滋味——既甜又苦,既温暖又凄凉。
古人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话把思念的那种时间错位感说得透彻。
物理时间一分一秒规律地走着,心理时间却因思念而被拉得长长的,每一刻都充满了等待的张力。
思念叫人懂得距离的沉重。隔得远时,思念是长长的线,这头是你,那头是牵挂的人;隔得近却见不着时,思念就成了薄薄的纱,明明透明,却硬生生隔开了彼此。
最磨人的,莫过于对那些已经离去、再也回不来的人的思念。这种思念没有了期待,只剩下回忆的反复咀嚼。
它不会带来重逢的欢欣,只留下无尽的怅惘。可即便是这样的思念,我们依然舍不得放下,因为放下就意味着彻底的失去。
记忆和思念之所以不可触摸,是因为它们属于精神世界的产物,超越了物质的界限。
你可以触摸一张老照片,但触摸不到照片背后的故事;你可以抚摸一封旧信,但抚摸不到写信人的深情。
这或许正是人生的况味——最珍贵的东西,往往是最虚幻的;最深刻的体验,往往是最不可把握的。
面对这些不可触摸却又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最好的态度就是接纳——接纳记忆的来去自如,接纳思念的缠绵不休。不抗拒,不执着,让它们如云卷云舒,自然来去。
对于记忆,我们不必强求它永远鲜活,也不必害怕它会褪色。它自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出恰如其分的提示。
对于思念,我们不必刻意压抑,也不必沉溺其中。它自会在时间的流淌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诗经》里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时光流转,记忆在变,思念的对象在变,但那份情感的真挚却始终如一。
人生在世,总要有些抓不住的东西,才显得那些能抓住的珍贵;总要有些不可触摸的所在,才让心灵有了向往的方向。
记忆无花,却永远盛开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思念无用,却永远清晰地勾勒出我们情感的轮廓。
这或许就是人性的奇妙之处——我们总是被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深深地打动;总是为那些已经逝去、或遥不可及的人与事,最深地感动。
既然如此,那就让记忆自在盛开,让思念自然清晰吧。不必追问为什么,不必计较值不值。人生本就是一场体验,而记忆和思念,正是其中最纯粹、最深刻的部分。
它们不可触摸,却可感受;不可把握,却可品味。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在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由记忆和思念构建的精神家园,那里花开不败,情意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