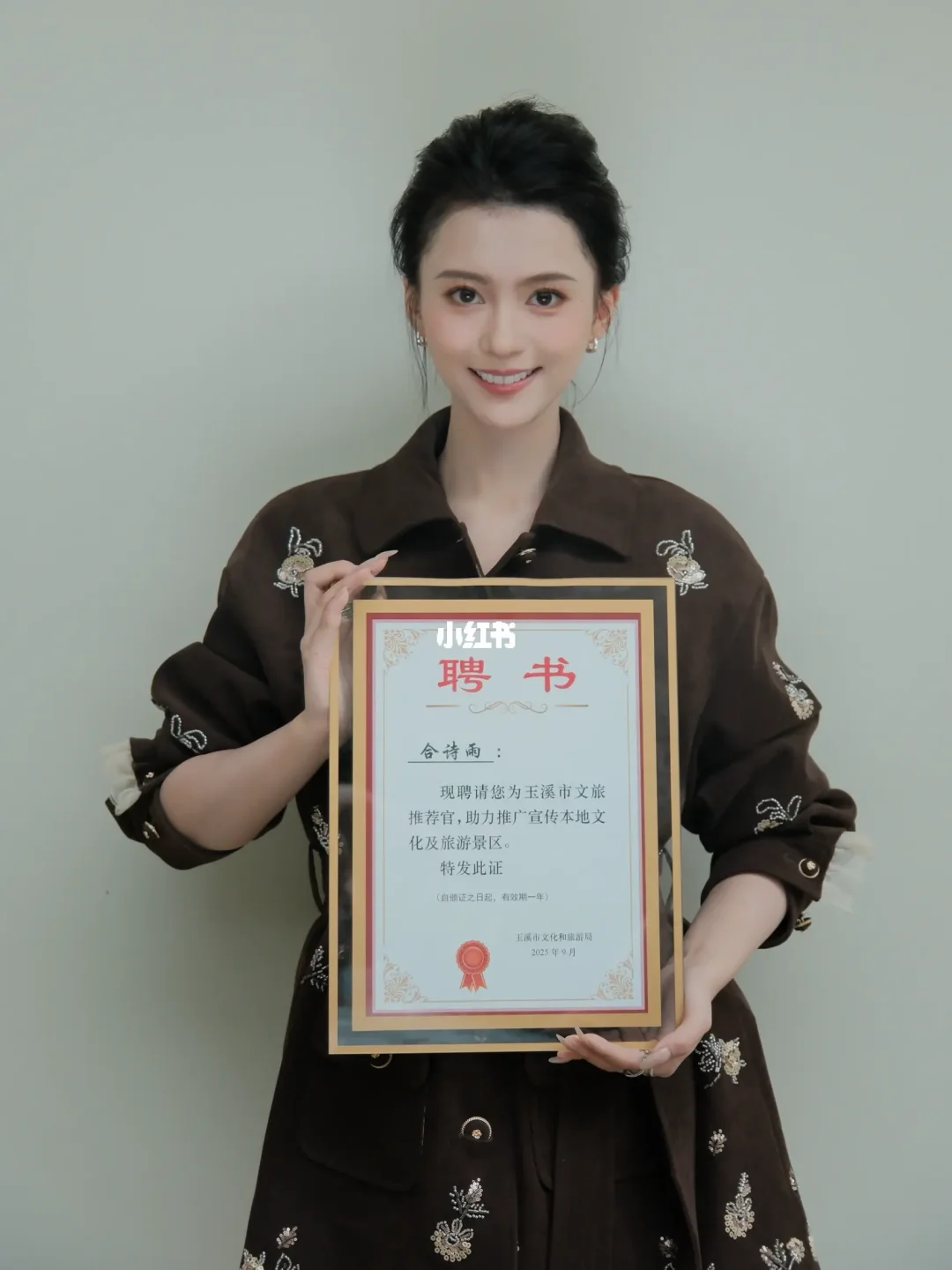“知青领袖”丁惠民:他终结了上山下乡运动......
参考资料:让孩子们回来吧”——1978年“知青大返城”一页、走不出的知青领袖梦——南方周末、我们要回家——版纳知青大返城纪实
2024年9月22日,一个叫丁惠民的老人在重庆突发心梗走了。
消息传出后,一封封唁电象雪片一样飞来,许多人从外地火速赶到重庆石桥铺殡仪馆吊唁,附近的花圈甚至都卖断了货。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丁惠民这个名字遥远而陌生。
而在上世纪七十年末,他的大名响彻全国。
人们不会忘记,1978年,是丁惠民给邓小平写了三封信,喊出了“知青回家”的口号,后来又率领数万知青北上请愿,最终撕开了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豁口。
丁惠民是一个群体的代号,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的离去,意味着知青这个特定时代的产物,终于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01 “我要回家”
美丽的云南西双版纳,曾经是1978年中国知青大返城的策源地。
当年,来自上海的丁惠民和所有知青一样,带着“建设边疆”的决心来到西双版纳,投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他们走进莽莽大山,住在草棚里,拼了命地干。砍掉原始森林,种上橡胶树,有时候一次大会战甚至能十几天不下山。
但几年努力,仍改变不了农场的样子。
在丁惠民的记忆里:“边疆除了自然风景,其他的一切几乎都跟宣传不一样。更何况,吊打、侮辱、强奸知青的事情时有发生。”
日子一年不如一年,回家遥遥无期,知青们几乎绝望了。
丁惠民当时在景洪农场一所学校担任总务。他经常出来给学校采购东西,有机会东走西走,几年下来足迹遍布热带雨林的每一个乡镇、每一个团、每一个营,听到了许多关于知青的悲惨故事,无意中完成了一次社会大调查。
丁惠民对那个年代的解释是:“一开始都很老实,后来在长期艰苦的条件下,人性中暴躁的一面就暴露了。知青和军人都是如此。”
当时知青的出路不少,主要有招工、参军、考大学,但毕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有几个能过去呢?
为了回家,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投亲、嫁人、顶替、病退,什么招都想出来了。
为了得到一张病退证明,甚至有人服用麻黄素来制造高血压,喝高效麻醉药制造“心力衰竭”,喝农药制造“胃痉挛”。
不惜一切,只为回家。
然而最终能够实现梦想的人,还是寥寥无几。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成为了流行口号。
虽然地处边疆,但是西双版纳每天都有新的消息传来:老干部解放,地、富摘帽、右派平反.......
这让丁惠民和其他知青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他们隐隐预感到,回家的日子可能不远了。
是耐心等待上面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还是主动采取行动,促使中央早日着手解决知青问题呢?
在这个问题上,丁惠民经历了激烈的心理挣扎,最终选择了后者。他想起了《国际歌》那几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想改变命运,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为此,丁惠民决意放手一搏。
1978年10月16日,丁惠民写了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信》。
在信里,他说:“我们知青回城后可以干最脏最重的活,可以拿最低的工资。只要能回到父母的身边……”
字字泣血,让人泪目。
丁惠民揭竿而起,率先喊出了“我要回家”的口号,拉开了云南农场知青大返城的一幕。
他的信就像一把大火,迅速在知青之间燃烧,许多人在油灯下签名表示支持。
在“回家”的信念鼓舞下,成千上万的知青奔走着叫好。丁惠民所在的景洪农场,成了风暴的漩涡中心。
02 北上请愿
10月18日,丁惠民写出了第二封公开信。
如果说第一封信是诉苦、哭穷,像孩子跟父母撒娇的话,那么第二封信则是正式从政治上经济上提要求了。
原先说知青上山下乡是为缩小“三大差别”,然而经过多年实践,“三大差别”不仅没有缩小了,反而越来越扩大了。
说来也巧,当时《中国青年报》恰好发表了一篇名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意思是:全国各地知青问题积压甚多,到了非认真解诀不可的地步。
有了理论支持,知青的联名信活动一下子打开了新局面。
1978年12月8日,西双版纳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招待所公开地正式召。
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大决战由此拉开了帷幕。丁惠民被选举为总指挥,他起草了代表五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即第三封联名信。
与此同时,知青们派出了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州委政府和农垦分局,找到领导汇报情况。
可是在漫长的等待后,他们没有见到任何领导。这不是单纯的受冷落的问题,而是五万知青企盼的希望即将再次落空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