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日,沈巍与上海建工爷叔,这两个被称之为上海最大的网红,终于在一家新开的宁波菜门店里,历史性地相遇了。
建工爷叔生于1943年,今年82岁,与沈巍相差20多岁。他们的走红,隐伏着极大的相似性。
这一相似性,表现在他们都是在马路上被发现,而发现的原因,都是是因为他们类似的敞开胸怀的表达方式。
相对于上海人的高冷,沈巍与建工爷叔都有着相似的藏不住秘密的性格,他们不知道在曲意问话者的追问里,隐蔽住自己的一点隐私,总是像开闸放水一般地、滔滔不绝地、全程曝光出自己的生活里的秘辛。
建工爷叔对于沈巍的相见,充满期待。3日这一天,他在他的简陋的65平方米的陋室里,吃了两个大馒头,带上了一袋礼品,于九点钟,准备出发前往目的地。

但建工爷叔等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等上公交车,直到沈巍的团队成员开车前来接应,他方才搭上了顺车,速速地前往约会地。
建工爷叔赶到“佬太公宁波食府”闵行店的时候,沈巍及一众主播早已风卷残云,狼籍了盘盏,此刻已经十二点近半。
两大网红的汇聚,引起了两股追随者的涌浪,撞击着人满为患的包厢。隔着餐桌,沈巍与建工爷叔双手相握,意味着一个耐人寻味的特别时刻,在这一刻定影。

建工爷叔入座后,用他的标志性的激情澎湃的挥舞的手臂、童稚般纯真的眼睛还有那富有节奏的大幅度的肢体动作,表现着他的兴奋与激动,在老成持重的沈巍身边,更像一个顽童。
两大网红,在“文赶”的遭遇上,有着异曲同工的镜像对称。建工爷叔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喜剧演员惯有的风格,说自己被“围追堵截,帽子叔叔说明年可以重返广东路。”
沈巍深有感触,他说:你还能重返广东路,但是我重返白鹤路是不可能了。
热情的建工爷叔搜肠刮肚其它的活动地点,鲁迅公园是他的备用场所,于是,他大方地向沈巍“捐赠”了他的这一预备地:“你能不能去鲁迅公园?”

不提也罢,沈巍立刻想到春天的时候,他带着一众主播,曾兴致勃勃地前往鲁迅公园,但半途而废,胎死腹中。现在建工爷叔竟然哪壶不开提哪壶,实在有些滑稽,于是沈巍在调侃自己的时候变本加厉地自嘲道:“上一次到鲁迅公园铩羽而归,翅膀毛都拔掉了。”
沈巍比划着,形容着自己被拔毛的赤膊状,在幽默这一点上,他与建工爷叔有着遥相呼应的共同性,这也是他们成为网红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上海市民的滑稽气质,之前一直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电影里的一个调剂,这就是海派文化里特有的城市里的俚俗传承,上影厂的一批搞笑的演员牛犇、程之、游本昌都可以视着这一海派传统的继承者。
建工爷叔的夸张表演,我们可以看到牛犇这样的上海喜剧演员的表演特质。这种喜剧风格,也是上海市民化解城市困厄的一剂解药。

沈巍与建工爷叔的对对碰,实际上可以感知他们之间有着惊人相似性,而这背后,折射出的这座城市的民众来历的必然发展出的演化特点。
沈巍与建工爷叔见面的时候,必然要提及各自的籍贯与出身。这也是沈巍面对网友时,总是抛出的第一板斧。
建工爷叔说自己的祖籍是安徽肥东,他自己出生在上海。而沈巍与建工爷叔一样,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移民二代,这可以说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民众来历的共同特点。
沈巍介绍他的籍贯是常熟,建工爷叔称赞常熟有名气。从近代史的纵深来看,翁同龢是常熟人,而出生于肥东的近代名人,当数李鸿章。这样,沈巍与建工爷叔的祖籍地,都曾经产生过历史上著名的历史人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两个人之间似乎能够呼应着故乡地面上走出的近代史中有着关联的历史人物,这样,似乎有一根隐秘的伏线,让他们再次在当代上海相遇。
他们作为移民二代,在上海出生,但都面临着移民二代在这座城市打拼的生存困境。沈巍正是因为被送交外婆抚养,才受到外婆习惯的影响,决定了他日后流浪的基调。

建工爷叔介绍自己的经历,当时因为听说到西部以后可以当小学教师,便放弃了在上海的工厂,来到了边疆。后来他回到上海,但没有户口,挣着低薄的薪水,养着全家七口人。现在住的经适房是按6000元的房价买来的,总价39万元,还掉了19万元,还有20万元。
因为住房问题,儿子48岁才结婚,现在他有一个小孙女,应该年龄还不大。
我们可以看出,上海的移民二代,在这座城市里实际上被边缘化了。他们的上一代都是外地人,经过艰难地打拼,终于在上海扎下根,但是下一代,仍然被这座城市挤压,建工爷叔还好,还有一座陋居,而沈巍还在为他的遥遥无期的房屋而苦苦打拼。
相对而言,上海的市中心涌入的都是外地人,包括两个上海网红见面地的“佬太公宁波食府”的老总,也是一个宁波人。
而当天晚上,邀请沈巍出席“厢会”餐厅的大桶大足浴连锁店女老板和她的姐妹都是安徽人,这些外地人,在上海打拼数年后,都经营起了上海的餐饮娱乐业。

“佬太公宁波食府”的老板开始的时候经营KTV,后转行加入餐饮业,不断扩大业务规模,干的风生水起。相比之下,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如沈巍,却被挤到桥洞下,流浪26年。
这就是城市的残酷的规律。笔者2016年,曾经到万航渡路上寻找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行别业”遗址。当年这里曾经发生一起汪伪特工枪杀中行员工的血腥事件,轰动一时,找到这个小区时,里面的建筑仍是三十年代的样貌,只不过重新进行了表层喷涂。

在这里遇到一位笪姓老伯,他说:现在有钱的人,都是外地人,上海人是很穷的,哪一个能卖得起车啊?你看看这里面到处停着车,都是外地人的(可参见本人所写的《飘落在中行别业的怅惘》)。
而他的下一代,从事艺术的工作,这也是上海移民二代的一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职业选择,他们受城市的文化熏陶,对经商不感兴趣,而痴迷于文化,就像八旗子弟的后代,很多都成为了票友,吹拉弹唱,无所不能,但养活自己却很困难。
在移民二代越来越沉湎于毫无竞争力的文化自娱中的时候,上海的城市布局悄然发生着斗转星移。

外地人长驱直入上海的腹地,把老市民赶到边缘的郊区。我的母系亲属当年住在国际饭店背后的黄河路上,就是沈巍数月前前去听淮戏的那家剧院的门口马路上,后来黄河路拆迁,过去的那两层楼的里弄建筑被推到,在那块地面上竖起了现代化的小区,而原来的居住户很难有钱在此立足,只好向郊区迁移。
城市就在悄然之间置换了居民的成色,就像沈巍,现在他从郊区的白鹤镇进入市中心要花费一个多小时,他戏称自己,现在到外滩,就像“乡下人到上海。”
而建工爷叔同样如此。国庆期间,他被他身边的粉丝带着来到了外滩,望着隔江而立的世茂大厦,甚觉陌生,而东方明珠塔,他是认出来的,但是他说,他自己还从来没有上去过呢。
沈巍作为上海移民二代,可谓是边缘化的一个代表缩影。他对这座城市需要的商业维度不感兴趣,日益被挤压出城市的轨道之外,而在边缘的旮旯里,他只能用文化来自娱,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被发现他掌握的文化内涵能够语惊四座的时候,他重新杀回了上海市中心。
这是一个多么险象环生的几乎无法复制的逆转传奇。

建工爷叔同样被挤出城市的中心位置,但是,他凭着他的最外化地显示出上海市民那种既纯朴、又带着一点狡黠,既带着随遇而安、而又带着坚毅的执着,既谨小慎微,又带着无所顾忌的直言不讳的杂糅的性格,而反噬城市,成为城市的一种标志性的代表者。
沈巍与建工爷叔的相遇,可以成为解读上海密码的一扇窗,这是真正的当代海派文化的现实传奇,而上海的小说家,尚未写出这样一种时代的典型人物,而生活让沈巍与建工爷叔成为了一种现实中的真实典型。
所以,他们红了。
他们的背后是上海的历史的支撑,所以才有着他们的厚重与抹不去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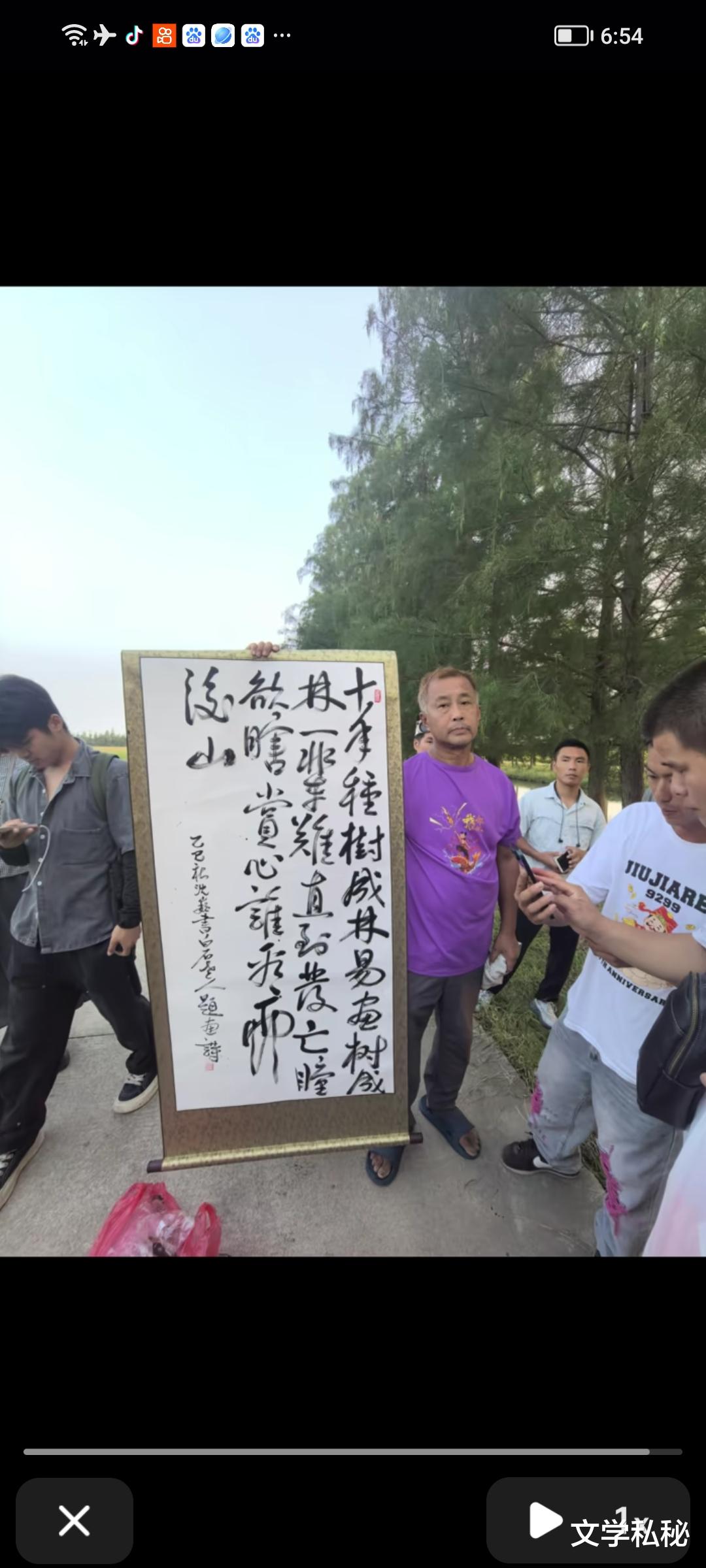
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沈巍爆火的更深次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是这座城市底蕴的土壤里长出的一枝动、百枝摇的中心枝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