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绩效研讨学习的微信群里一个 HR 朋友随口说:“理想汽车不是换了三套绩效体系吗?结果呢,还不就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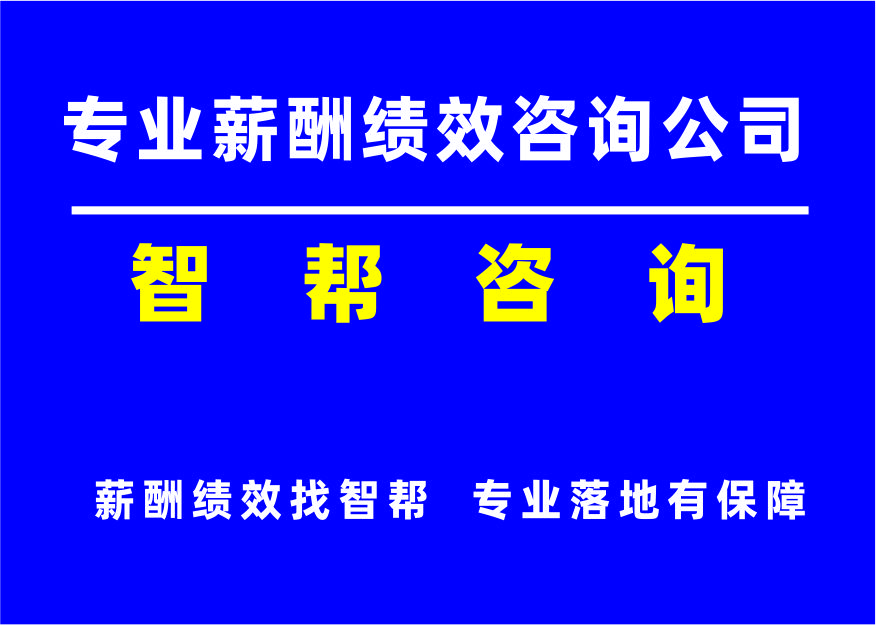
当时没人回话。不是因为他说得对,而是我们心里都在琢磨——真是那样吗?
要是换制度真没用,那李想他们图什么?又不是没事干,非要折腾全公司的考核系统?
后来我认真翻了理想这十年的绩效演进史,才发现,他们压根不是在找工具,而是在找一种能撑住组织变革的底层逻辑。
他们做的每一次调整,都不只是在修修补补,而是在押注下一阶段的组织效率和战略路径。
有些公司,是因为制度老旧被淘汰;而理想,是靠制度不断进化活到今天。
从 KPI 起步,那是一段活下来就行的岁月
刚开始接触理想汽车的管理故事时,有个判断很直觉——他们的第一套绩效系统,大概率是 KPI。
不是因为它先进,而是它管用。
你想啊,2015 年理想刚成立,项目在烧钱,团队靠人撑,组织基本靠吼。在这种背景下,还能搞什么精细管理?活下来就是硬道理。
那时候,KPI 最对胃口。目标明确,干完就算,管它过程漂不漂亮。比如研发,核心节点能不能推进、供应链资源拉得够不够、首批订单有没有进展,这些都是“一眼能看见结果”的事。
说白了,就像公司还在搭骨架,管理必须用力,一锤定音的指标体系,比什么柔性的目标协同都实际。
而且,KPI 这种机制,一套模板全公司能套用,效率极高。对初创公司来说,复杂的系统是负担,而 KPI 是工具,是武器,是活命线。
当然,这种绩效方式后来肯定出了问题,但当时,它真的救了命。
也可以说,理想的第一轮组织纪律感,是被 KPI“逼”出来的。
但这种逼,是外压,而不是内驱。
你可以想象,到了 2017 年后,公司产品线开始推进,人才结构变复杂,问题就显现了:不同部门互不理解、彼此推诿,KPI 考核逻辑在跨部门合作上直接失灵。
管理者开始发现,KPI 的副作用是:只要做完“我那一段”,就万事大吉,至于整体项目跑不跑通,反正不是我背锅。
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得换一种语言了。
OKR 来了,把大家绑成一个团队,而不是一群任务执行者
OKR 第一次在理想内部出现,是 2018 年。
不是从哪个讲师那听来的,也不是跟风学硅谷,而是真有管理痛点逼出来的。
最早推的是产品团队,他们内部做事节奏快,KPI 一套上去,啥都变得机械。后来推到了研发、智能驾驶、再到组织职能,整家公司就像突然学会了一种新语言。
但别误会,他们学得一点不“原教旨”。
比如谷歌那种挑战型 OKR,目标定得高,完不成也无所谓,理想不吃这一套。李想亲自定调:“我们搞的是承诺型 OKR,定了就要做到。”
这和他们做车的风格一脉相承。你总不能说:“这个自动驾驶功能我试试看,做不成拉倒。”
在理想,做不到就意味着延期,延期就意味着市场错过,损失是千万级别的。
所以 OKR 在这里是严肃的,不是“写来好看的”。
为了配套推进,他们甚至搭了一整套“OKR 基础设施”。每个人的目标必须写进系统,全员可见。进展如何,每周都要更新,项目卡在哪里必须讲清楚。到了季度末,还得拉团队一起做复盘,讲成果,也讲过程,不能只是“上交一个数字”。如果 OKR 写得不清楚,专职团队还会要求重写——写清楚目标,已经变成理想员工的基本功。
OKR 还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组织不再是被命令推动,而是被目标吸引。
比如智能驾驶团队 2021 年那会儿搞“端到端”,刚开始技术方案不成熟,KPI 压上去,大家都怵;但用 OKR 写清“探索路径”“试点场景”“风险验证”,反而激发了团队的自驱。
原来,不是技术不行,是绩效机制压错了方向。
这也是 OKR 在理想能活下来的根本原因——它不是用来对人,而是用来连人的。
再往前走,OKR 管不住一个几万人大公司了
一切变化,都从 2022 年底开始。
那时候,理想的车卖得飞起,组织一夜之间膨胀成一个“集团型公司”。
过去那种“靠信念协同”的状态开始失效。你不能指望一个有 12 年经验的销售总监,还能像当年初创那样,和你一起“对齐目标”;你也不能指望一堆部门能靠自发配合搞定复杂系统项目。
公司再不“硬起来”,组织就塌了。
所以他们干了一件非常“理想”的事——学习华为。
是像素级对标,连语言都在学。
绩效体系直接升级为 PBC,不再讲协同,而是讲承诺。每个人要签下“业务契约”,说明自己在这个周期要完成什么、交出什么结果、提升什么能力,条条写清。
这套机制听起来像是“回到刚性管理”,但在理想当时的状态下,是一种必须。
绩效周期也从季度变成半年,为的是压缩管理成本、适配长周期业务逻辑。绩效等级也重新划分,M 档比例做大,让“符合预期”变成主流,降低了激进筛选的紧张感。
更特别的是,“高七”被写进 PBC 里头,变成了评价员工行为的第二维度。不再是你绩效好就能升,而是你要表现得像个“高效能成年人”——主动沟通、敢于负责、追求成长,这些习惯,是硬门槛。
可以说,PBC 不只是制度,是一种文化投射。绩效是理性,背后却有情绪指向。
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有的业务不能被承诺定义
2024 年底,理想突然宣布,要从“智能电动车公司”转型为“人工智能企业”。
这不是换个说法那么简单,而是整个业务方向发生了本质变化。
原来造车,是结果明确、路径清晰的事;现在做 AI,是高度不确定、边试边改的过程。
这时候你再拿 PBC 去要求“承诺结果”,就是在压死探索。
果然,很快他们在 2025 年做了新一轮绩效调整——部分业务条线回归 OKR,尤其是创新类部门。
比如搞智能驾驶模型的团队,再也不能用半年考核一个结果指标。他们用 OKR 写试验计划、技术迭代、风险识别,把试错空间撑出来,重新激发了活力。
这时候理想终于放下了“非此即彼”的执念:不是 OKR 好还是 PBC 好,而是——每个机制,都有它该出现的位置。
从此之后,他们内部的绩效系统变成了“混合模式”。
创新条线用 OKR,执行条线保留 PBC,职能条线甚至保留了部分 KPI 残留。绩效不是“一刀切”的教条,而是“一线感”的机制组合。
这时候你才明白,真正成熟的公司,是敢于在组织内部“分层管理”的。
写在最后
总结这一大圈,我只想说一句:
理想在绩效管理上,一直在“找最合适的办法”,而不是“找一个完美的工具”。
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制度能包打天下。OKR 再先进,不适合你就得放下;PBC 再刚猛,压错地方也是灾难。
他们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是从不盲信“哪一套”,而是时刻看“这一套现在还能不能撑住公司”。
绩效制度的好坏,不在于工具本身,而在于用得是否合时、合地、合组织。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管理进化”:你始终不变的,是愿意不断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