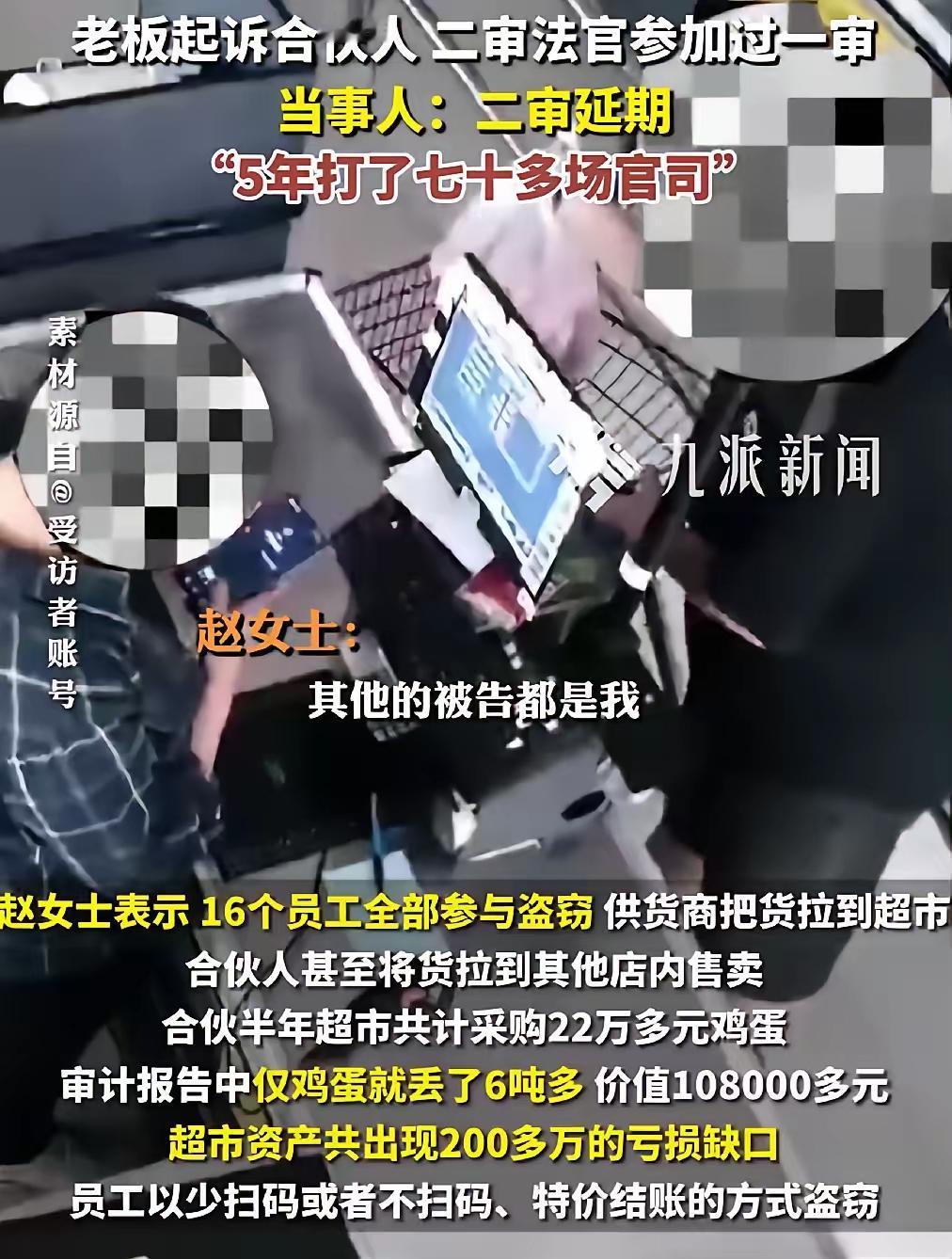一、起因:合作开端与争议起因
2004年,承某受北京城某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委托,与周口海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后更名河南某职业大学)签订两份经公证的建设工程合同,承接教学楼(伸缩缝以西)与宿舍楼施工,约定明确单价与180天工期,由此开启了双方的合作,《监督申请书》《承某法律服务方案》均有记载。
合同履行期间,校方出现多项违约行为:单方面压缩工期导致成本增加、施工现场不达标引发停工待料、频繁变更设计延长工期,更长期拖欠工程款,致使承某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并因此被起诉。即便如此,承某仍于2006年8月完成工程交付,而校方拒绝结算。
2006年1-2月期间,承某接到相关通知前往处理工程相关事宜,到场后,相关人员收走车钥匙、摩托罗拉手机等物品,并造成随后,承某被带至看守所。2006年12月20期间,另有人员闯入其工地办公室,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办公室内被褥等物品被毁,资料也被烧毁。此后,李某以“伪造企业印章罪”对承某进行举报,导致承某被拘留并判刑两年。关键在于,伪造企业印章罪依法应由被伪造印章的北京城某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控告,该公司始终未采取行动,反而是利益相关的李某推动此事。承某在《最高法申诉书》中提出,认为该举报实为相关方为逃避债务所为。刑事判决导致承某失去两年自由,期间部分关键施工资料也意外遗失,这为其后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增加了客观难度。
二、维权过程:十年信访与八次判决
2006年9月4日,李某出具手书便条,写明“9月4日学生开学,宿舍、教室先搬进住;9月5日按合同算账”。这份收录于《二审判决》的便条,证明校方已接收工程并投入使用,且未提任何异议,一审判决也曾认可此事实。但“算账”承诺未能兑现,不久后承某被羁押。2008年底刑满释放后,他开始持续维权。
承某表示,他从2009年起频繁信访,向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19年底,他起诉至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诉讼过程如下:2020年5月,法院以“超时效”驳回;6月中院维持;11月省高院裁定“时效认定不足”,指令再审;12月中院撤销原判发回。2022年4月,川汇区法院判校方付工程款251.81万元,同时判承某赔校方242.4万元,双方上诉;10月中院以“新证据”再发回。2023年5月,法院以“双方无充分证据”驳回双方诉求;8月中院维持;12月省高院驳回承某再审申请。2024年7月,检察院也驳回其监督申请。
承某表示,其在庭审中感到陈述和举证受限,并称曾多次前往法院、拨打电话,但沟通不畅。这些陈述与反复的判决、冗长的程序反映了其在维权过程中——工程已交付,却需要就其完成工程的主张进行举证。
三、争议焦点:证据认定与法律适用的分歧
案件争议核心围绕“证据认定”与“法律适用”,在这两个环节上的分歧,导致承某的诉求未获支持。
承某的核心证据中,2006年李某的便条最为关键。《最高法申诉书》强调,“学生宿舍教室先搬进住”不仅是接收证明,更意味着工程合格,契合“发包人擅自使用视为合格”的法律规定,但后续判决认为该便条“未明确认可全部完工”,对其证明力未予采信。此外,2021年鉴定机构依据图纸和签证,算出工程总造价884.83万元,欠付251.81万元,校方对此予以否认但未提供反证。鉴定意见未被法院采纳,理由是“非实际工程量”。更有《民工诉讼》中农民工判决书,证明工程已结束,与校方“未完工”说法矛盾,却未被重视。
校方提供的证据之间存在不一致:24张现金支票与证人证言冲突,万某称“工程款分期付”,支票却显示一次性支付,贾某称“现金付”,校方却拿支票记录,且贾某答不出工程单价;校方主张的损失金额反复,从28.12万元到10万元再到52.9万元,法院在认定证据证明力时,综合考虑了双方证据的情况。
在法律适用方面:校方以部门规章指责承某未交竣工资料,却忽略其不能对抗《民法典》;承某未交资料是因刑事羁押致材料丢失、后续找校方结算遭拒,责任不在他,法院认定其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申诉方认为,法院在举证责任的分配和证明标准的把握上存在争议;申诉方指出,校方新增反诉未补缴诉讼费,其程序合法性存疑。
四、结语:近二十载维权历程与待解的诉求
从2006年工程交付到2025年仍信访,承某的维权已近二十年。他经历了刑事处罚、多次诉讼和检察监督程序被驳回,但始终未放弃维权。2025年8月川汇法院召集专家和各界人士听证并对案件情况进行了讨论,虽然与会人员都认为原判决有错应予纠正,但两级法院仍未有后续进展;他至今仍在为诉求的解决而努力。
承某的诉求不仅是追索工程款,也希望能澄清其按约完工后仍需反复举证的原因,并希望其提供的证据能得到充分考量。期待此事能依法得到妥善解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得到保障。
(本文基于当事人陈述及公开资料整理代为发布,如有不实言论我们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侵权请联系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