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拔掉氧气管?"
医生这句轻声的问话,在2000年夏威夷那个清晨的加护病房里,仿佛有千斤重。张学良坐在轮椅上,沉默良久,最终轻轻点了点头。

你猜,那一刻他心里在想什么?是无奈接受,还是某种解脱?抑或,这是他和她之间,外人永远无法理解的默契?
病房里,呼吸机依旧发出规律的声响,只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人,已经等不到天亮了。赵一荻的眼睛睁着,看着陪伴了她七十二年的男人,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被岁月折磨得不成样子——红斑狼疮、切掉半边肺、骨折后遗症,晚年连呼吸都像拉风箱一样艰难。

实话说,我本来想写她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步的,但后来发现,真正让人心碎的,可能是那碗没喝成的粥。
6月7日晚上,88岁的她不想吵醒看护人员,摸黑去厨房煮粥。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就垮了。这让我想起她年轻时的那股倔强:宁可自己硬撑,也不愿麻烦别人。被幽禁在贵州阳明洞时,张学良的伙食被特务克扣,她养鸡种菜,攒鸡蛋给他补充营养,自己啃红薯。这么看来,那碗没喝成的粥,简直成了她一生的隐喻——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别人,自己默默承受。

话说回来,张学良那个点头,真的只是无奈吗?我总觉得,这里头藏着只有他俩才懂的密码。1990年刚解除幽禁时,赵一荻写过一句话:"为什么才愿意舍弃自己?就是因为爱,才愿意舍弃生命"。她年轻时舍弃了父女关系、舍弃了自由,到老了连一口气都舍得。
那张学良呢?1940年收到一封电报,他从香港赶往贵州陪伴被囚禁的她。之后他念叨了一辈子:"我亏欠她太多"。所以当医生让他做决定时,他想的或许不是放弃,而是放开手。就像当年她为了他放弃幼子,如今他替她斩断痛苦的绳索。这对恋人,连告别都带着宿命的对称——1929年赵四小姐从天津私奔,她父亲在《大公报》连登五天声明:"四女绮霞,近日被自由平等所迷惑,竟然做出私奔……从此以后一概不再负责"。这断绝关系的启事,不也是一种"拔管"?七十一年后,轮到他亲手切断最后一丝生机。

坦白讲,我一开始以为这是决裂,后来才明白,这更像是一种成就。拔管后,医生给注射了镇静剂,赵一荻入睡了,张学良一直握着她的右手,直到脉搏停止两小时后才被劝离。之后侄孙赵允辛回忆,少帅回到公寓还习惯性嘟囔:"太太在睡觉,不要吵醒她"。这场景,像极了1936年西安事变后,她被送往香港前在上海空宅等待——那时她不知道他能否存活,如今他不知道她何时会苏醒。只是这一次,没有下一趟船了。
讽刺的是,他们一生被政治、战争、幽禁折腾,最后却要靠医疗程序来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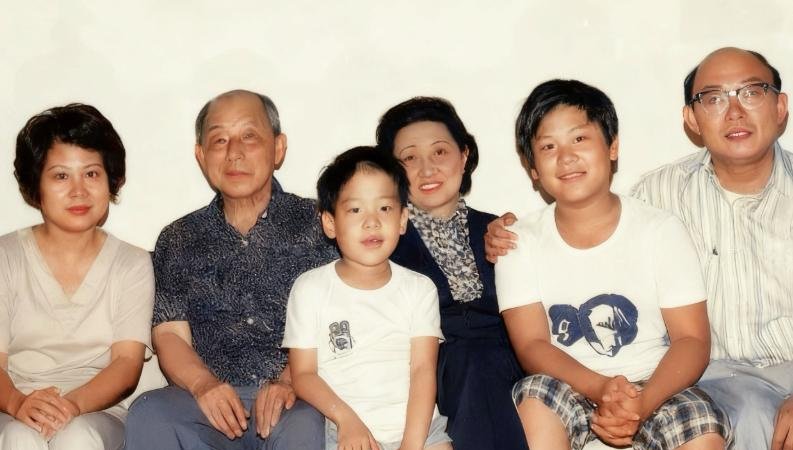
回头想想,这选择早有伏笔。1964年台北"兰花婚礼"上,牧师问"不管是生病还是健康,会不会不离弃",张学良回答"我愿意",手却在颤抖。那枚兰花戒指戴到赵一荻手指上时,她的眼泪落在他手背上。
三十六年都熬过来了,却要在能自由的时候,学习如何说再见。
葬礼上,赵一荻穿着红色绣花上衣,胸口别着珍珠针,身下垫着侄孙从北京机场匆匆买来的锦缎被面。棺木落入神殿谷墓穴时,张学良盯着墓碑空白处发呆。后来碑文刻的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是他们常读的《约翰福音》里的话。墓室旁的空位,五年后他也躺了进去。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永恒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