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都宫的夜晚,烛火晃得人眼晕。杨广坐在铜镜前,指尖划过鬓角的白发,那发丝像极了运河里漂着的枯柴,一扯就断。他抬手摸了摸腰间的剑,剑鞘上还留着当年平陈时的磕碰痕迹——那会儿他还是二十出头的晋王,跨马渡江时,风都跟着他的马蹄跑。可现在,窗外的江风裹着兵变的流言,拍在窗纸上,像有人在不停敲门,敲得他心头发紧。

“朕这一生,到底是做了千古功业,还是造了无边罪孽?”他对着铜镜里的自己低声问,声音散在空气里,连个回音都没有。萧皇后端着一碗温热的莲子羹进来,见他这模样,把碗放在桌上,轻声说:“陛下,夜深了,喝口汤暖暖身子吧。”杨广没动,只是盯着铜镜里皇后的影子,忽然笑了,那笑声里裹着哭腔:“当年在扬州,朕学吴语给你听,你说朕不像北方来的皇子,倒像江南的书生。可现在,这江南的水,怕是要淹了朕的江山了。”

开皇八年(588年)的秋天,六合城的军营里,杨广正拿着地图跟高颎、韩擒虎议事。隋文帝要统一南方,把这个担子交给了刚满二十岁的他,任行军元帅。帐外的士兵们正在磨兵器,叮叮当当的声音里,杨广的声音格外清亮:“陈叔宝沉迷酒色,朝政荒废,咱们这一去,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让天下百姓不再隔江相望。”他手指在地图上划过长江,从六合到建康,每一个据点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年十二月,隋军分八路渡江。韩擒虎带着五百人夜里偷渡采石矶,陈军的士兵还在睡梦里,就成了俘虏。杨广在后方坐镇,每天接到的战报都在往好里走,直到正月里,韩擒虎从朱雀门进入建康,活捉了陈叔宝。消息传来时,杨广正在营帐里写奏折,笔杆一顿,墨水在纸上晕开一小团。他站起来,走到帐外,望着南方的方向,风里好像飘着建康城里的钟声。后来他进了陈宫,看到陈叔宝藏在井里的酒器,拿起闻了闻,对身边的人说:“如此奢华,焉能不亡?朕若治国,必不让百姓受此奢靡之苦。”可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多年后,有人会用同样的话评价他。
开皇十年(590年),江南的叛乱像野草一样冒了出来。沈玄侩、高智慧这些士族,不满隋朝的制度,拉起队伍反抗,一下子就占了十几个州。杨广刚从建康回到长安,又被隋文帝派回扬州,负责平叛。这次他没带兵,只带了几个谋士。到了扬州,他没急着派兵镇压,而是先找了当地的士人谈话。在一个雨夜里,他跟江南名士虞世南坐在灯下,听虞世南说江南百姓怕的是“制度改得太急,家乡的根没了”。杨广点点头,第二天就下了令:江南各州的旧俗,只要不违国法,都可以保留;还任用了不少江南士人做地方官。

杨素带兵镇压叛乱时,杨广就在扬州城里安抚百姓。有一次,他看到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哭,问了才知道,老妇人的儿子被抓去当兵,家里只剩她一个人。杨广让人给老妇人送了粮食,还下了令:凡因平叛被征调的士兵,家里都给免税三年。后来叛乱平定,江南渐渐稳定,杨广站在扬州的城楼上,看着长江里往来的商船,对身边的萧皇后说:“你看,百姓要的不是打仗,是安稳过日子。只要让他们安稳,江南就不会再乱。”可那时候的他,还没意识到,日后他会因为自己的雄心,打破这份安稳。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仁寿宫的空气里满是药味。隋文帝病重,杨广守在病床前,看着父亲枯瘦的手,心里又慌又乱。他知道,父亲一旦走了,这大隋的江山就该轮到他了。可他也怕,怕自己撑不起这份家业。有一天,隋文帝拉着他的手,说:“朕把江山交给你,你要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别学陈叔宝,要学汉文帝,让百姓安居乐业。”杨广用力点头,眼泪掉在父亲的手上。

没过几天,隋文帝就去世了。杨广在仁寿宫即位,发布即位诏书时,他站在朝堂上,看着下面的文武百官,声音有些发颤:“先皇遗诏,让朕继承大统。朕定当遵先皇之业,弘大隋之治,让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可朝堂下,有人在悄悄议论,说隋文帝的死有蹊跷。杨广听到了,却没解释——他知道,不管怎么说,都会有人怀疑。他只能用行动证明自己,可这份证明,后来却走偏了方向。

大业元年(605年)春天,洛阳城外的工地上,两百多万民夫正忙着营建东都。杨广站在邙山上,看着宇文恺画的规划图,手指在图上的宫殿、粮仓上划过:“洛阳居天下之中,西接关中,东连山东,南靠江南,在这里建东都,能镇住天下。”宇文恺在旁边说:“陛下英明,东都建成后,含嘉仓能存百万石粮食,就算关中受灾,也不怕了。”

可杨广没看到,工地上的民夫们弯着腰,把泥土一筐筐抬走,太阳晒得他们皮肤脱皮,汗水滴在地上,瞬间就干了。有个老民夫累得倒在地上,旁边的人想扶他,却被监工的士兵推开:“别耽误干活,陛下等着东都建成呢!”杨广其实知道民夫辛苦,有一次他夜里去工地,看到民夫们在啃硬邦邦的窝头,就下令给民夫们加发粮食和布匹。可到了下面,这些东西大多被官吏克扣了,民夫们还是吃不饱、穿不暖。
同年三月,通济渠的开凿也动工了。杨广站在洛阳西苑的门口,看着民夫们从谷水、洛水开始挖渠,要把黄河和淮河连起来。他对身边的大臣说:“南北分隔了几百年,有了这条渠,南方的粮食能运到北方,北方的货物能卖到南方,天下就能连成一体了。”《资治通鉴》里记载,这次征发了河南、淮北的民夫一百多万,男人不够,就征女人。

有一天,杨广乘船视察通济渠,看到两岸的民夫在水里泡着,有的人脚都烂了,还在挖泥。他让船停下,叫过一个监工的官吏,问:“为什么不让他们歇一歇?”官吏低着头说:“陛下,工期紧,要是误了,怕……”杨广没再问,只是让身边的人拿些药膏给民夫。可他心里清楚,为了赶工期,这样的辛苦是免不了的。他看着渠水一天天变宽,心里既高兴又不安——这条渠会给天下带来好处,可也会让百姓记恨他吧?
大业三年(607年),杨广决定北巡突厥。那会儿启民可汗已经臣服隋朝,可杨广还是想亲自去看看,让北方的游牧民族知道大隋的强盛。他率着几十万大军,从榆林出发,还下令修建了一条榆林大道,宽百步,从榆林一直到突厥的牙帐。
到了突厥牙帐,启民可汗带着部众跪在路边迎接,捧着酒壶给杨广敬酒,跪伏得特别恭敬。《隋书》里写“启民可汗奉觞上寿,跪伏甚恭”。杨广坐在帐篷里,看着突厥的贵族们一个个低着头,心里特别自豪。他举起酒杯,对启民可汗说:“朕与可汗为兄弟,以后北方的边疆,就靠可汗守护了。”启民可汗连忙点头:“臣定当为陛下守好边疆,不让匈奴再犯。”
可宴会结束后,杨广单独召见了长孙晟,问他:“突厥表面臣服,心里会不会有二心?”长孙晟说:“陛下,突厥实力不弱,只是现在怕我大隋的兵力。咱们还是要加强边防,不能掉以轻心。”杨广点点头,第二天就下令在榆林以北修建长城,征发了十几万民夫。他知道,表面的和平靠不住,只有实力才能守住边疆。

大业四年(608年),杨广又下令开凿永济渠。这次是为了征高句丽做准备——高句丽不遵隋朝的诏令,还联合其他部落,杨广想亲自带兵去征讨,永济渠就是为了运军粮。他让阎毗负责,征发了河北的民夫一百多万。那时候北方天气冷,民夫们在寒风里挖渠,很多人的手都冻裂了,流着血,还得接着干。
杨广去视察永济渠时,看到一个民夫的手裹着破布,血从布缝里渗出来,还在用力挖泥。他走过去,拿起民夫的手,看了看,说:“这么冷的天,怎么不给他们发棉衣?”身边的官吏说:“陛下,棉衣已经发了,可能是……”杨广没听他解释,直接下令:“再调一批棉衣过来,亲自发给民夫,谁要是敢克扣,斩!”可就算这样,还是有很多民夫因为冻饿病死在工地上。杨广站在渠边,看着冰冷的河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为了征讨高句丽,他只能这样做,可百姓的苦,他也记在心里。

大业六年(610年),江南河的开凿开始了。从京口到余杭,十几万丈的河道,征发了江南的民夫十几万。这次杨广没去视察,只是在洛阳宫里等着消息。有一天,负责工程的官吏回来汇报,说江南河已经开通,宽十余丈,能过大船。杨广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决定南巡。
他乘船从洛阳出发,沿着大运河一直南下,到了杭州。站在钱塘江边,看着潮水滚滚而来,他写下了“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的诗句。可写着写着,他想起了征高句丽的事,笔就停了。萧皇后在旁边说:“陛下,江南这么美,不如多待几天?”杨广摇摇头:“高句丽还没平定,朕哪有心思赏花。等平定了高句丽,朕再陪你好好游江南。”可他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机会好好看江南的花了。

大业七年(611年)冬天,涿郡的军营里挤满了人。杨广要征高句丽,在这里集结了一百多万军队,还征发了两百万民夫运粮。《隋书・炀帝纪》里说“七年冬,大会兵于涿郡,将伐高句丽”。可这么多人,粮草根本不够,民夫们从家里运粮到涿郡,路上要走几个月,很多人还没到地方,粮食就吃完了,只能逃回家。
有个叫王薄的人,在长白山起义,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劝百姓别去辽东送死。歌里唱“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首歌唱遍了山东、河北,很多百姓都跟着王薄起义。

杨广听到消息后,很生气,说:“一群乱民,也敢造反!”他下令让张须陀去镇压,可心里也有点慌——百姓为什么会造反?难道是自己征调得太急了?可他又想,高句丽不除,北方就不安定,就算百姓有怨言,也得先平定高句丽。他在涿郡的宫殿里,每天都看军报,盼着能早日出兵。
大业八年(612年)正月,杨广下令进军高句丽。来护儿率水军从东莱出发,攻平壤;宇文述率陆军从涿郡出发,向鸭绿江进军。可高句丽早就做好了准备,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起来。隋军深入高句丽境内,粮草很快就不够了。宇文述的军队走到萨水,高句丽的将领乙支文德假装投降,骗宇文述继续前进,然后在萨水设下埋伏。
隋军过了萨水,刚走没多远,高句丽军就从两边冲出来,隋军大乱,纷纷逃跑。萨水被尸体堵住,水都流不动了。这次出征,隋军损失了几十万兵力,来护儿的水军也打了败仗,只能撤军。

消息传到杨广的营帐里,他手里的杯子“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摔碎了。他坐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脸色苍白。夜里,他翻看战报,看到“死者数十万”几个字,把奏折扔在地上,说:“此非朕之过,乃诸将不力也!”可他心里清楚,是自己太急了,没做好准备就贸然出兵。那一夜,他没睡觉,坐在灯下,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又羞又怒——他这个曾经平定江南的晋王,竟然败在了高句丽手里。
大业九年(613年),杨广不甘心失败,又下令二征高句丽。这次他亲自率军攻辽东城,指挥士兵用云梯、撞车攻城,可辽东城的城墙特别坚固,隋军攻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攻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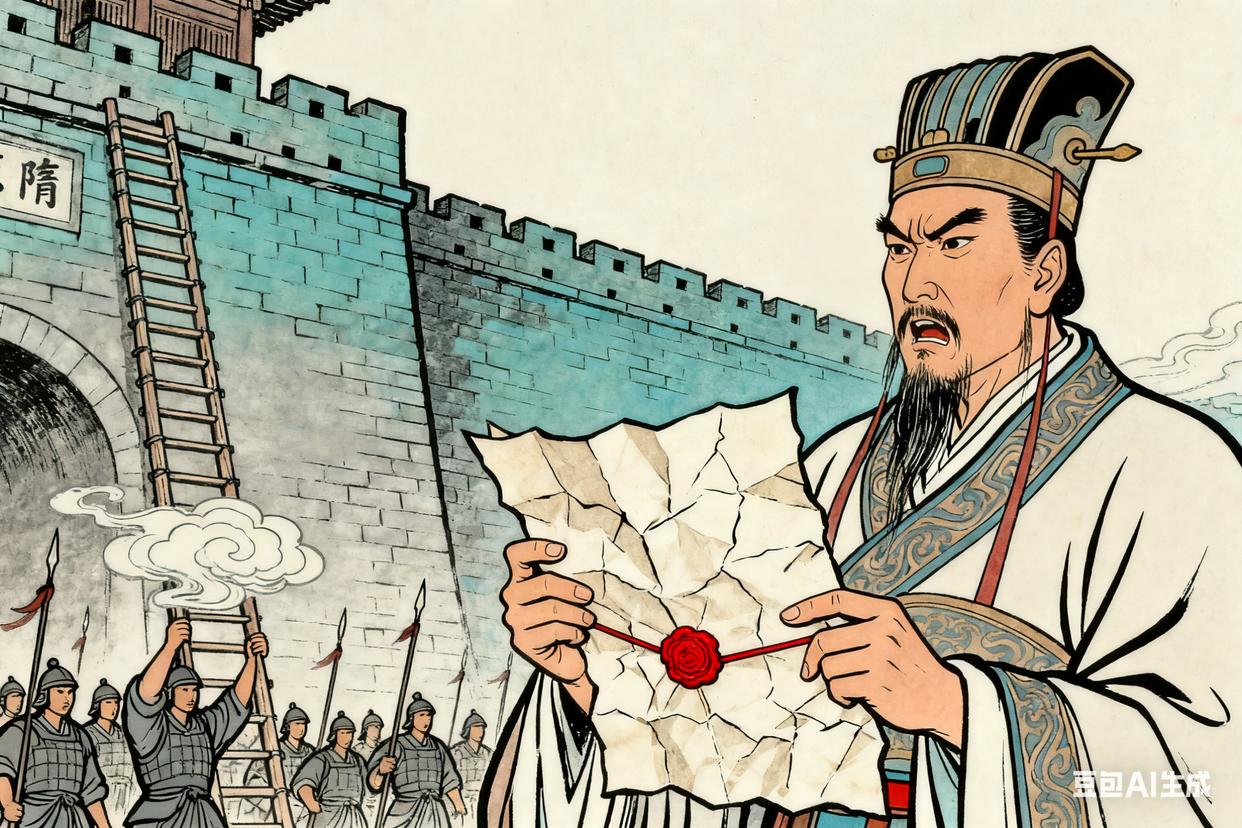
就在这时,后方传来消息: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了!杨玄感是杨素的儿子,官至礼部尚书,他看到百姓困苦,觉得杨广暴政,就趁机起兵,还招揽了很多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消息传来,杨广的手都抖了——杨玄感是自己的亲信,竟然会造反!他马上召集大臣,说:“杨玄感竖子,敢坏朕大事!朕要回师镇压,等平定了他,再回来攻高句丽!”
宇文述率军回师,很快就把杨玄感的起义镇压了。杨玄感战败自杀,杨广下令严惩参与者,杀了三万多人,连杨玄感的族人都没放过。有个官吏向杨广进言,说这些人大多是被逼无奈,求陛下开恩。杨广却怒了:“敢反朕者,必如此下场!要是不严惩,以后还有人敢造反!”
可杀了这么多人,杨广心里也不好受。夜里,他让宫女念《离骚》,听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时,他叹了口气,对萧皇后说:“朕是不是太狠了?可要是不狠,这江山就保不住了。”萧皇后没说话,只是给他递了一杯茶——她知道,杨广心里的苦,没人能懂。
大业十年(614年),杨广决定三征高句丽。这时候,隋军的士气已经很低落了,很多士兵都不想去,在路上纷纷逃跑。可杨广还是坚持要去,他说:“朕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平定高句丽,挽回大隋的颜面。”
来护儿率水军再次攻平壤,这次高句丽也撑不住了——连年征战,高句丽的国力也耗尽了。婴阳王高元遣使求和,愿意称臣。杨广接到消息后,心里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攻下平壤,但高句丽投降了,也算是赢了。他下令撤军,回师洛阳。

可在回师的路上,杨广看到沿途的百姓流离失所,田地都荒了,很多人在路边乞讨。有个小孩拉着他的马缰绳,说:“陛下,给我点吃的吧,我爹娘都饿死了。”杨广让身边的人给小孩粮食,可心里像被刀割一样。他问身边的大臣:“天下何以至此?朕只是想平定高句丽,让边疆安稳,怎么会变成这样?”大臣低着头,不敢说话——他们知道,是杨广的频繁征调,让百姓没了活路。
大业十一年(615年),杨广去北巡,没想到突厥的始毕可汗突然反叛,率几十万大军围攻雁门。雁门城里只有几万士兵,粮草也不够,杨广被困在城里,特别害怕。他抱着幼子杨杲,哭着说:“朕今日恐不得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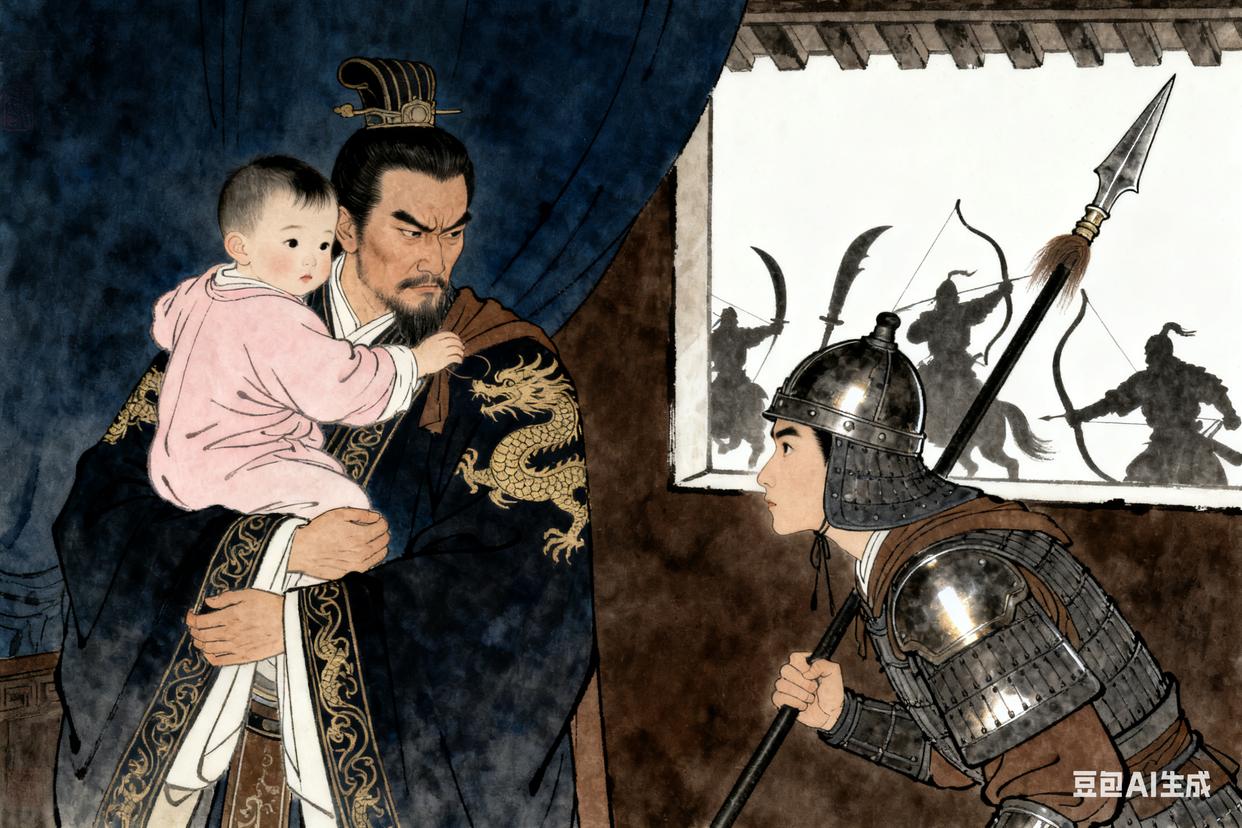
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士兵站出来,说:“陛下,突厥人善骑射,但攻城不行。咱们只要坚守待援,各地的援军一到,突厥人自然会撤。”这个士兵就是李世民,当时才十七岁。杨广听了他的话,下令募兵,还承诺只要能守住雁门,士兵们都能升官加爵。
各地的援军很快就到了,始毕可汗看到隋军援军众多,又怕后方被偷袭,就撤军了。雁门之围解了,可杨广却留下了心理阴影,再也不敢北巡了。他回到洛阳后,整天待在宫里,不想见大臣,也不想处理朝政——他怕再听到叛乱的消息,怕再看到百姓的苦难。
大业十二年(616年),中原大乱,李密、窦建德、杜伏威等人的起义军越来越壮大,攻占了很多城池。杨广不想面对这些,决定南巡江都。大臣们纷纷劝谏,说:“陛下,江都太远,要是北方有变故,陛下鞭长莫及啊!”杨广却不听,说:“外间大乱,朕且在江南乐几年,等乱平了再回来。”

他率着禁军南下,从洛阳到江都,走了几个月。沿途的百姓看到杨广的船队,都躲得远远的,有的还在路边骂他。杨广听到了,却假装没听见。到了江都,他每天都在宫里饮酒作乐,写了一首《江都宫乐歌》,里面有“求归不得去,真成遭个春”的句子——他其实也想回洛阳,可他知道,回去了也没用,中原已经不是他的了。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率军西进,很快就攻占了长安。李渊立杨广的孙子杨侑为皇帝,自己做了大丞相,掌握了实权。消息传到江都,杨广正在宫里跟萧皇后喝酒。他听到消息后,手里的酒杯停在半空,半天没动。过了一会儿,他笑了,对萧皇后说:“朕不失为长城公(陈叔宝),卿不失为沈后。”萧皇后哭了,说:“陛下,咱们还有禁军,不如回长安,跟李渊拼了!”杨广摇摇头:“没用了,朕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他们早就想回家了,没人会跟朕拼的。”

从那以后,杨广更消沉了。他每天都喝得大醉,有时候还对着镜子自言自语:“好头颈,谁当斫之?”萧皇后听到了,哭着说:“陛下,您别这么说!”杨广却笑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朕做了一辈子皇帝,也够了。”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江都的禁军将士思乡心切,再也不想待在江南了。宇文化及、司马德戡等将领趁机发动兵变,率军攻入宫中。杨广听到动静,从床上爬起来,想找地方躲,却被士兵们找到了。
他看着士兵们手里的刀,平静地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可士兵们没有鸩酒,只是拿着绳子看着他。杨广解下自己的腰带,递给士兵,说:“朕乃大隋天子,就算死,也要死得体面。”士兵们用腰带把他缢杀了,死的时候,他才五十岁。《隋书・炀帝纪》里记载:“十四年三月,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等作乱,帝崩于江都宫。”

杨广死了,大隋也亡了。可他开凿的大运河,却一直流淌到今天。现在的大运河,已经成了世界文化遗产,两岸的百姓靠着它灌溉、运输、旅游,过着安稳的日子。有人说杨广是暴君,因为他的雄心让百姓吃了太多苦;也有人说他是有远见的帝王,因为大运河连接了南北,促进了中国的统一和发展。

就像杨广当年常带在身边的那柄玉柄麈尾,在江都之变时掉在了地上,被一个宫女捡起,后来传到了唐朝,现在成了文物。麈尾上的玉柄已经磨损了,可上面的纹路还能看清——那纹路像极了大运河的河道,弯弯曲曲,却一直向前。

我们今天回望杨广的一生,会想起他年轻时平定江南的意气风发,想起他开凿大运河时的雄心壮志,也会想起他晚年的落寞和悲剧。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理想再伟大,也要考虑现实的条件,也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就像我们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不能只想着自己要什么,还要想想身边的人,想想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影响。只有平衡好理想和现实,才能走得更远,才能不留下遗憾。
声明:本故事为文学创作,非历史研究。读者需区分虚构与史实,深入了解历史建议查阅专业资料。未经书面许可,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擅自复制、转载、改编、传播等,亦不得用于商业用途,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