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的故事在我国民间渊远流传,千年以来被改编成了无数个版本,在不同的载体上反复传播。王昭君也因此而名垂青史,受到历朝历代文人雅士的推崇。她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所谓”沉鱼落雁“中的“平沙落雁”,形容的便是王昭君在马背上弹奏枇杷的情景。她嫁给南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为汉匈和平共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成为我国古代史中外交层面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本来是有机会回到汉朝的。可是在她上书汉成帝刘骜提出归汉请求时,却遭到了拒绝。

王昭君出塞是在汉元帝刘奭的晚期,也是在西汉对匈奴取得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大胜之后。前文讲过,在昭君出塞之前,匈奴内部爆发了五单于争位的内乱,内乱中分裂成为南北两部。北匈奴为郅支单于统领,南匈奴为呼韩邪单于统率,两人都是虚闾权渠单于的儿子。两部匈奴内战不休,呼韩邪单于在战争中落败,只能带着部下南迁至长城附近,依附于汉朝谋求生存。郅支单于则占领了西域,与康居国结盟,阻断了丝绸之路,劫杀了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于是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都护陈汤矫诏出兵,消灭了郅支单于,恢复汉朝对西域的统治。

这场大战之后,汉朝重新在西域建立了无上的威信,得到了西域诸国的拥戴。各国纷纷派遣使者到长安进贡,并留下质子以表示臣服。呼韩邪单于得到消息后亲自来到长安,并上书汉元帝刘奭表示愿意迎娶汉朝公主为妻。于是刘奭下诏在宫女中选拔了王昭君,并以公主的名义下嫁给呼韩邪单于,这才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后,两人生活了三年,育有一子,名叫伊屠智伢师,是南匈奴的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去世时,王昭君的儿子不到三岁,此时汉元帝刘奭已经去世,汉成帝刘骜刚刚继位一年多。

此时王昭君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儿子也不大,回到汉朝依然能够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她上书朝廷请求归汉的意愿却没得到允许,收到的是汉成帝刘骜关于“从胡俗”的诏令。也就是说,呼韩邪单于去世后,王昭君在南匈奴的地位按照匈奴的风俗进行处置。
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时,汉元帝刘奭赐名为宁胡阏氏。阏氏是匈奴单于的正妻,王昭君当时在匈奴的地位就相当于王后,带上“宁胡”是朝廷希望她能够在汉朝和匈奴之间完成主和的政治任务。可是呼韩邪单于去世后,他的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继位,王昭君原来在匈奴中的地位就不存在了。

虽然作为前阏氏依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毕竟无法与当政者相比,也很难左右匈奴的政策路线,起到与汉朝和平共处的作用。而且王昭君的儿子还小,虽然地位很高,但无法插手匈奴政治,所以她在匈奴政权中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面对这种情况,王昭君提出归汉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汉成帝刘骜的诏令却让她“从胡俗”,也就是按照匈奴人的收继婚制执行。所谓收继婚制,就是匈奴的单于去世后,她的妻妾可以嫁给继任单于。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婚姻制度,与汉朝文明的礼法和传统是相违背的。

从汉朝礼法上来讲,王昭君是呼韩邪单于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的继母。以继母的身份嫁给继子,在汉朝是绝对不行的,而匈奴却是可以承认的婚姻状态。这种违背汉朝礼法的荒唐诏令居然下发到了匈奴,王昭君顿时陷入了窘迫之中。但她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不得不依照诏令嫁给了复株累若鞮单于。此后和复株累若鞮单于生活了十二年,生了下两女,长女名须卜居次,次女名当于居次。复株累若鞮单于去世后,他的弟弟搜谐若鞮单于继任,王昭君又在匈奴生活了两年,最后以病逝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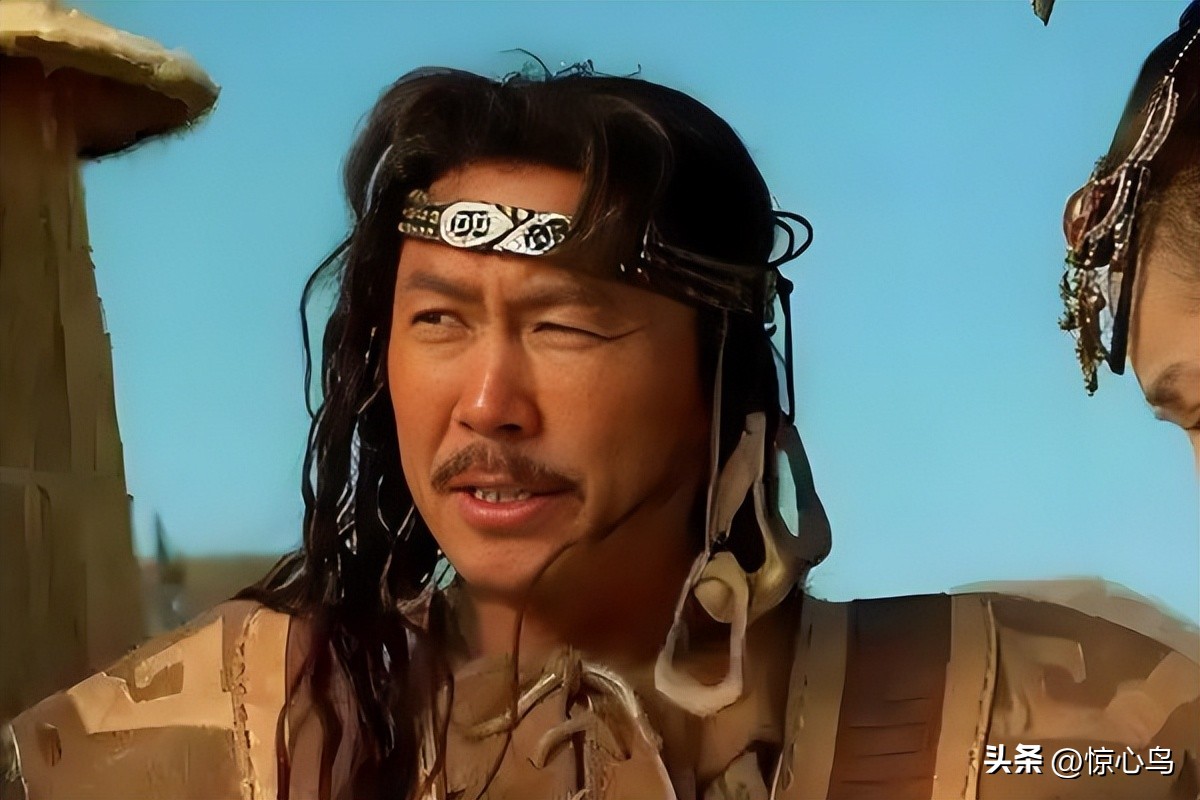
可以说汉成帝刘骜的一道诏令决定了王昭君的人生,让她出塞后终生没有回到汉朝,最终病逝在匈奴草原之上。对于王昭君的美丽,古代文人们竞相写诗称颂,其中尤以宋朝名相王安石的《明妃曲》最为著名。但是对于王昭君“从胡俗”改嫁给呼韩邪单于的两个儿子,最终病逝匈奴草原的结局,后世的文人也感到唏嘘不已。在大多数人看来,既然王昭君是汉朝公主的身份嫁到匈奴的,就不应该承担这样的结果。呼韩邪单于已经去世,即便需要继续和亲,汉朝也应该另外找人,而不是搞这种“从胡俗”的,野蛮的婚姻来绑定王昭君。

实际上从当时的汉朝历史背景来看,汉成帝刘骜下给王昭君的诏令,其实是汉朝内部权贵阶层的共识。前文讲过,汉朝内部的权贵阶层对于边境的安全是不太关心的。一方面是边境距离汉朝腹地太远,这些地方的利益与权贵阶层无关。另一方面是维持边境的和平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财富,而边境地区又比较贫瘠,所以各种消耗都需要从中原腹地调取。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让汉朝腹地的权贵们承担这么大的消耗,他们都是不太乐意的。因此对于边境的问题,除了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病已等少数比较强势的皇帝,汉朝大多采取保守的处理方式。

这样对待边境事务的政治逻辑,在汉元帝刘奭时代贾捐之上书放弃海南岛珠崖郡的事件中就已经表现得淋漓精致了。所以在面对北匈奴郅支单于独霸西域的战略形势时,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都护陈汤只能采取矫诏的方式出兵,而不能走朝廷的正常流程。因为他们都知道,走正常流程得到的肯定是不准出兵的诏令。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不只一起,西汉最后一位名将冯奉世平定西域莎车国之乱,也是采取的矫诏方式。由此可见,除了汉武帝刘彻等少数皇帝当政之时,大多数由汉朝权贵主导的朝廷中,对西域和匈奴都是采取回缩的外交策略。

汉成帝刘骜不是强势的皇帝,而且汉朝有名的昏君。他执政期间把所有的朝廷大权都交给了以大将军王凤为代表的外戚集团,形成了典型的权贵政治体系。在当时依附于王凤的朝廷官员中,不论是杜钦这种贵族子弟,还是王尊、谷永等士大夫之流,亦或是与王家同盟的史丹、刘向等皇亲国戚,都是对边境事务漠不关心的。他们更关心的是朝廷中的利益分配,实际上就是中原腹地的权力分配和家族利益。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汉成帝刘骜时代的汉朝朝廷实际上对外事务是非常懦弱的,不仅削减了边境防卫的开支,而且减少了对外族的控制。

在王昭君请求归汉的事情上,汉朝朝廷的态度非常统一,那就是千万不能回来。王昭君回归汉朝,对于她个人而言是如释重负,但是对于边境地区是很大的灾难。一方面,她的回归必然影响到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她的儿子伊屠智伢师不到三岁,如果跟着回到汉朝,必然会引发汉匈之间的政治猜忌。匈奴方面很可能就怀疑汉朝有另立单于的打算,政治上对汉朝的防备和敌视增加,这不利于边境的和平。当然如果是汉武帝刘彻在位,以他的雄才大略,恐怕会很好的利用这个匈奴王子,从政治上瓦解匈奴内部,而不是单纯的牺牲王昭君。

即便王昭君把儿子留在匈奴,她的回归也会引起很大的麻烦。前文讲过,王昭君到匈奴其实有着推动汉匈融合的意思,也承担了很多汉化匈奴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汉朝对王昭君投入很多,对匈奴也赐予了大量的汉朝事物,以改变匈奴的风俗文化,使之向汉朝靠拢。但是这样的情况被汉成帝刘骜一道“从胡俗”的诏令给打破了,也将王昭君多年的功绩毁于一旦。由此可见,从汉成帝刘骜继位开始,汉匈边境上民族融合的进程已经停下了。汉朝已经放弃了通过民族融合,逐渐达到将匈奴纳入汉朝版图的计划。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果王昭君彻底回归,汉朝必然将失去对匈奴的主动联络。没有了这根线牵着匈奴,汉朝朝廷失去对匈奴的控制,在战略上是处于绝对劣势的。但朝廷方面又不愿意在这上面过多的投入,怕让权贵阶层的利益受损,所以干脆牺牲王昭君,以延续汉朝和匈奴的和平时期。这种做法和汉朝初年汉高祖刘邦的和亲是一回事,都是一种非常屈辱的,丧失了国家政治立场的行为。站在国家的尊严角度,王昭君下嫁给呼韩邪单于的儿子,本质上是对汉朝极大的侮辱,也使得汉朝边境军民多年的努力化为乌有。

最为可笑的是,从汉宣帝刘病已时代开始,儒家学术思想在朝廷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儒家学术里面,仁义礼智信是一位儒者最为基础的做人行为准则。可是面对王昭君请求归汉的事情,朝廷中的权贵阶层们一言不发,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全部丢到了爪哇岛,心中只剩下家族利益和蝇营狗苟。这件事可以证明,此时的汉朝朝廷已经不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时代积极向上发展的状态,而成了一群伪君子瓜分国家利益的餐桌。他们牺牲王昭君,不过是为了给瓜分国家利益延续时间,这种情况也说明汉朝的大劫难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