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欧比运动”,是阿拔斯王朝时期的波斯民族主义运动。因“民族”一词阿拉伯文作“舒欧布”(Shu‘ub,舒欧比叶),故名。8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古老的波斯文化传统曾对居统治地位的阿拉伯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发生一定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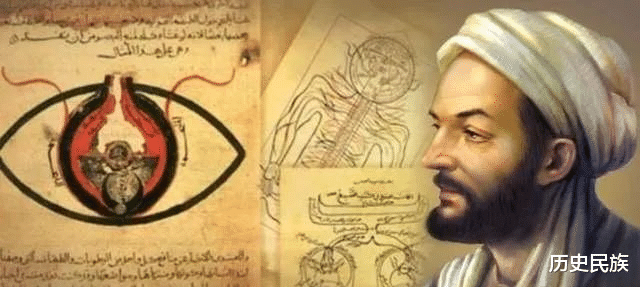
但作为政治语言和宗教语言的阿拉伯语,仍非帝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语言,阿拉伯文化仍被非阿拉伯人视为外来文化。10世纪以后,由于统治者继续奉行阿拉伯化、伊斯兰化政策,引起非阿拉伯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以文学、诗歌的形式,批评阿拉伯贵族的种族优越感,尤以波斯文化界为甚。民族主义运动由比鲁尼等著名作家飞科学家发起,他们在著述、创作中强调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一律平等、亲如手足,抨击阿拉伯贵族的专横跋扈,认为非阿拉伯人在文学、科学、文化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不应受制于人。运动虽遭到伊本·古太白等波斯学者的抵制,仍产生很大影响。舒欧布运动在反对阿拉伯种族至上的同时,仍主张以《古兰经》和圣训为立国之基础,从而肯定了作为宗教语言的阿拉伯语的地位,但阿拉伯语不单被视为一种民族语言,同时又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的哲学、科学、文学和文化的语言。这种带有泛伊斯兰文化色彩的文化运动,因强调各族一律平等,亦称“多民族主义运动”。
波斯学者伊本·穆加法将印度的梵语典籍《五卷书》,从古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并按照世人的习俗予以改编和加工,取名为《卡利莱和迪木乃》。该书以动物世界比喻人类社会,阐述了作者的伦理观念和处事原则以及改革社会和治理国家的政治抱负,开创了伊斯兰世界艺术散文的先河。
在其《近臣书》一书,以哈里发身边的大臣为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各方面的问题,其他著作《大文学》和《小文学》也包含了揭露社会现实的内容。波斯籍文士杜尔突什的《帝王明灯》等阿拉伯文学作品中充满了波斯文化色彩。
此外,曾对东、西方各国文学、音乐、戏剧、绘画等文艺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阿拉伯民间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这部著作的故事主要来源之一是古代波斯地区的故事,其蓝本是古波斯文的《一千个故事》。后来增加了阿巴斯时代的传闻轶事和民间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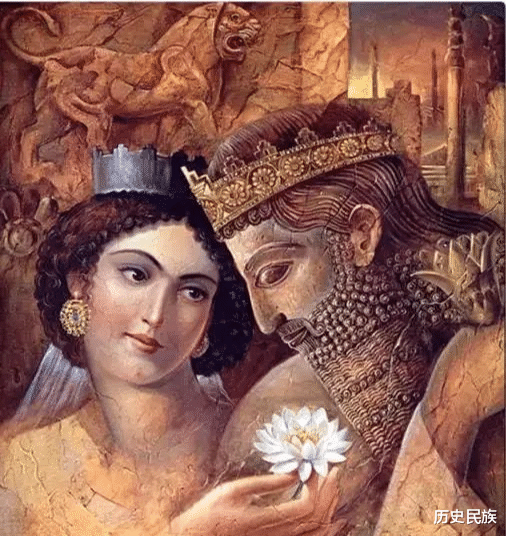
该书原本在民间口传,10世纪由巴格达人海什尔整理成书,15世纪时最终成型。该书构思奇妙,语言优美,情节曲折,生动地展示了该时期伊斯兰世界社会生活的斑斓画面。其时,帝国内各民族人民的频繁交往,促进阿拉伯人与被征服民族的融合,尤其是波斯人在与阿拉伯人的交往过程中,将波斯的社会习俗带入到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中。
“舒欧比”文学运动反映了波斯人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影响力的扩大,也是两大文化深层次互动的突出表现。“舒欧比叶”之名源于古兰经第49章的一节经文,在阿拉伯语中,“舒欧比叶”意为人民或民族,在历史学家艾敏眼中,此次社会思想运动主张民族平等,阿拉伯人并不优于其他民族,实质上是提倡民族平等主义;希提将该思潮称为“多民族主义”。简言之,舒欧比叶者主要依靠伊斯兰教义中的平等理念,宣扬帝国内各民族平等无异。在后期,超越了民族平等的主张,逐渐倾向于贬低阿拉伯人在文学领域的地位,标榜波斯文化的优越性。不止如此,鉴于波斯悠久的历史和许多波斯人对马兹达克信仰挥之不去的依恋,“舒欧比叶”运动也暗示着对伊斯兰教地位的挑战。
显然,“舒欧比叶”运动不仅贯穿了民族平等的思想,而且是波斯人表达政治诉求的方式。波斯人政治诉求背后反映的是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具体而言,被征服民族在皈依伊斯兰教后,希望与阿拉伯人享有同等的社会地位,但事与愿违,阿巴斯王朝统治者仍以阿拉伯人为中心,实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在阿巴斯哈里发曼苏尔统治时期,一些阿拉伯人反对呼罗珊的波斯籍管理者和学者担任官职,许多来自于呼罗珊的波斯管理者和学者担任各级官职,但却遭到一些阿拉伯人的反对,称波斯人为阿贾姆(意为哑巴或笨蛋)。波斯人,尤其已担任各级官职的波斯人,自恃文化素养深厚,不肯屈居于阿拉伯人之下。波斯人通过舒欧比叶运动为其身份及波斯文化辩护,以抵御阿拉伯沙文主义。
波斯民族主义者将帕拉维语的波斯书籍译为阿拉伯语版本,并用阿拉伯语创作包含爱国情感的作品,以证明波斯文化的优秀,颂扬波斯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从文化层面抵抗波斯舒欧比叶者的影响,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文人学士也积极创作诗歌,以提醒阿拉伯人作为亚伯拉罕启示的接受者和伊斯兰帝国的缔造者的优越身份。
“舒欧比叶”运动对阿巴斯帝国统治下两大民族的思想文化交融意义深远。
其一,该运动为双方对自身和对方的文化进行审视提供了契机,促进了两大民族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这是因为,“舒欧比叶”运动引发了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在文学领域的激烈论战,双方创作了大量文学论争作品,一方面,经由波斯人的抨击与批判,阿拉伯人不仅对自身历史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和洞察,更开始认真审视和借鉴波斯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为证明波斯文化的优越性,波斯学者和官员积极寻觅和搜集前伊斯兰时期波斯文化的素材,这些学术研究工作,间接加深了波斯人在社会文化层面对阿拉伯人的影响。进而言之,得益于“舒欧比叶”运动的开展,尽管阿拉伯人指责波斯人的舒欧比叶运动有诋毁伊斯兰教先知之嫌,但波斯文化影响力的日益扩大以及两大文化的互动和交融,却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于是,“舒欧比叶”运动成为文化碰撞、互动和创造力的象征。
其二,该运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帝国统治者的政策方向,对营造一个更为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和开放多元的文化氛围意义重大。具体而言,阿巴斯人摒弃阿拉伯人的民族优越原则,在帝国内部确立穆斯林之间的平等关系。这种平等和包容精神进而延伸至政治领域,统治者将效忠于己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什叶派纳入帝国统治体系。哈里发麦蒙深受该运动的影响,指定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穆萨·里达为哈里发的继承人。无怪乎有学者认为:这些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继承征服者的意志,将阿拉伯帝国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其三,该运动虽发生于8—9世纪的阿巴斯王朝时期,但事实上,其影响范围波及至整个伊斯兰世界。11世纪,居住在巴伦西亚的西班牙裔穆斯林伊本·加西亚借鉴波斯人的“舒欧比叶”运动成果,创作了自己的“舒欧比叶”文学作品,以反抗西班牙长期存在的阿拉伯沙文主义。
阿拉伯语是阿拉伯文学的基础,其时阿拉伯文学的繁荣发展也离不开阿拉伯语中丰富的词汇。在阿拉伯帝国时代,精通阿拉伯语语法、修辞学和诗歌对于文人学士而言至关重要。在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语是半岛区域内阿拉伯人的部落方言,伴随着阿拉伯的军事征服,其传播范围也逐渐扩大。由此可看出阿拉伯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扮演了宗教语言的角色,而且在倭马亚时代成为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府语言,在阿巴斯时代也成为了学术活动研究的语言。
结语尽管其他语言在国内仍有重要意义,例如中古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但在翻译运动期间,阿拉伯帝国的学者用阿拉伯语创造一种新的文学繁荣。到了9世纪,即使是反对伊斯兰教或阿拉伯人的舒欧比叶运动中的文学作品也必须用阿拉伯语写作,才能在帝国内部传播,扩大其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