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中国妇女报

杨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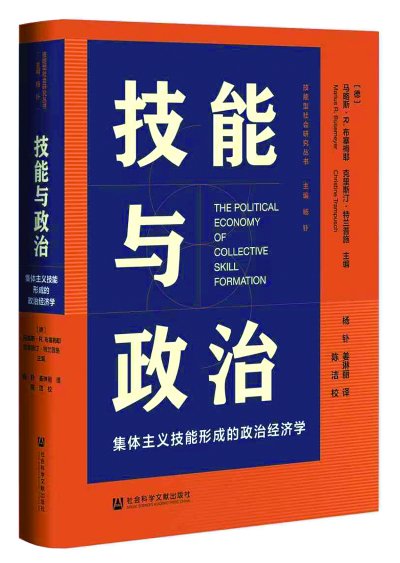
·谈谈提示·
如今,职业教育正在成为重新塑造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力量。但职业教育并不天然中立。它既是培养技能的场所,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深层的性别分工与结构。北京大学杨钋教授团队的译著《技能与政治:集体主义技能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为各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探寻该著作的理论精髓和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日前专访了杨钋教授。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杨舒羽
《技能与政治》的核心价值与实践思考
记者:《技能与政治》于2012年结集出版,对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和丹麦的职业培训进行了深入研究。此书讨论的议题在今日仍具有现实意义吗?书中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对您有什么影响?
杨钋:《技能与政治》的核心是讨论不同经济体如何解决政府和市场在职业培训中的分工,尤其关注政治体制、政策机制对有效技能形成的作用。这些问题是国家技能形成制度和职业教育培训体系设计的核心,且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密切相关,因此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此书采用比较政治学中的历史制度主义视角,采用过程追踪和跨案例分析等方法。我在职业教育研究中多次采用,这些方法有助于基于案例研究发展理论,提升了我的理论分析能力。
记者:您初次接触此书是2014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访学期间。此书让您对国内职教有了新认知。具体解开了您哪些相关谜题?您又由此形成了哪些新认知?
杨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向德国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澳大利亚TAFE模式、美国社区学院等多国学习职业教育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很难有效移植到中国。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和职业教育制度并非孤立,而是深深嵌入生产体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关系等在内的制度网络中,它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历史制度和文化因素制约的产物。从一个侧面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因地制宜探索本国职业教育发展之路。
记者:《技能与政治》前后耗费十年时间翻译完成,您认为它是最有价值、最值得与中国读者分享的佳作之一。它的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杨钋:该书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跨学科视角提出了新的研究议题,即为何国家技能形成体系具有多样性?如何解释这些多样性?这些问题把职教体系建设从实践层面提高到理论层面,直接推动职教区域国别研究发展为新的研究领域。二是创新研究范式。该书将抽象的理论讨论还原到各个国家的历史现场,通过历史案例剖析现实相关问题,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三是具备现实参考意义,它有助于理解发达工业化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帮助我国从人口大国发展为人力资源强国。
记者:该书聚焦“协调型市场经济”国家的集体技能形成体系。这种体系促成了低青年失业率与高质量职业技能的共存,进而提升经济体的竞争力。这对我国相关政策有何启发?
杨钋:降低青年失业率、提供高质量职业技能,是我国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集体主义技能形成体系的优势在于在中等教育阶段提供高质量的校企合作技能培养方式,并通过与高等教育的衔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当前应该继续保持中等教育的多样性,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项目。这样有助于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提高高职院校和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同时提高毕业生的技能认同感和技能水平。
不同职教体系中的性别差异与成因
记者:德国女性在双元制中集中于健康/教育等低薪职业,而在工业技术岗位占比不足5%。这种职业隔离是制度设计还是文化传统的产物?
杨钋:德国教育体系的职业导向极强,这种导向意味着分工的早熟与分层的固化。学徒制项目的性别集中非常明显:工业、机械、信息技术等领域几乎被男性垄断;而女性更多地聚集在护理、教育、社会服务等行业。表面上看,这是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这种“选择”早已被制度化的教育分流所框定。德国的职业培训模式在形式上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企业为核心的学徒制,另一种是以学校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前者偏向制造业和技术岗位,后者则集中于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等通用性岗位。正因这些岗位的“技术折旧率”较低,即使女性因家庭和育儿暂时离开职场,技能价值也不会迅速贬损,因此女性更倾向于选择这些相对“安全”的路径。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为女性提供了稳定的就业通道,但也无形中巩固了职业的性别分隔。德国的学校型职业教育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带有“性别化考量”,在其结构上为女性提供了“体面而可回归的职业”选项。甚至在高等教育层次,德国也是唯一一个通过非大学体系来培养卫生与福利领域人才的国家,而女性正是这些专业的主体。换句话说,职业的性别隔离并非偶然,而是制度分工的产物,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德国社会长期形成的文化逻辑。从性别平等视角看,这无疑在延续“现代外衣下的传统性别秩序”。
记者:丹麦通过学校培训整合职业教育,使女性高等教育参与率达60%。这种模式如何平衡技能通用性与职业专用性?
杨钋:丹麦的教育体系用制度设计告诉我们:技能培养可以兼顾职业效率与性别平等。高中阶段的教育体系由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共同构成,其中普通高中占比超过一半。普通教育更强调通用性知识和跨领域能力,天然具备较强的性别中立性,对女性而言,这意味着更多的选择、更高的流动性,不会被过早地“定型”为服务业或照护岗位的候选人。即便在职业教育内部,丹麦女性也更多选择商业、服务业和家庭经济学等领域,这些领域同样强调通用性能力,而非机械性的专业技能。丹麦把职业专用技能的培养推迟到高等教育阶段,这是关键性制度安排。卫生、福利等传统“女性主导”的行业,并非在中职阶段完成培训,而是由大学承担。这意味着女性在获取职业资格的同时,也能获得高等教育的学历与资源,从而在职场上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和晋升空间。丹麦通过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分工,平衡了“通用技能”与“职业专用技能”的矛盾,让技能不再是限制女性发展的标签,而是一条通往更多可能性的道路。
职业教育性别平等的挑战与启示
记者:书中呼吁应对知识经济挑战。作为研究者,数字技能培训的性别中立是否可能?还是会再生产新的偏见?
杨钋: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重塑劳动力市场的今天,“人人都该学点数字技能”几乎成了共识。表面上,数字技能培训是一种中性的、通用的能力投资,似乎不会区分男女。如果数字培训由政府主导,或嵌入到学校教育体系中,性别差距反而可能缩小。公共财政承担成本,培训面向全民开放,学校与公共机构在规则上更具包容性。这类制度性培训能让更多女性在起点上就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数字技能机会,从而打破传统行业分工对女性的不利约束。但当培训成本由企业或个人承担时,性别偏见便悄然浮现。企业往往更愿意把培训机会留给男性员工。他们被视为更“稳定”、更“值得投资”;而女性员工即便同样胜任,也可能因为家庭责任或职场刻板印象被排除在外。个体自费培训的模式也潜藏结构性不平等:女性在收入与时间上面临更高机会成本,导致投资意愿因此下降。因此,数字技能培训的性别中立性是一种脆弱的理想。它能否实现,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并纠正市场中的性别结构。只有公共政策能提供更多财政支持与制度性保障,让培训机会真正向所有性别开放,数字化的未来才不会成为旧偏见的新载体。
记者:本书能给读者带来哪些关于职业教育性别方面的启示?
杨钋:如今,职业教育正在成为重新塑造劳动力结构的重要力量。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事实是:职业教育并不天然中立。它既是培养技能的场所,也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社会深层的性别分工与结构。
第一是看见偏见。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性别中立程度差异显著。比如,雇主深度参与的“双元制培训”,在德国被视为高效的技能培养模式,但往往最容易带有性别偏见。这种差异不仅影响培训阶段的技能积累,也在劳动市场中延续成岗位隔离与收入差距。要改变这一结构,首先必须敢于讨论偏见。从招生宣传到课程设置,从专业分布到就业辅导,都需要有意识地识别并改变性别逻辑。
第二是理解结构。职业教育的性别改革并非孤立发生的技术性调整,而是制度性的变革。欧洲多国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体系深受经济结构、福利制度与政治文化的制约。它不是一条独立的线,而是与劳动力市场、产业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紧密交织的网。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改革,必须与更广泛的社会性别政策协同推进,从育儿支持到企业文化,从薪酬透明到反歧视法制,缺一不可。
第三是要打通路径。真正有效的职业教育性别改革,不能止步于职业院校内部,它应当与高等教育相衔接,构建“性别平等的人力资本积累路径”。换言之,职业教育不只是“就业训练营”,更应成为女性突破职业天花板的“通行证”。
职业教育的性别改革,考验的不只是政策设计的智慧,更是社会能否直面偏见、拆除结构性壁垒的勇气。当教育的门真正向每一个人敞开,技能才会成为平等的起点,而非不平等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