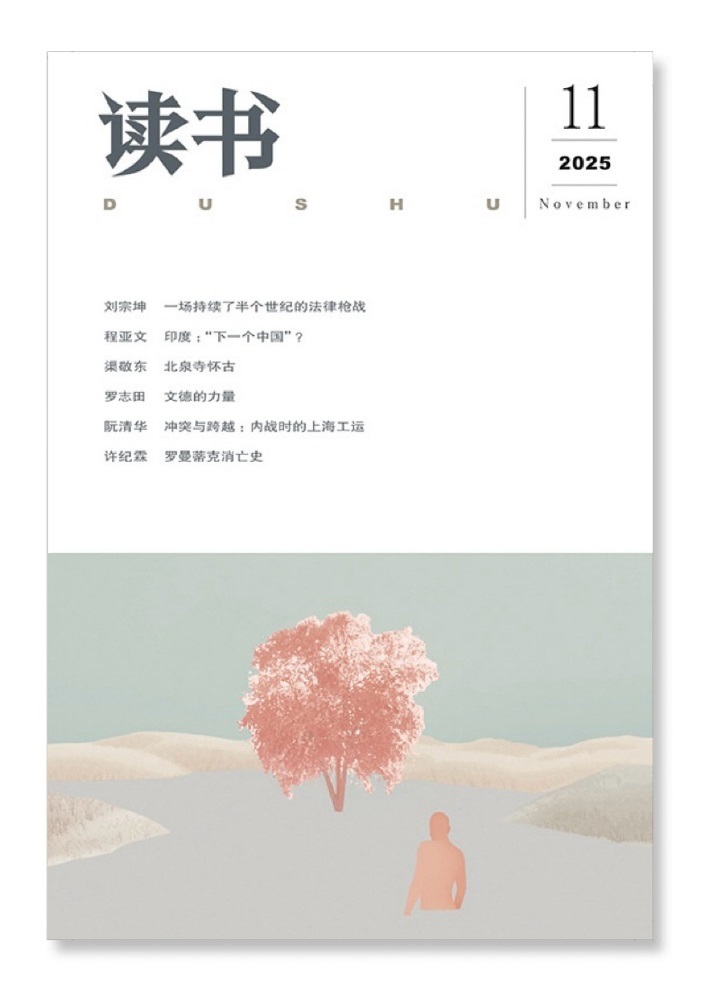【 《读书》新刊 | 许纪霖:罗曼蒂克消亡史 】 (读书杂志 2025年11月14日 17:04 ) 《罗曼蒂克消亡史》 文 | 许纪霖 (《读书》2025年11期新刊) 程耳曾经拍过一个很棒的电影《罗曼蒂克消亡史》,用它来形容当代中国男女亲密关系的流变再确切不过。罗曼蒂克是如何消亡的?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它有一个内在的自我逻辑蜕化:第一阶段是通向婚姻的至爱,第二阶段是与婚姻脱钩的爱情,第三阶段是不再相信永恒的爱情,第四阶段是不再有爱的situationship。如果用影视剧来代表的话,八十年代的琼瑶剧、九十年代的《廊桥遗梦》、二〇二〇年的《正常人》和近年来邵艺辉的《爱情神话》和《好东西》,分别代表了这四个阶段爱情的典范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琼瑶的小说和琼瑶剧所代表的古典爱情观。与好莱坞的爱情经典《魂断蓝桥》类似,其核心观念是:爱情的终点,天然是婚姻。男女主人公历经感情的折磨、外界的阻力,最后走到一起,有情人终成眷属。琼瑶的个人情感经历,也是最好的见证。她有过三段爱情,几乎囊括了三种爱情的模式:我爱的(中学语文老师蒋仁)、爱我的(大学生作家庆筠)与对齐的(皇冠杂志社老板平鑫涛)。琼瑶的一生,如同集邮一般,将古典爱情的三种模式都尝试过,惊心动魄、刻骨铭心。爱情的最后归宿必定是婚姻,不通向婚姻的爱是不真诚的,更是不道德的;爱就是一生一世、至死不渝;爱不是得到,而是付出;爱与其说是幸福,不如说是痛苦。真正的爱都伴随着痛苦,通向爱情终点的道路,不是铺满了鲜花,而是充满了荆棘,只有极致的痛苦,最后才能抵达爱的终点。 到了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现代爱情替代了古典之爱,爱情就是爱情,不再必然与婚姻发生关联,也未必以婚姻为终点。哪怕是婚外恋,只要是真诚的,不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的。一九九四年沃勒的小说《廊桥遗梦》在中国翻译出版,刮起了一股旋风。一个已婚的中年女性与周游世界的摄影师萍水相逢,瞬间点燃无比激情。尽管相信自己遇到的是一生一世的至爱,但她不再信任婚姻。如何让爱情保鲜?《廊桥遗梦》的结局残酷而美丽:萍水相逢的两个恋人永远不再见面,让美好的瞬间封存在记忆之中,永远不坏。 现代人虽然对婚姻失望,但他们依然相信爱情,相信爱情的永恒与唯一。然而,年轻一代之中弥漫的虚无主义,扫荡了婚姻,最终按照其自身的逻辑,也必定要触及爱情本身:不再相信永恒的爱情。马尔克斯的名著《百年孤独》,典范式地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爱情观:“过去的一切都是虚假,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返,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眼云烟。”二〇二〇年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萨莉·鲁尼的畅销小说《正常人》以及同名电视剧,告诉了我们千禧年一代人的爱情观:即便全身心去爱,依然为自己和对方保留自由的空间。每个人逃脱不了孤独的宿命。时代是不确定的,空间也魔幻无常,一切都在流变之中,不再相信永恒,放弃追求确定,唯一可信的,是自我的意志,是承受孤独的自救。 近年来,中国不仅婚姻率下降,而且爱情对年轻一代也失去了吸引力。爱情虽然是奢侈的,想说爱你不容易,但孤独的男女们依然需要异性的亲密,需要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和慰藉,于是,一种不再有爱的爱情模式出现了,邵艺辉的《爱情神话》和《好东西》可以视为现象级的作品。在《爱情神话》之中,她与其说创造了爱的神话,不如说解构了爱的神话,在男主与三位女性的感情戏之中,男女之间的主导权被颠覆,温情脉脉的情感背后,都只是生活的苟且、欲望的发泄和利益的考量。爱情被祛魅化了,所剩下的,只是孤独男女的相互取暖而已。而《好东西》又向前延伸了一步。戏的重心放在中年、青年和童年三代女性,没有男人,女性依然可以活得自主、自洽,那么男人的地位呢?影片中小叶有一句话,“男人还是挺好玩的”,“如果能让你开心,那就是好东西”。于是,铁梅与小马的关系只是“课间十分钟”的生活调剂,与小叶约会上床的胡医生坦承自己无法承受男女之间一段持久的、深入的关系。《爱情神话》是解构的,而《好东西》是建构的,它建构了如今在年轻一代之中相当流行的亲密关系型模式:situationship。 situationship可以翻译为“情境性的关系”,通俗一点,叫作“临时性搭子”。它与传统的亲密关系不同,模糊了友情、约会和正式伴侣的界限,以“未定义”为核心特征,既满足情感和身体的需求,又规避了明确的责任绑定。虽然年轻一代相信“智者不入爱河”,但并不意味着不渴望有另类的亲密关系。situationship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存在主义解决方案:通过亲密关系的临时状态,以消解对亲密关系终极价值的追问和确定。这种男女之间的临时性搭子,有多种模板:床搭子、饭搭子、调情搭子、倾诉搭子、聊天搭子、旅行搭子以及各种混合形态,它们都处在具体的、特定的情境当中,无法确定地定义。与一夜情不同,它有一定的固定性,但又缺乏持久的状态,更没有道义、情感上的承诺与义务,一切随情境而定,也随情境的变化而消失,在一起的时候轰轰烈烈,分开的时候了无痕迹,彼此之间无牵挂、无念想、无留恋;不具有排他的唯一性,不存在所谓的妒忌、吃醋;双方都是独立自由之身,就像两个彼此独立存在的圆,有各自的中心,只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重合在一起,仅此而已。 《中国人口报》在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的报道中提到,有56.9%的大学生表示目前不想谈恋爱。大学是男女青年青春燃烧的空间,也是荷尔蒙激荡的岁月。然而,有如此多的年轻学生对恋爱没有兴趣,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低欲望社会里,爱是一个奢侈的话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琼瑶式的古典爱情,承载了太多的东西:理想、自由、友爱、温暖、共情……想说爱你不容易,爱上了以后更沉重。如今的年轻人,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活得非常累、非常沉重,他们不希望再给自己增添新的压力,躲不了生活,却躲得了感情,何必在亲密关系当中要死要活、刻骨铭心、伤筋动骨呢?只要有情绪价值就好,像一杯喜茶、一支歌曲那样,激发我的多巴胺,给我带来快乐的情绪价值。情绪与情感不一样,情绪是表层的、临时的、不确定的,来去无踪,稍纵即逝的,转换非常之快。但情感是深层的、持久的,具有相对的确定性,相互之间有高度的依赖,更确切地说,情感与一个人的人生观有关,依附于其内心的意义结构之中。然而,许多当代的年轻人不需要情感,特别是情感当中最深刻、最揪心、最纠缠的爱情,爱情太累了,太折磨人了,他们只需要情绪,那种给自己带来瞬间快感的情绪。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人生的价值,由一连串或许是互不相关的快乐碎片连接而成。 如今在年轻一代之中弥漫的虚无主义,不仅是价值的虚无主义、理性的虚无主义,而且是情感的虚无主义,在内心的情感领域,已经被掏空了,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与感受深刻的能力。贫乏的内心,不是指理性的贫乏,更多的是情感的贫乏。一种无意义的精神状态,必定是缺乏稳定的情感底盘,而被各种各样偶然、突发的情绪所摆布。男女的亲密关系,何需亲密的绑定,何需如此的沉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轻松愉快地相处就好。所谓亲密,也只是瞬间的身体或者情绪的亲密而已,仅此而已。 古典的爱情,过去、当下和未来,有一条时间的脉络线,经历过的身体和情感的亲密,是最珍贵、值得一生回味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而未来也是值得憧憬与期待的,当下所有的一切,假如失去了过去与未来,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临时性的搭子,斩断了当下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接,当下即是一切,过去是虚妄的,未来也不必期待,最值得珍惜的,只是此刻,快乐销魂的此刻。情绪价值背后的真实底牌,正是这种情感虚无主义。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年代,年轻人也越来越保守,自觉或本能地躲避各种风险,从远离创业、争相考公、寻求稳定的铁饭碗,到情感上的拒绝投资、不愿投入真情实爱。当年的年轻一代,特别是经历过三年疫情以后,人与人之间、男女之间的连接,很多都是弱连接,是半虚拟的线上约会,是微信上碎片式的码字。有深度的恋爱好像是一种累赘和麻烦,投资太大,收益不确定。许多年轻人宁愿轻资产运行,不想投入太多,也不期待过多的收益。 今天是一个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全面介入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包括爱情,爱的表达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社交软件和算法推送主导的现代社交中,年轻人发展出“模块化亲密”的方式:情感的连接更加碎片化和象征化,用表情包和梗图替代深度对话,让大模型为自己代写情书、词曲和图像。一切都可以让AI代劳,无所不能。爱本来是一种呈现,一种表达,需要来自内心的真实情感表白来滋养。但AI出现以后,爱情只需要定制,而且可以个性化地定制。 当年轻一代越来越娴熟地操作大模型,完成各种定制的时候,就慢慢失去了爱的能力和表达能力,内心的情感生产与再生产也会变得枯竭。本来作为工具的AI,按照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规律,反过来会主宰人,掏空人的情感世界。某个脑机接口实验记录显示,受试者在与AI系统进行深度情感交互时,前额叶皮层的决策活跃度下降23%。当机器比人类更懂得如何取悦我们,当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情感需求,人类作为情感主体的独特性正在悄然流失。 (未完待续) * 原文稍长,分两次分享;点击链接,可一次阅读: ———————— *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编委。 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