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醍醐灌顶的话: “有人总是怕死,实际上,很多人活到六七十岁死掉,和活到八九十死掉的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多活二十年,只是多了一些疾病和烦恼而已。” 医生说我肺癌晚期时,我第一个念头是:“能不能让我活到七十岁?”像在菜市场讨价还价。 隔壁床的老周笑了,他肺里也长着东西,但每天雷打不动地泡功夫茶。他说:“我七十三了,多活的这三年,是给医院当全职病人。” 老周有个本子,记录每天“赚到”的事。今天写的是:“护士小陈笑起来有酒窝。” 我学着他的样子,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今天呼吸比昨天顺畅些。”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可怜,曾经规划上市蓝图的手,现在在记录呼吸频率。 化疗第三周的时候,我偷偷跑回公司。下属们正在开庆功会,因为我病倒前布局的项目赚了钱。 他们看见我,像看见鬼。新上任的副总结结巴巴地汇报工作,我听着听着,忽然发现那些曾让我热血沸腾的数字,此刻遥远得像外星信号。 在回医院的路上,我买了支棉花糖。小贩说:“老爷子,这个太甜,对血压不好。”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成了别人眼里的“老爷子”。 老周看我举着棉花糖回来,眼睛亮了。我们像两个逃课的孩子,在消防通道里分食那朵庞大的云。糖丝粘在脸上,他说:“上次吃这个,是带孙女去公园。” “后悔吗?”我问。 “后悔没早点吃。”他说。 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的生命是根橡皮筋,六十岁那年就该断了,但我硬是把它拉长到了八十岁。多出来的二十年,橡皮筋失去了弹性,软塌塌地垂着,上面挂满了药瓶、化验单和氧气管。 醒来时老周正在收拾行李。“医生说我可以回家了。”他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最后几个月,不想闻消毒水味了。” 我帮他拎包下楼。上出租车前,他忽然说:“知道吗?人活得太长,就像欠了时间的债。多活一年,多还一年利息。利息是什么?是眼花,是耳背,是对拖累子女的愧疚,是吃什么都像嚼蜡。” 他上车前塞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我的‘赚到’本子,送你了。” 本子最后一页写:“今日大赚:阳光很好,风很轻,自己走着出的医院门。” 老周走后的一个月,我也出院了。医生建议继续放疗,我拒绝了。 儿子从国外飞回来,红着眼眶说:“爸,咱们去美国治,我认识最好的专家。” 我摇摇头,递给他老周的本子:“帮我把剩下的日子,都写成‘赚到’。” 现在,我每天清早去公园看老太太们跳舞,下午在阳台养多肉。上个月还学会了弹《小星星》,虽然只能弹前两句。 昨天孙子视频问我:“爷爷,你害怕吗?” 我说:“就像你玩累了要睡觉,有什么好怕的。” 今早照镜子,发现头发长出来些,灰白的,像初春的草地。我在本子上写:“今日大赚:头发新生,像土地返青。” 窗外,一群鸽子飞过,哨音悠长。我忽然理解老周了,生命不是熬年岁,是收集光。六十岁收集的光,未必就比八十岁的暗淡。 如果现在让我走,我可以坦然地说:我这根橡皮筋,虽然没能拉到最长,但每一寸,都曾真实地、饱满地弹响过。 塞内加:“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是它有多长,而是它有多好。” 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尺是其内容的丰盈、经历的品质与精神的满足,而非单纯的时间跨度。 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 从某种角度解读,一旦领悟了生命的真谛(“道”),实现了精神上的圆满,那么即使在当日晚间死去,生命也已了无遗憾。 叔本华:“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如果多活的岁月只是在痛苦(疾病)和无聊(失去生活热情)中摇摆,那么其附加价值确实值得商榷。 西塞罗:“晚年本身就是一种疾病。” 衰老所带来的身心衰退是普遍的,无法阻挡的。 《圣经·传道书》:“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 若“尊荣”被过多的疾病和烦恼所取代,长寿的吸引力自然会下降。 大多数人的一生,基本上都在沿着既定的轨迹行走,求学、立业、成家、养育后代、经历爱恨情仇,然后在六七十岁前已然完成。 此后,生命的剧本往往进入重复或衰退的章节。 多活的二十年,如果只是在病榻上延续生理机能,或是在对过往的追忆与对当下的琐碎烦恼中度过,那么这“量”的积累,确实未能产生“质”的飞跃。 当生命的“质量”被持续的痛苦、不便和失去所充斥时,单纯追求“数量”就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这不是悲观,而是对生命历程后半段普遍现实的清醒认知。 生命的精华,往往浓缩在青壮年时期。 我们害怕的,或许不是死亡的瞬间,而是临终时发现从未真正活过的悔恨。 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去体验、去创造、去爱、去感受世界的广阔与美好。 让每一天都充实、有意义。 “不怕死”的底气,来源于“曾真正活过”的满足。 当我们能把每一个“当下”都活出应有的深度和光彩,那么无论终点在何时降临,我们都可以坦然地说:我体验了生命的丰盛,我无愧于这趟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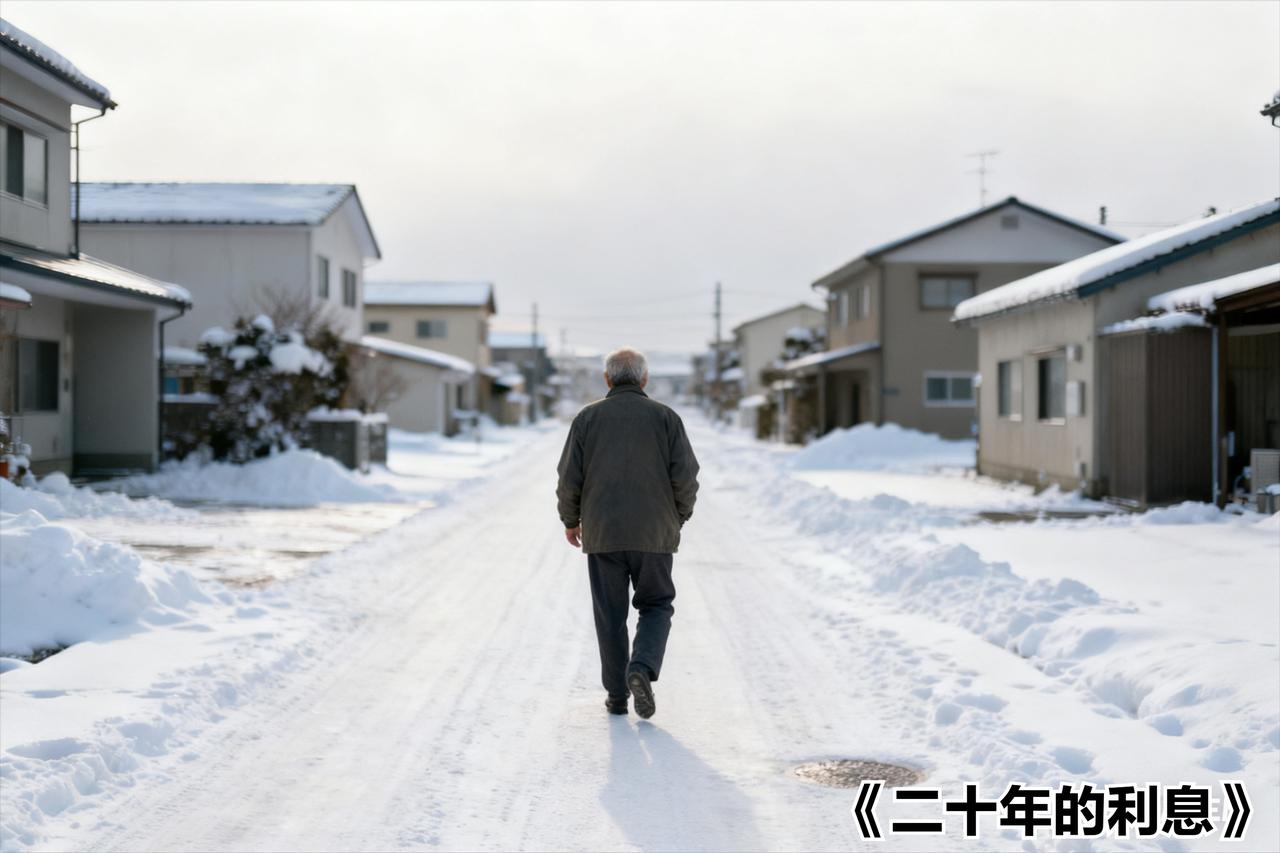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