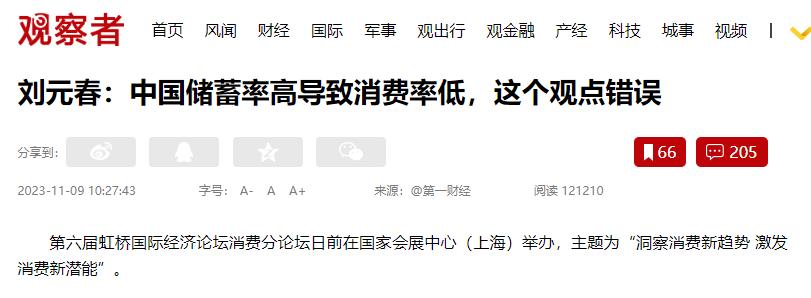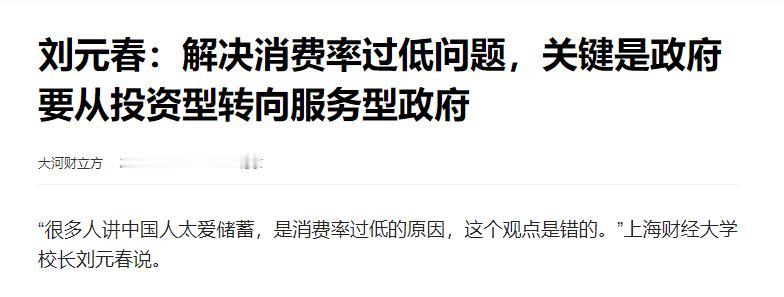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曾说:中国的消费率偏低,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不足,有人认为中国人热衷于存钱而不愿消费,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唯有将现有的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破解这一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 这一论断,简直是戳破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论调,先看一组扎心数据,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9.1%,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49个经济体里排倒数第10,在人口800万以上的经济体中更是垫底,比全球均值56.6%低了近18个百分点。 这么低的消费率,总有人怪老百姓太爱存钱,可谁不想潇洒消费?账本早就给出了答案。 2024年一季度央行调查显示,61.8%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这比例比2017年足足涨了19.5个百分点,但这可不是“热衷”存钱,而是钱包实在没底气,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43%,意味着人均GDP看似有1.3万美元,实际到居民手里的也就0.56万美元,平均每月才3800元左右,这水平连发达国家的一半都不到。 更关键的是工资增长长期跟不上经济步伐,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仅60.6%,钱没多挣,自然不敢乱花,把存钱归为“热衷”,实在是没看懂账本里的窘迫。 那老百姓的钱都去哪儿了?答案藏在那些不得不花的刚性支出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547元,看似绝对值不算高,但背后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我国再分配仅能缩小12.3%的基尼系数,连欧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教育、养老、住房这三座“大山”压着,谁不得提前存钱防身?央行问卷早就显示,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应对医疗、养老等未来支出,并非不愿消费,而是消费得起的不敢随便花,想花的又没底气,就像有人调侃的,不是不想逛商场,是房贷和医保缴费单比价签更显眼。 而问题的根子,其实在政府的角色定位上,过去投资型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确实让GDP一路狂奔,2018到2023年GDP从93万亿冲到129万亿,但代价是消费空间被严重挤压,地方政府一门心思搞基建、拉投资,却在公共服务上欠了账:国企把超额利润拿去扩产能而非给居民分红,地方财政重投资轻民生,结果就是居民要自己为教育医疗买单,消费能力自然被稀释。 反观浙江苍南的例子,投入资金搞养老服务、办消费活动,仅以旧换新就撬动7亿消费,这说明只要公共服务跟上,消费潜力立马能释放。 所以,刘元春说要转成服务型政府,真是说到了点子上,2025年出台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已经释放信号,政策重心正在从短期发消费券,转向长期补民生短板,毕竟消费券是“兴奋剂”,公共服务才是“营养餐”,如果医保报销比例再高些,养老保障再扎实些,谁愿意把钱死死存着?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同样是东亚文化圈,人家在相似发展阶段通过完善公共服务,让居民消费率稳定在48%以上,比我们现在高了近10个百分点。 说到底,提振消费从来不是让老百姓“少存钱多花钱”的口号游戏,而是要先解决“有钱花、敢花钱”的根本问题,工资水平提不上来,公共服务跟不上,再热闹的消费节也只是昙花一现。 从投资型到服务型政府的转身,本质上是把“造GDP”的重心,转回到“为人民造福利”上,当居民收入占比上去了,教育医疗有保障了,不用谁号召,消费自然会成为经济的硬支撑,毕竟对普通人来说,敢花钱的底气,永远来自鼓鼓的钱包和踏实的保障,这比任何消费刺激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