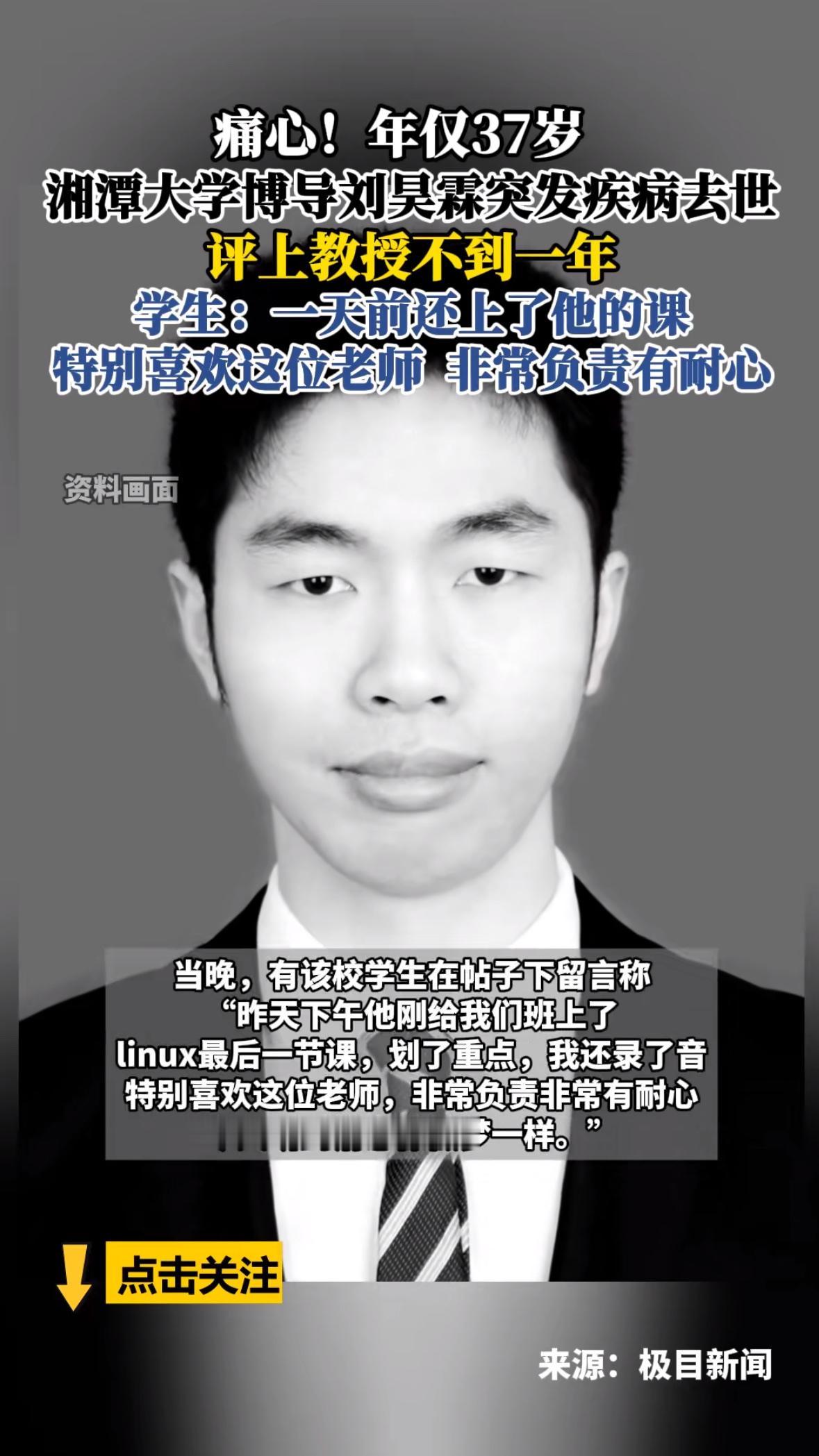“昨天下午他还站在讲台上划重点,手机里存着他最后一节课的录音,今天人就没了?”10月25日深夜,湘潭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学生群里炸开了锅。37岁的博导刘昊霖教授,在评上教授不到一年的节点,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离世。这个消息像一记重锤,砸碎了无数人的平静——那个总把“再讲五分钟”挂在嘴边,会蹲下身帮学生调试代码的老师,永远留在了2025年的秋天。 最后一课:粉笔灰还落在讲台上,人已匆匆离去 “他走得太急了。”学生小林翻着手机里存着的课堂录音,声音发颤。10月24日下午,刘昊霖像往常一样夹着教案走进教室,给本科生上Linux系统课的最后一节。没人注意到他泛青的嘴唇,也没人察觉他捏着粉笔的手在微微发抖。他照例把重点写在黑板上,又掏出手机拍了张板书照片,说“怕有同学没记全”。下课前五分钟,他突然停下敲键盘的手:“这章内容有点难,我多讲两道例题。” 可谁也没想到,这“多讲的两道题”,成了他留在人间的最后声音。第二天清晨,急救车的鸣笛划破了湘潭大学的宁静。宁乡市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记得,遗体送来时,刘教授的公文包里还塞着没批改完的硕士论文,扉页上写着“建议修改”的红笔批注,墨迹都没干透。 学术界的“拼命三郎”:37岁扛起7个国家项目 翻开刘昊霖的履历,能看见一个典型的“学霸逆袭”剧本:2006年从四川大学本科毕业,2015年拿下工学博士,同年进入湘潭大学任教。十年间,他从助教一路拼到博导,36岁评上教授时,成了全校最年轻的正教授。 但“年轻”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同事透露,刘教授的办公室灯总是最后灭的,凌晨两点的微信群里,他还在回复学生的科研问题。他主持着7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光是2024年就在顶级期刊发了5篇论文,手头的专利能铺满半面墙。更让人心疼的是,今年6月学院考核,他刚拿了“优秀教师”,9月又忙着带研究生招生——直到生命最后一天,他还在为学生的前途操心。 “他总说‘时间不够用’。”学生小周记得,有次陪刘教授去北京开会,高铁上他还在改论文,饭都没顾上吃。“现在才明白,他是把每一分钟都掰成了两半用。” 谁在透支“刘昊霖们”的生命? 37岁,本该是学术生涯的黄金期,却成了生命的终点。这让人想起去年那个倒在工作岗位上的35岁医生,想起前年熬夜写教案猝死的中学教师。我们不禁要问:当“年轻有为”变成“过劳代名词”,当“评上教授”成了用健康兑换的勋章,这样的“成功”到底值不值得? 更讽刺的是,刘教授去世的消息下,最高赞的评论是:“他带的硕士生怎么办?项目谁来接?”我们习惯用“贡献”“成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却忘了最基本的道理:再高的职称,也换不回一条鲜活的生命;再多的论文,也填不满亲人眼里的空洞。 那些在深夜亮着的办公室灯,那些没吃完的外卖盒,那些被忽略的体检报告,到底在为谁亮着?有人说这是“时代的悲哀”,可时代的车轮不该从活生生的人身上碾过。当“内卷”成了常态,当“过劳”变成勋章,我们每个人都是推波助澜的帮凶。 生命不该是“冲刺赛”,而是“接力跑” 刘昊霖教授的追悼会定在宁乡市殡仪馆,灵堂里摆满了学生送的白菊。有位老教授摸着他的遗照说:“小刘啊,你总说要在40岁前拿个国家奖,现在奖还没发,你怎么就走了?” 这句话,让在场的人集体红了眼眶。我们总爱说“等忙完这阵就休息”,可生命从不会等任何人。那些没兑现的承诺,没陪孩子去的游乐园,没和父母吃的团圆饭,最终都成了永远的遗憾。 今天,我们为刘教授的离去痛心,更该为所有“刘昊霖们”敲响警钟。你的身体不是永动机,你的生命不该是别人的KPI。从今天起,关掉电脑时说一声“明天再改”,回家路上买束花送给爱人,周末带孩子去公园放风筝——这些看似“没用”的小事,才是对抗“过劳时代”最好的武器。 最后,想问屏幕前的你:如果明天是最后一天,你会选择继续熬夜赶项目,还是陪家人吃顿热饭?评论区说说你的答案——或许你的故事,能救下一个正在透支生命的“刘昊霖”。 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