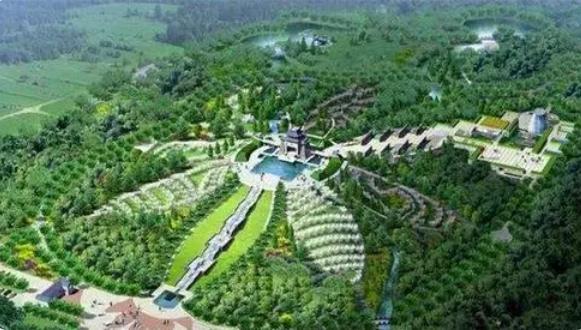看到先生的墓地选在八宝山那一刻,我浑身一激灵,什么都懂了。 之前总听他说,跟邓稼先是超越兄弟的感情。也总听他颤抖着手,对着话筒喊那句:“稼先,我懂你的‘共同途’是什么意思!” 可说实话,隔着屏幕,我哪能真懂。 直到今天。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这句约定,他花了50年去回答。 说白了,这哪是两个人的约定,这是一个民族的两个天才,在历史的分岔口,选择的两种报国路。 一个留在国内,在最艰苦的岁月里隐姓埋名,撑起了民族的脊梁。 这位喊出“共同途”的先生,正是与邓稼先同为西南联大物理系高材生的杨振宁。1945年,两人在昆明校园里并肩走过的日子,早已埋下报国初心的种子。彼时抗战刚胜利,国内科研条件极度匮乏,杨振宁遵循学界常规选择赴美深造,邓稼先则留在国内参与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备,两人虽隔重洋,却始终通过书信交换对国家科技未来的设想。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杨振宁的归国之路被彻底阻断。也是在这一年,邓稼先接到组织秘密任务,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投身于原子弹理论研究。从那一刻起,邓稼先的名字从公开文献中消失,连家人都只知道他“去外地工作”,这一“消失”便是28年。而远在普林斯顿的杨振宁,虽在粒子物理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却始终因无法归国而备受煎熬,他在写给国内亲友的信中多次提及“若有机会,必为祖国科研尽力”,这份牵挂成了他学术之外最重的心事。 1971年,杨振宁借访问新中国的机会,终于见到了阔别20余年的邓稼先。彼时邓稼先刚从罗布泊核试验场归来,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已出现明显不适,但他对核试验的细节只字未提,仅在私下交谈时对杨振宁说“我们做的事,对得起当年的约定”。直到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躺在病床上的他才通过妻子许鹿希,向杨振宁完整讲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设计到试验成功的全过程。也是在这时,杨振宁才知晓,1964年中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时,邓稼先正身处爆心23公里处,徒手检查核爆现场,用生命换取第一手数据。 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亲自撰写悼文,文中首次公开了两人“共同途”的约定。此后的数十年里,他放弃了美国的优厚待遇,于2003年正式回国定居,担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培养中国青年物理学家上。他牵头设立“杨振宁奖学金”,资助数百名学生赴美深造,却在每一次座谈中强调“学成后一定要回国,这里才是你们实现价值的地方”。他用自己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为中国引进顶尖科研资源,推动清华大学与世界一流高校的合作,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与邓稼先的“共同途”。 如今,杨振宁的墓地选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与邓稼先的墓地相隔不过百米。这百米距离,既是对两人半个世纪友谊的呼应,更是对“共同途”最生动的诠释——一个在荒漠戈壁点燃核火,一个在学术殿堂播撒火种,虽路径不同,却始终朝着“强国”这一共同目标前行。从西南联大的少年意气,到各自领域的鞠躬尽瘁,他们用一生证明,个人的理想从来都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