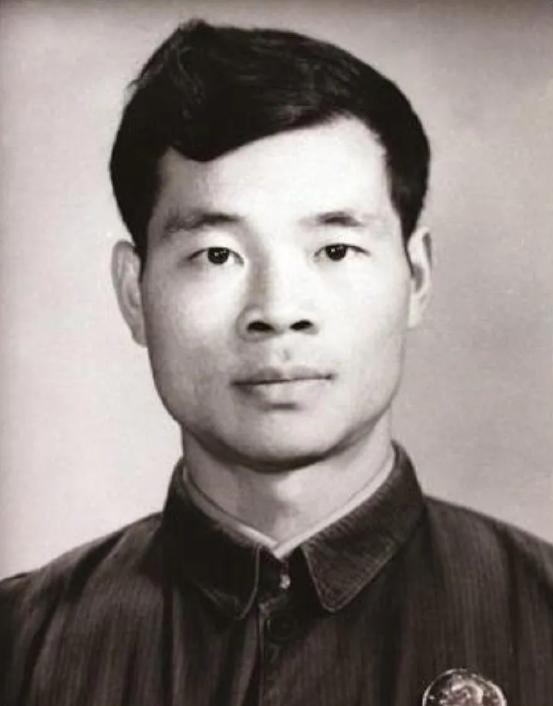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2023 年博物馆展厅,玻璃展柜里的蓝皮本泛着旧光。 扉页边缘沾着淡淡的药渍,那是 1981 年罗健夫带病记录数据时留下的。 讲解员指着药渍:“他疼得握不住笔,还是硬撑着写完了关键参数。”展柜旁,女儿捐赠的止疼药盒空空如也 —— 那是他最后几个月的 “支撑”。 参观者看着蓝皮本上颤抖的字迹,没人说话,只有轻声的叹息。 1981 年春,实验室的凳子上,罗健夫扶着桌沿慢慢坐下。 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头晕得厉害,他却只当是没休息好。 从抽屉里摸出止疼药,干咽下去,又拿起笔在蓝皮本上记录数据。 写着写着,手突然抖了一下,钢笔在纸上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他皱了皱眉,用左手按住右手,继续写,额角的汗滴落在纸页上。 1981 年夏,罗健夫趴在实验台上,胸口贴着发黑的膏药。 膏药换了一张又一张,皮肤被粘得发红,他却没工夫管。 同事进来,看见他疼得额头抵着仪器,还在说 “再测一次就好”。 “您去医院看看吧,” 同事劝他,他却摇头:“项目要紧,等忙完再说。” 话音刚落,他突然咳嗽起来,手里的记录纸飘落在地上,满是药味。 1981 年秋夜,实验室的灯光下,罗健夫的影子歪歪扭扭。 浑身疼得厉害,他只能靠在仪器上,一只手按住胸口,一只手翻资料。 胃也跟着疼,他摸出怀里的干馒头,咬了一口却咽不下去,又放回口袋。 蓝皮本摊在腿上,他用铅笔慢慢写,每写一个字都要停顿一下 —— 太疼了。 窗外的月亮升得很高,他却没察觉,眼里只有那串还没算完的数据。 1982 年 1 月,罗健夫调试仪器时,突然倒在地上。 同事们赶紧把他扶起来,发现他胸口的膏药已经渗出血迹,脸色苍白。 “别管我,先记数据,” 他挣扎着说,手指指向仪器屏幕:“那个参数很重要。” 被送到医院后,医生查出晚期淋巴癌,骂他 “不要命了”。 可他躺在病床上,还在问同事:“蓝皮本带来了吗?我还有几个数据要补。” 1982 年 2 月,医院病房里,罗健夫的手缠着绷带。 化疗让他虚弱不堪,却还是让妻子把蓝皮本带来,放在枕头边。 护士进来换药,看见他在纸上写着什么,字迹歪歪扭扭,几乎认不出。 “您都这样了,还写这个干什么?” 护士心疼地说,他却笑了:“这是我的命。” 陈显万坐在一旁,看着丈夫苍白的脸,眼泪掉在蓝皮本上,晕开了字迹。 1982 年 3 月,罗健夫强撑着坐起来,翻开蓝皮本。 他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定,让同事把数据记下来:“这个公式要再验证一次。” 说着说着,他突然咳嗽起来,咳得撕心裂肺,手里的蓝皮本差点掉在地上。 同事想让他休息,他却摇头:“我时间不多了,不能留下遗憾。”那天下午,他断断续续讲了两个小时,直到体力不支,才闭上眼睛。 1982 年 4 月,罗健夫已经很难说话了。 他用眼神示意同事翻开蓝皮本,指着其中一页,又指了指仪器图纸。 同事明白,他是在叮嘱要把数据和图纸对应上,不能出半点差错。 陈显万握着他的手,他轻轻拍了拍妻子的手,又看向蓝皮本 —— 那是他最放心不下的。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蓝皮本上,仿佛在为这个执着的人,镀上一层温暖的光。 2023 年博物馆,罗健夫的女儿指着蓝皮本上的血迹。 “这是我爸爸最后一次写数据时,不小心弄上的,” 她轻声说,眼眶红了。 孩子摸了摸那处血迹,问 “外公是不是很疼”,她点头:“疼,但他没放弃。” 参观者们看着那本沾着药渍、血迹的蓝皮本,没人说话,却都红了眼。 这本笔记,不仅是科研数据,更是一个人用生命书写的坚守。 如今,蓝皮本上的每一道痕迹,都在诉说着罗健夫的故事。 那些颤抖的字迹、淡淡的药渍、浅浅的血迹,都是他带病工作的证明。 科研人们来参观时,总会对着蓝皮本鞠躬,致敬这份永不放弃的精神。 他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是 “为理想而活”,什么是 “此生无悔入华夏”。 这份坚守,跨越半个多世纪,依旧在科研路上,为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 信息来源:华声在线——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追忆罗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