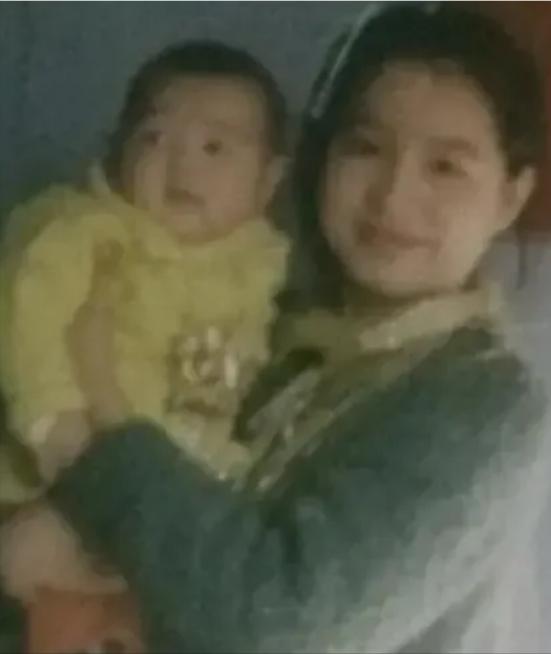[太阳]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返城,母亲怒骂:未婚先孕,不知羞耻!可得知孩子身世后,竟然抱着孩子痛哭流涕,哥哥嫂子也抢着要抚养孩子...... (信息来源:网易新闻——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回京,被母亲大骂, 晚上母亲竟说我来帮你养大) 1976 年深秋的北京火车站,寒意已浸透衣料。25 岁的邵红梅背着褪色的蓝布包袱,怀里紧紧抱着个怯生生的男孩,四岁的赵玉刚攥着她的衣角,小脸上满是对陌生世界的惶恐。 踏上熟悉的胡同青石板路时,邵红梅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顿,指尖因用力而泛白 —— 她知道,等待自己的不会是久别重逢的温情。 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母亲王氏正坐在院里择菜,枯黄的菜叶堆在竹篮边缘。抬头望见这一幕,她手里的菜篮子 “哐当” 砸在地上,萝卜滚得满地都是。 王氏的脸瞬间涨成酱紫色,声音尖利,抄起墙角的竹扫帚就往邵红梅身上挥。邵红梅下意识地将赵玉刚护在身后,扫帚柄重重落在背上,钝痛蔓延开,她却死死咬着唇,眉头都没皱。 赵玉刚吓得缩在她怀里发抖,小手揪着她洗得发白的衬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不敢掉下来。 邵红梅腾出一只手轻轻拍着孩子的背,目光掠过母亲因愤怒而扭曲的脸,落在院墙上褪色的 “上山下乡” 标语上。红漆剥落的字迹,将她的思绪拽回七年前的陕北黄土坡。 1969 年的陕西延川县赵家沟,黄沙漫过土路,连风都带着土腥味。 邵红梅刚到这里时,细皮嫩肉的手磨出了血泡,连红薯面窝头都咽不下,夜里总在被窝里偷偷抹泪。 借住的农户赵砚田和闫玉兰夫妇成了她的依靠:赵砚田黝黑的脸上总挂着笑,每天清晨会把热乎的玉米糊端到她炕头;闫玉兰的口袋里总藏着攒下的鸡蛋,趁没人时悄悄塞给她。 她下地崴了脚,赵砚田背着她走五里山路去卫生院,粗布褂子被汗水浸透,喘息声沉重却稳稳托着她。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这对淳朴夫妻的照料,是邵红梅灰暗知青生活里唯一的光。 她早已在心里把他们当成亲哥嫂,可1972年的冬夜,陕北的风刮得窗纸呜呜响。闫玉兰难产,血染红了半铺炕,最终还是没能挺过来,只留下襁褓中嗷嗷待哺的赵玉刚。 看着赵砚田抱着啼哭的孩子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哄劝,邵红梅抹掉眼泪,默默收拾了自己的铺盖搬进他们家。 从此,她白天跟着下地挣工分,晚上就抱着赵玉刚缝补衣物、哼着歌谣哄睡,把每月定量的细粮省下来给孩子熬粥,自己啃着难以下咽的糠饼。 赵砚田过意不去,几次要把家里的口粮分她些,她却笑着摇头,指尖轻轻刮了刮孩子的脸蛋,眼里满是温柔。那天起,她成了孩子的 “红梅姨”,也是名义上的干妈。 日子在黄土飞扬的劳作与孩子的笑声中缓缓流淌,赵玉刚从襁褓中的婴儿长成了会跑会跳的小不点,总跟在邵红梅身后喊 “姨”。 直到 1976 年那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连日的雨水泡软了谷仓的木梁,当邵红梅抱着最后一袋玉米往外跑时,头顶的屋顶突然发出刺耳的断裂声,让人头皮发麻。 千钧一发之际,赵砚田猛地将她推出去,自己却被轰然倒塌的横梁砸在底下。邵红梅踉跄着回头,只看见赵砚田沾满泥土的手伸向她,嘴唇动了动,最后定格在 “护好玉刚” 的口型上。 葬礼简单而沉重,黄土堆起的新坟前,赵玉刚捧着母亲生前绣的虎头鞋,小声喊着 “娘”。就在这时,知青返城的通知送到了赵家沟。 她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将赵砚田夫妇的遗像仔细包好揣在怀里,抱着赵玉刚回北京。 出发前她就预想过家人的反对,却没料到母亲的反应会如此激烈。 邵红梅终于抬起头,眼眶泛红却眼神坚定,声音带着压抑许久的哽咽,缓缓讲述着陕北的七年,每一个字都带着黄土的厚重与生死的重量。 王氏举着扫帚的手慢慢垂了下来,指节因用力而泛白,脸上的愤怒渐渐被震惊取代,最后化为深深的动容。 她走上前,粗糙的手指轻轻抚摸着赵玉刚冻得发红的脸蛋,眼泪 “吧嗒吧嗒” 掉下来,滴在孩子的棉袄上,王氏的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 邵红梅的哥哥嫂子也闻讯赶来,哥哥刚进院门就皱起了眉,听完前因后果,眉头渐渐舒展。嫂子快步上前,把赵玉刚抱进屋里,从柜子深处翻出几块水果糖,塞进孩子手里。 王氏拍了拍她的肩膀,转身进了屋,不一会儿端出一碗热姜汤,递到她手里:“妈懂你,妈帮你一起带。咱们一家人,总能把日子过好。” 往后的日子里,邵红梅在街道工厂找了份缝补衣物的活儿,指尖被针扎得布满小伤口,却总在下班后匆匆赶回家。晚上就着煤油灯给赵玉刚辅导功课,王氏则在家帮忙洗衣做饭。 两年后,经人介绍,邵红梅认识了在中学当老师的李建国。听她那段过去,李建国眼中满是敬佩,看向她的目光多了几分郑重。 婚后,李建国果然如他承诺的那般,待赵玉刚视如己出。赵玉刚渐渐放下拘谨,某天放学回家,脆生生喊了声 “爸爸”,那声呼唤让邵红梅多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眼眶瞬间湿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