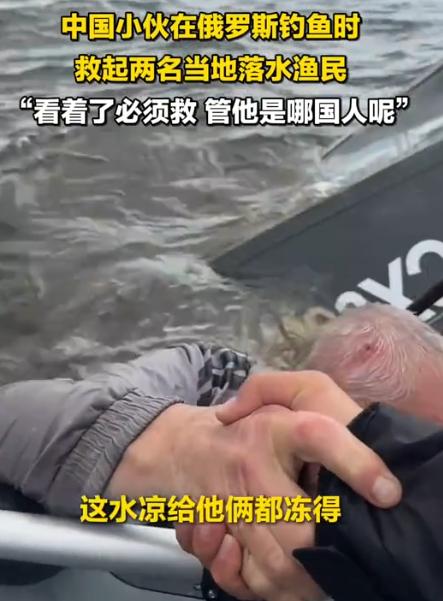2007年,大学生崔松旺伪装成流浪汉,浑身散发恶臭,牙齿布满污垢,每天在垃圾桶旁捡食残羹剩饭,甚至当众狼吞虎咽,该事引发持续关注。 他那天穿的衣服是提前挑出来的旧衣服,衬衫有点破,外套扣子也少了两颗,裤脚脏得像拖地布,一身看起来就跟睡马路的一样。 崔松旺回忆说,准备的时候他专门在地上蹭了好几下脸,还用手抹了鞋底的泥巴往头发上拍,他说不搞得像一点,怕没人信。 他连续几天没刷牙,牙缝里的那股酸味他自己都受不了,说话时嘴巴都不敢张太大,怕别人离太远。 白天他就在城边乱转,挑那种没什么人理的小巷子晃,路边的塑料瓶他也装模作样捡一下,有人看见也只是一眼就走。 他说最开始几天没什么动静,就是身上那股味道太呛了,晚上睡桥底下,连别的流浪汉都挪地方。 有一次他实在饿得慌,就蹲在一家小饭店后面,趁没人注意,从泔水桶里拎出个塑料袋,把里面的米饭扒拉几口吃了,嘴里满是酱油味还有油腻腻的汤汁。 他说那顿饭吃完,头晕得厉害,胃像被烧了一样疼,但他不敢去医院,也不敢洗澡,怕被看穿。 他说有人路过会递给他一瓶水或一个馒头,但基本没人说话,有人皱眉头,有人侧着身子走,就当他是空气。 大概到了第十天的时候,他整个人瘦了快十斤,脸上的胡子长出来了,头发也打结了,他照了照水沟的倒影,说自己都认不出自己。 第十二天傍晚他坐在一个小公园角落,注意到有俩人一直没走远,一个穿蓝夹克,一个戴鸭舌帽,一直在盯他看。 他说他当时心里有点发毛,猜可能是人贩子,但又不敢确定,就装得更呆一点,眼神发直,手一直在抠衣角。 那俩人过来时说话特别顺:“兄弟,这天怪冷的,要不跟我们走吧,那边有活干,还有饭吃,别这么熬着了。” 崔松旺说他当时点了点头,假装听不懂太多,但其实脑子飞快在转,想着到底要不要上那辆车。 最后他跟着走了,被带上了一辆贴了黑膜的面包车,窗户糊着布,车厢里闷得要命,还有股柴油味和汗臭味混一起。 他说那车开了几个小时,一路颠簸,手机早就被他们收走了,钱包也没了,窗外是山,一眼看不到灯。 车停下来的地方是个封闭砖窑,有围墙和铁门,空气里都是灰和煤味,远处烟囱在冒烟,四周静得发慌。 刚进去时有人拎着皮鞭吼:“这不是学校,是砖窑,不听话就往死里打”,有人真被抽得滚地,崔松旺看得发愣。 他说第一天就被分配去抬砖,砖都是热的,刚从炉子里拉出来,手上一会儿就起了泡,他喊疼没用,只能忍。 晚上睡的是潮湿的地铺,周围都是汗臭味和脚气味,有人咳得睡不着,有人一躺下就打呼,他说他几乎整夜睁眼。 吃的是发霉的馒头,水是混着泥的井水,连口碗都没有,有人喝了就拉肚子,也没人管。 他说有人干活太慢被骂成“畜生”,还有人摔倒后被砖砸了,躺地上没人扶,后来再也没见过。 他说逃跑是想都别想,山上没信号,铁门锁着,有人试过,结果第二天被揍得脸肿得像猪头。 他偷偷观察,发现有个角落白天没人管,晚上也不亮灯,他晚上假装小便,其实在那藏了个小相机。 他说自己以前学过点摄影,就用这玩意拍了几段画面,有窑炉,有挨打的背影,也有脚上磨破的伤口。 这事持续了大概三个月,他手臂有一次被砖压了,血哗哗流,他找人借了条毛巾包着,夜里疼得直哼哼。 终于有一次晚上有人喝醉了,把铁门钥匙丢在地上,他就趁乱偷出来,连夜往山下跑。 跑到公路边时,他整个人像疯了一样,喊住一辆卡车司机,说自己被困了几个月,要报警。 司机把他带到派出所,他当时浑身是土,脸黑得像抹了煤,民警都吓了一跳,叫了救护车。 他把录像交了出来,还说了地址和路线,警方后来一连抓了七个人,封了那家黑砖窑。 据《南方都市报》2008年3月的报道,警方确认该砖窑存在非法拘禁和雇佣行为,案件后续有刑事处理。 崔松旺后来说,那段经历不愿意回忆太多,只说“里面的事,比他想象的还要脏还要狠”。 他说那不是勇敢,是一时冲动,结果就是把自己差点丢在里头,“以后谁还敢搞这种调查”。 目前他人已脱离危险,但对当时的身体伤害仍在恢复中,精神状态也还没完全稳定。 他说那几个月每天都怕死在那儿,现在睡觉还是会梦见窑里的火光和鞭子。 信息来源:当事人提供信息,部分内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