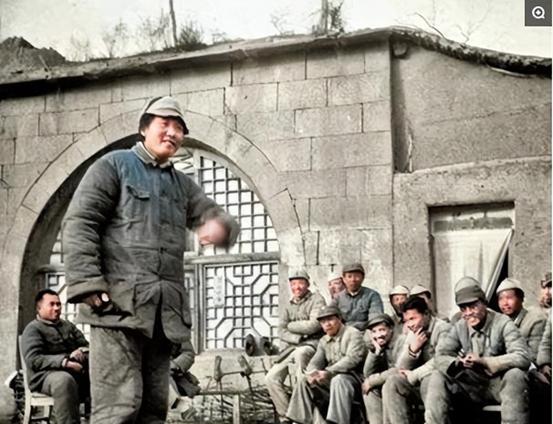延安国民党特务猖獗,毛泽东亲自出手,逼走了国民党派的延安县长 “1940年初春的凌晨两点,你们听见没有?城南又开始散布小报了。”周兴披着大衣,小声对守在窑洞口的两名警卫说。 延安夜寒,窑洞外的风掠过黄土高坡,带来一股刺骨的凉意,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陕甘宁边区成了全国注目的焦点——前有八路军总部,后有中共中央;兵家必争,谍报组织自然也把赌注压在这块黄土地上。国民党军统、中统、陕西保安处、伪政府派来的探子像钻沙子的蚂蚁,四处乱窜。 最先显露端倪的,是那些莫名其妙流行起来的秦腔唱本。唱词换了味儿,汪精卫成了“忍辱负重的大英雄”,朱毛红军则被渲染成“祸害乡梓的乱党”,还配上一句“蒋委员长才是真正的救星”。戏台下面,老乡听得津津有味;戏台上头,却有一双双贼亮的眼睛暗自得意。谣言、流言、怪言,一时间比高原的尘土还多。 边区保卫处于是加紧了巡查。刚上任不久的处长周兴发现,除了唱本,还有一批来历不明的报纸悄悄进城——版式是重庆的,纸张却是延安根本买不到的好货。更不对劲的是,报纸总能提前一周报道中央首长的动向。这个破绽太大,他立刻把几条线索交叉比对,找到了几个可疑节点:延安南门的车店老板冯长斗、县保安队里叫韩老二的差拨和一名在国统区待过的“乡贤”蒋福海。 就在情报逐渐拼图成形的档口,1937年4月25日那次伏击发生了。周恩来一行乘坐的卡车行经劳山,土匪与军统联手,三面压火力。轮胎先爆、再点火,弹雨如瓢泼,场面之凶险,亲历者日后都称那是“枪林弹雨里的鬼门关”。若非警卫员陈国桥拼命掩护,仅靠驳壳枪根本挡不住山头的机枪点射。余下还能脱困的,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边区震动,中央震动,周兴的保卫处更是如坐针毡。 不到一个月,周兴调动特务队、骑兵排、边区独立团,一口气拔掉劳山周边四十余股土匪。冯长斗、韩老二、蒋福海悉数就地正法,劳山奇袭案告一段落。但他心里清楚,真正的“大鱼”还在暗流里游。 “大鱼”之一叫沈之岳。1938年4月,重庆大学访问团抵延安。名义上是教授助教,实则军统核心干将。此人行事谨慎,夜里跑到杨家岭外踩点却连脚印都刻意刮平。可他低估了延安的警戒等级。副处长王范与他闲话半日,听出河南籍却满口江浙腔,一查户籍漏洞百出。尽管沈之岳最终脱逃并在台湾官至中将,但他的暗杀计划完全流产,也让戴笠损失了一张王牌。 周兴没有停手。利用投诚官绅王忠岐的“回马枪”,他指挥特派员赵去非导演了一场精妙的反间计——一句“我们内部可能埋了共党细作”足够,在洛川的中统主任单不移干脆把自己人活埋了。中统网络顿时土崩瓦解,延安外围再少十来个暗点,边区空气立刻清爽许多。有意思的是,这一出“借刀杀人”后来还在解放军的情报教材里成了经典案例。 谣言虽暂歇,可根子未除。症结就在延安市区那座堂而皇之的“国民党延安县政府”。按照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约定,边区内部本不该有平行的“官府”。可国民党硬是派了县长罗某驻延安,表面是“共同抗日”,背地里却给军统、中统做眼线,搜情报、撒传单,举手投足都在唱“统一战线”的反调。多次交涉无果,周兴只能再度登门向毛泽东请示。 1940年4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突然出现在国民党县政府的大门口。罗县长睡眼惺忪地迎了出来。“罗先生,”毛泽东语速不快,“兄弟阋于墙,再不收手,可就给日本人腾地盘了。”一句“兄弟阋于墙”打得对方面红耳赤。接着又补了一句:“朋友做不成,也别做仇人。搬一搬地方,大家脸上都好看。”罗县长连连鞠躬,声音发抖,却只得答应。 延安城里的老百姓很快发现,那伙人匆匆打包,三天之内移回重庆。唱本没了,流言散了,黑市安静下来。边区警备司令部后来统计——国民党县政府撤离后,谣言、特务案、恶性抢劫案环比下降八成以上,这个数字比任何宣传口号都管用。不得不说,毛泽东亲自出面谈话的震慑力,远胜于一次大兵围剿。 回溯这段攻防,边区情报系统靠的是几条准则:谣言必溯源、敌情必前置、出手必快准。国民党特务机关玩阴的,边区保卫处就来明的加暗的;对手想“掺沙子”,中央便“筛沙子”。事实证明,在民族存亡、正邪对决的当口,任何花招终究敌不过坚定的政治立场与冷硬的斗争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