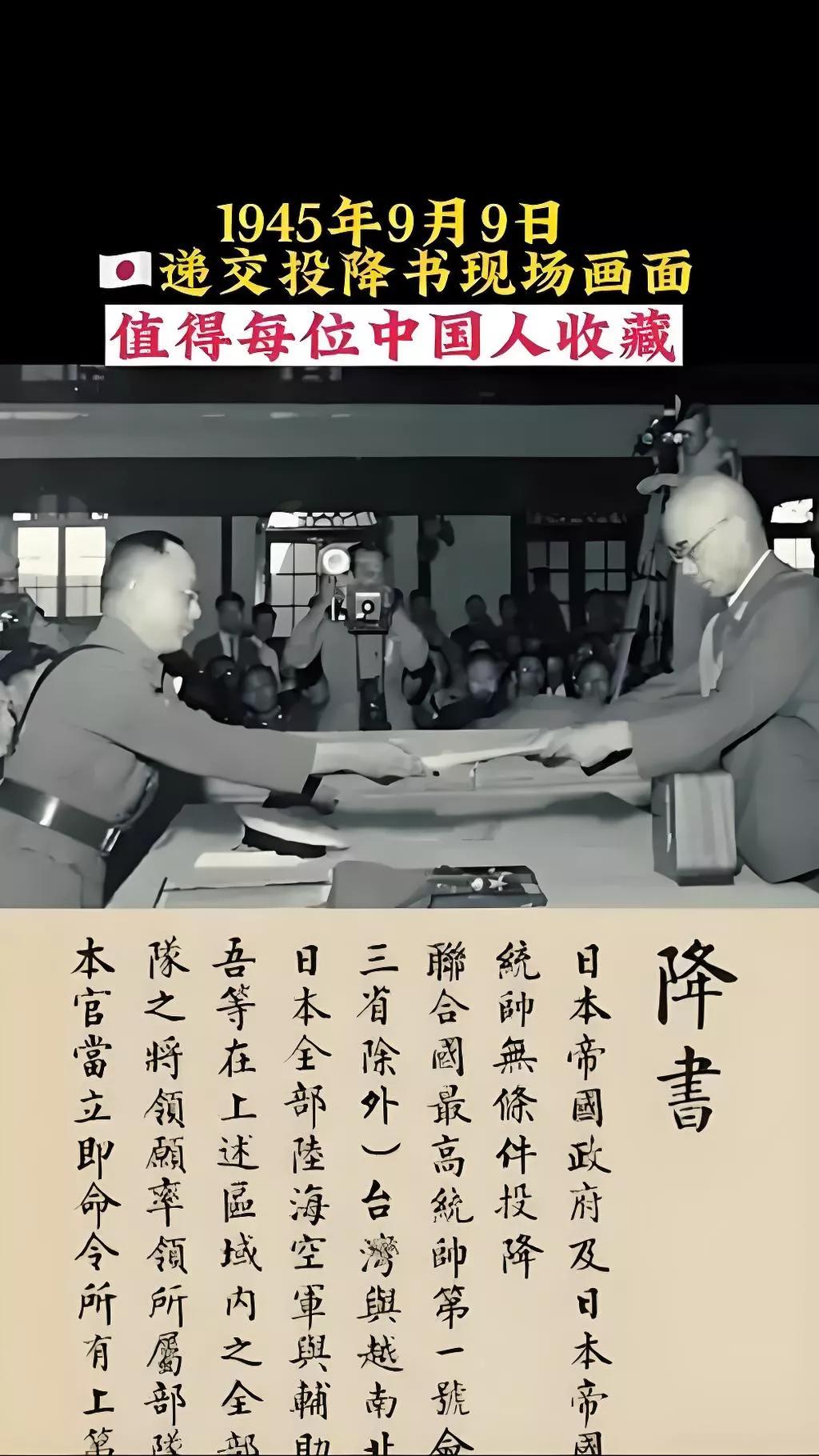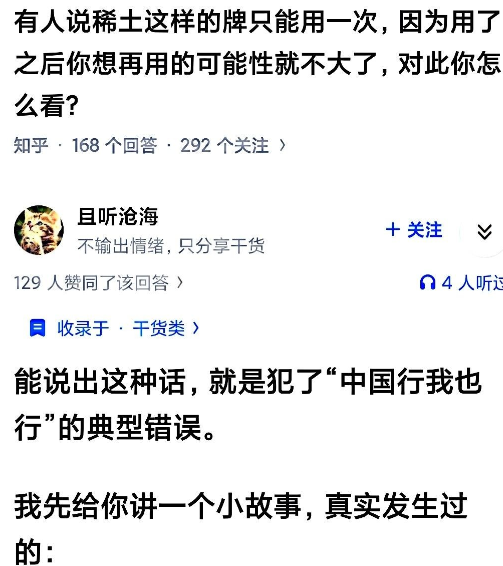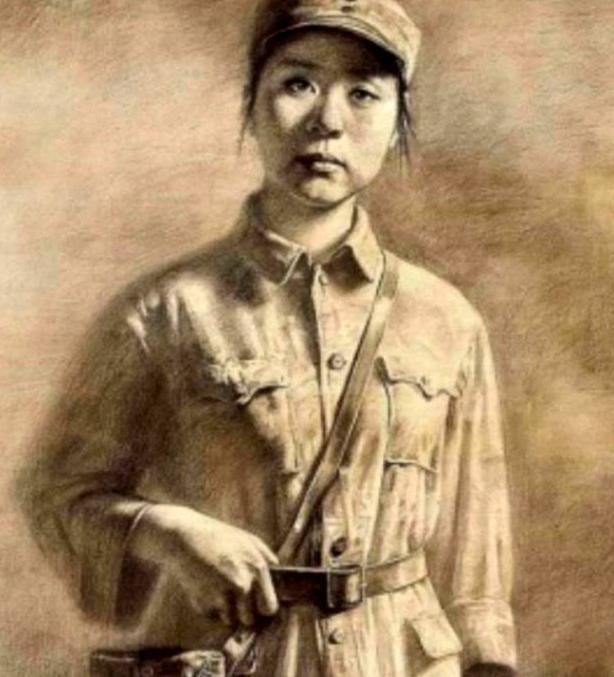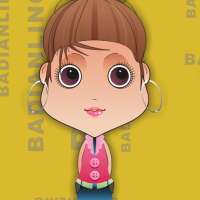在1962年叛逃的人的主要以维族和哈萨克族为主,大约有五六万人,现在他们过的一点都不好。 1962年那年春天,伊犁的雪比往年化得慢,河道边结着薄冰,牲口踩上去都不安分。 可比起这些,自打那年开春起,人心才真正开始变得不安分。 牧民一开始什么都不说,只是看着天,草原天大,风却紧。有人在集市边悄悄卖了家里最后两匹马,一匹黑的一匹花的,说是换盐,其实第二天人就没影了。 没几天,镇子上就有人开始传,说西边的路开了,霍尔果斯口岸那头,有人专门来接,有车、有吃的、有证,走过去就成了“苏联人”,还能发两块牛油。 起初,没人真信。 可谁都记得,前些年“困难”闹得有多凶。 仓库空了,孩子饿得啼哭,地里种出来的粮食不是没收就是被鼠灾毁掉。 连干部自己都悄悄种了地窖菜,还装出副革命面孔。 那年伊犁的棉布配额比哈密少,谁家有点好料子,全村都羡慕。 苏联电台开始密了,广播声穿过戈壁,维语、哈萨克语,一句句软绵绵地钻进耳朵:“你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那些字眼像老鼠啃粮袋子,一点点啃得心里发空。 后来真的有人走了。夜里走的,拖家带口。有个叫艾合买提的老汉,祖上是从塔什干逃来的,这次却又往回走。他说:“命数到这儿了,我想试试看。”他走得干脆,只留下炕上的水烟袋和孙子的破靴子。 再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不是偷偷摸摸了,是白天公开走。 一家人带着炉灶、被褥、羊圈门板,就这样排着队地去口岸。巴克图那边人说,苏联人准备好了,有帐篷,有麦饼,有医生。他们把这些人叫“兄弟民族”,招待得比自家人都细。 最扎眼的,是祖农·太也夫。堂堂一个维吾尔族的少将,新中国授衔时的英雄人物,说走就走了。他还带着家人和几个老部下。有人说他是受苏联蛊惑,有人说他是看穿了结局。那天他穿着军大衣站在边境口岸,风一吹,像是那身军装也觉得羞愧,不敢贴身。 他没说一句狠话,倒是眼神飘过来那一瞬,像是替人下了判断——你们还在犹豫什么? 伊宁的车站彻底乱套,是5月29号那天。几千人围着客运站,高喊着要去苏联,要坐国际班车。警察被打翻了帽子,玻璃碎了一地。有人抱着小孩哭,说走得太晚怕赶不上“队伍”。那天太阳特别刺眼,碎玻璃反光照在人脸上,跟火一样。 北京知道了这事。毛泽东批示:“让他们走,不必强留。”这话不像是愤怒,更像是冷静得可怕。他说:“天堂?你们去看看是不是真的。”那时候他就认定,这不是福,是祸。 可地方可不敢再让人这么走了。兵团的人开始往边境调,大卡车一辆接一辆,搭起帐篷,扎起铁丝网。干部一边安抚百姓,一边清点损失。很多村子成了空壳,牛圈的门咯吱咯吱响,没牛,也没人关。有人说自己家三口人就剩下他一人没走,一口锅、一张破炕席,他守着,像守一块没人要的地皮。 那年有统计:牲畜走了十几万头,耕地荒了几万亩。连县政府也差点搬空,有一次县里只剩三个干部,两个人还发高烧。 而走过去的人,真的像他们想的那样,被迎接成了贵宾吗? 刚开始是热闹的。哈萨克斯坦那边的收容所、农场、学校张罗得很快,发吃的,分衣服。可等新闻照片拍完,欢迎标语撤掉,他们才发现真正的生活才刚开始。身份,是个绕不过去的坎。 苏联对待这批人,并不真的当自己人。 他们不是移民,不是难民,更像是“合适的时候用来做宣传”的工具人。被安排去干最苦的农活,住在最旧的宿舍。孩子进不了主城区的学校,大人进不了干部队伍,连买东西都得排在苏联本地人后头。 有人悄悄写信回新疆,说后悔了。可边境线早已扎起新一轮的铁丝网,兵团哨卡每十公里一个,谁还敢再往回走? 1991年苏联解体后,问题彻底暴露出来。 国家不管了,农场也散了。 这批人,变成了没有户籍、没有福利、没有出路的人。有人饿死在阿拉木图街头,有人拿着苏联老护照去换面包,被拒。 还有人偷偷跑到边境,想试试看能不能混进来——可他们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祖农·太也夫,老了,死在中亚一个普通病房里,连棺材都是临时借的。 他没有等到荣归,也没有换来荣耀。 他曾是万人仰望的少将,最后像个失踪的人,名字慢慢从两国的官方记忆中被抹去。 那些留下来没走的人,生活也不容易。 但随着时间慢慢拨过,改革开放了,兵团稳了,边境线也安静了。 他们没穿上苏联的呢子大衣,但穿上了中国自家的蓝工作服。 孩子们进了学校,地又翻种起来。 牛羊照样跑,夜里还是有人吹笛子,只是那曲子里,再也没有临走时的慌乱。 1962年,是个坎。 人走了,地空了,铁丝网再也没松过。 风还在吹,草原夜里还是冷,可再没人轻易提起“过境”这个词了。 有人说,命运是自己选的,可有时候它像风,吹你一把,你就以为是自己决定的。 巴克图口岸的栅栏如今锈得厉害了,有些地方已经脱了漆。风吹过时,会发出咯咯的响声,像有人在轻轻敲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