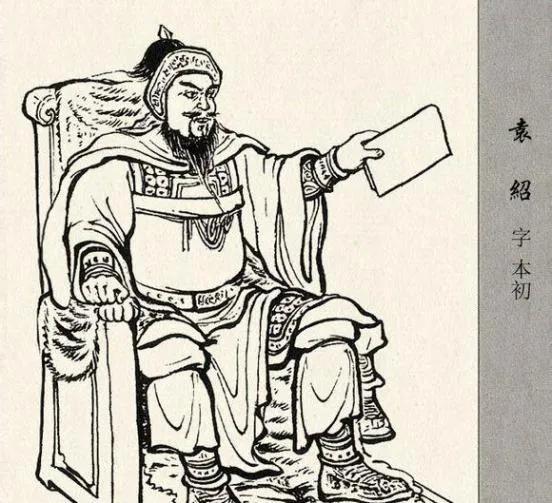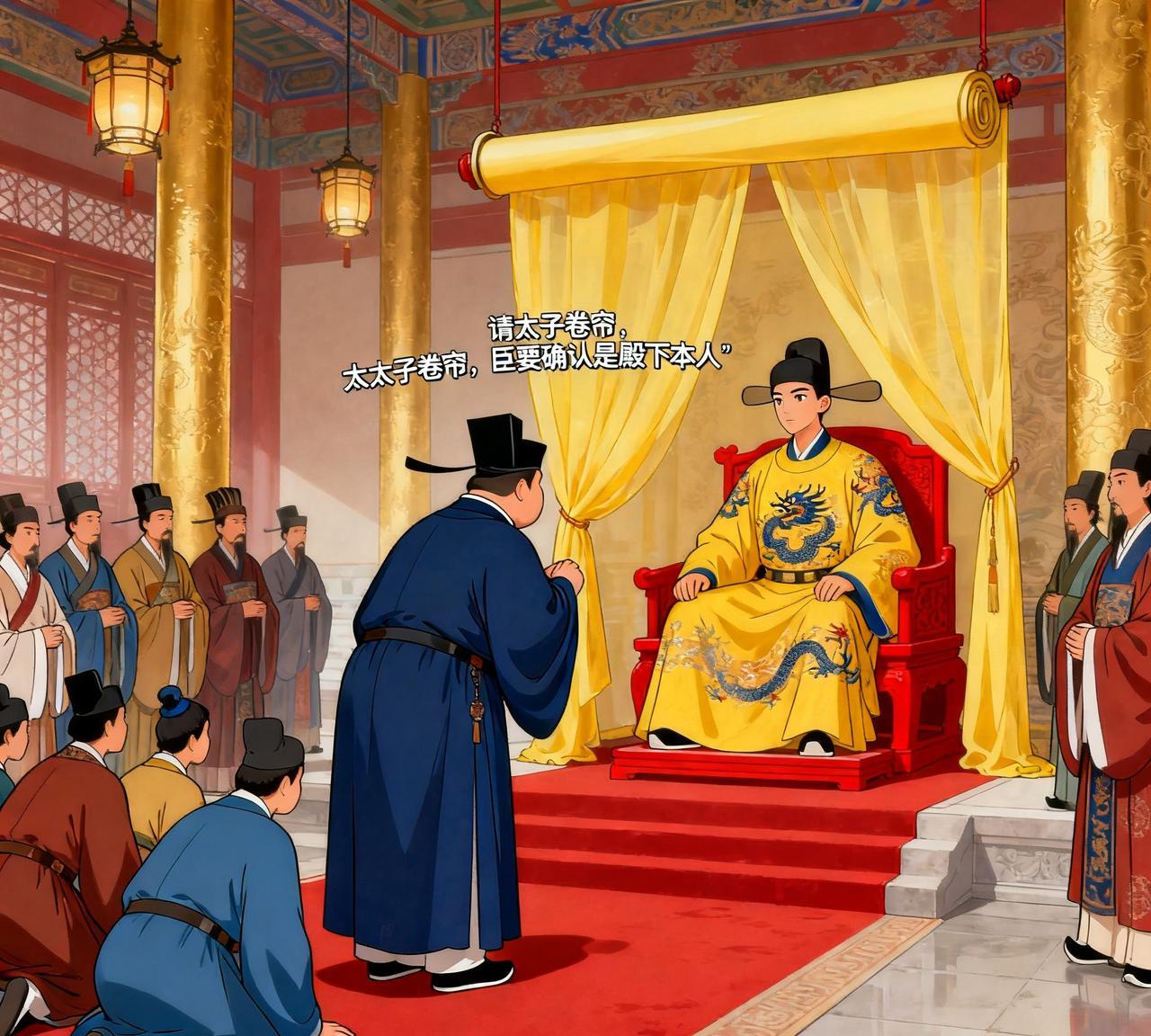北魏权臣高澄郊游,遇到了一个漂亮尼姑,就强行连夜逼她一起谈佛法,然后带回宫中,生了个孩子,就是世间第一美男子高长恭。 禅房的门被踹开时,油灯的火苗惊得缩成一团。尼姑攥着念珠的手在袖中掐出红痕,高澄的紫袍扫过供桌,打翻的香炉里,檀香灰混着他腰间玉佩的寒光,落在她光裸的脚背上。 “佛法说普度众生,” 他捏住她的下巴,看月光顺着她剃度的头皮流进衣领,“你且度度本王这凡心。” 随行的侍卫在门外偷笑,他们太清楚这位渤海王的手段 , 昨日还在朝堂上斩了三位贪腐的尚书,今日就能为一个尼姑驻马深山。 高长恭第一次戴上面具时,铜镜里的青铜饕餮正对着他笑。十四岁的少年指尖划过面具上的獠牙,把过于秀美的眉眼藏进阴影里。 母亲的画像早被父亲烧了,只留下句 “不得母氏姓” 的记载,像道没愈合的疤。 他在演武场挥槊时,总有老兵窃窃私语 “瞧这模样,真像那年被王爷带回宫的尼姑”,风把话送进他耳里,槊尖就劈得更狠,把地上的青砖砸出蛛网般的裂纹。 高澄的案头总摆着两物:镶金匕首和未写完的《麟趾格》。他用匕首挑开贪吏的奏章,笔尖在律法条文上划得飞快。 “选官只看才干,不论出身” 的政令贴满邺城时,吏部尚书的头刚被挂在城门上。 有老臣劝他 “留点余地”,他把匕首拍在桌上,寒光映着眼睛:“东魏的官,早该换批活的了。” 那时宫人们都传,渤海王夜里常去偏殿,那里住着个无名无分的女子,生的孩子眉眼比画上的仙童还俊。 邙山的雪落在高长恭的面具上,融成血水往下淌。五百骑兵跟着他冲破北周军阵,槊尖挑着敌将的头盔,面具后的喘息混着厮杀声。 金墉城上的守军起初以为是鬼魅来袭,直到他摘下面具擦汗,阳光撞在他脸上,城楼上竟一时没人敢出声。 那晚的军帐里,士兵们唱起新编的歌谣,“兰陵王入阵,鬼神皆避”,他摸着脸上的冻疮,想起父亲当年在朝堂上的模样, 原来血脉里的狠劲,戴不戴面具都藏不住。 膳房的刀声比往常脆。兰京端着托盘走进高澄的营帐时,匕首藏在袖子里,寒光和当年高澄逼尼姑时的玉佩一样冷。 “陛下(指东魏孝静帝)赐的膳”,他低头的瞬间,刀已出鞘。二十九岁的权臣捂着喉咙,血溅在 “受禅诏” 的草稿上,把 “皇帝” 二字泡得发胀。 帐外的侍卫冲进来时,只看见兰京疯了似的挥刀,嘴里喊着 “我不是奴才”,没人注意到墙角暗格里,藏着半封写给那个无名女子的信。 高纬的毒酒盏在宫灯下发绿。高长恭接过时,指尖的老茧蹭过冰凉的瓷面 ,那是常年握槊磨出的。 “陛下念王叔功高”,使者的声音像蛇吐信,他想起邙山之战后,后主曾笑着问 “若战败怎么办”,自己答 “家事亲切,不觉遂然”,那时的酒气还没散尽,如今就成了催命符。 毒发时他蜷在地上,眼前闪过母亲模糊的影子,又变成父亲遇刺时的血,最后定格在自己戴了多年的面具上,饕餮的嘴好像在笑。 邺城的戏台还在唱《兰陵王入阵曲》,伶人们戴着仿制的面具,唱腔里的悲壮比邙山的雪还冷。有老人说,那面具下的脸,一半像当年的渤海王,一半像那个没留下姓名的尼姑。 而高澄的《麟趾格》还在北齐的律法里,高长恭的槊被供奉在太庙,只是没人再提,这对父子,一个死在登基前夜,一个死在功高震主时,都没躲过权力这把刀。 信源:《北齐书·卷八·列传第一·高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