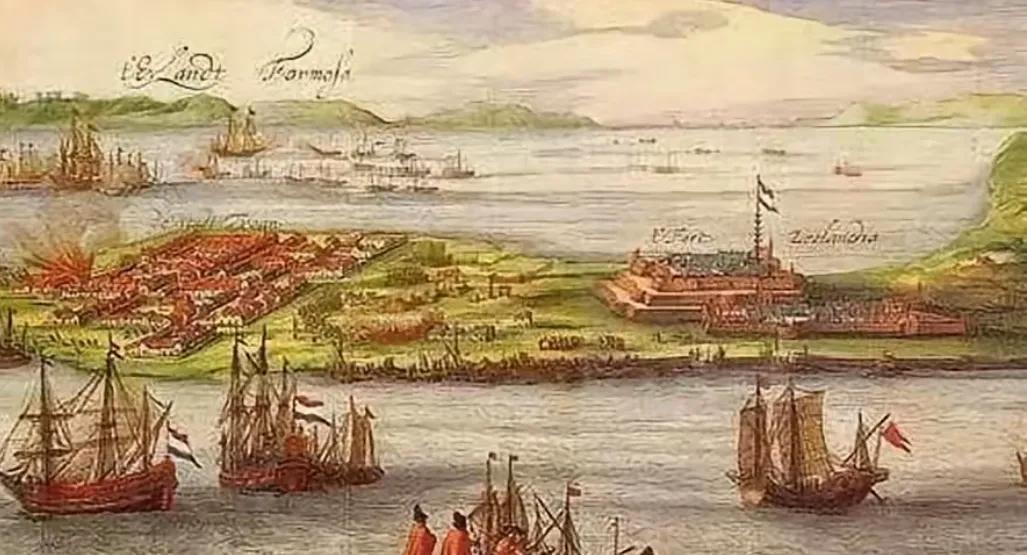古时,有个富商员外带着管家小厮在外游玩,突然看到街边有个年轻姑娘在卖身葬父,就上前询问道:“你需要多少银子?”姑娘低声回答:“只要10两银子就可以了。”富商打量着姑娘,最后说了一句:“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 姑娘的肩膀抖了一下,像被秋风扫过的落叶。她垂着的头慢慢抬起,露出一张沾着泥痕的脸,唯有双眼亮得惊人,像浸在井水里的黑曜石。管家在一旁咂嘴,心想这姑娘瘦得像根豆芽菜,偏偏眉眼生得这般勾人,难怪员外会多问一句。 “10两太少了。”富商突然笑起来,手指摩挲着腰间的玉佩,“我给你50两,不光能让你爹入土为安,还能给你置两身像样的衣裳。” 姑娘猛地抬头,眼里的光晃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她知道这世上没有白来的好处,就像去年冬天冻裂的手,想暖和就得往灶膛里添柴,哪有凭空冒出来的炭火。“老爷想要小女子做什么?”她的声音比刚才稳了些,带着点破釜沉舟的硬气。 “很简单。”富商蹲下身,视线与她平齐,“跟我回府,给我当个端茶倒水的丫鬟。你爹的后事,我让人替你办得风光。”他说这话时,阳光正好照在他油亮的绸缎马褂上,晃得姑娘有些睁不开眼。 三日后,姑娘穿着新做的青布衣裙,站在了富商的宅院门口。灵堂已经撤了,管家说老爷特意请了和尚做了七天法事,坟头还立了块像样的石碑。她攥着衣角走进二门,听见下人们窃窃私语,说她是走了狗屎运,从泥地里飞进了金窝窝。 可金窝窝里的日子,并不比街边好过。富商确实没亏待她,吃穿用度都按二等丫鬟的份例,可那双眼睛总像黏在她身上似的,尤其是在酒过三巡之后。有回他让她研墨,手指顺着笔杆滑下来,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背,她像被烫着似的缩回手,墨汁溅在宣纸上,晕开一大团黑。 “怕什么?”富商哈哈大笑,“当初在街边,你可不是这副样子。” 她突然想起那天在街边,自己为了筹钱,连路人投来的鄙夷目光都能忍,怎么到了这里,反倒敏感起来。夜里躺在通铺床上,她摸着枕头下藏着的半块碎银——那是她卖身时偷偷留下的,原想攒着赎身,现在却觉得这想法荒唐得可笑。 转机出现在一个雨夜。富商的独子从京城求学回来,浑身湿透地闯进了厨房,正好撞见她在灶台前烤火。那少年愣了一下,随即红着脸道歉,说自己太渴了想找口水喝。她递过去一碗热水,看见他袖口磨破了边,倒不像个娇生惯养的少爷。 往后的日子变得微妙起来。少爷总爱往书房跑,有时是找书,有时是问她些家常。她知道自己身份悬殊,从不敢多言,可少年眼里的清澈,让她想起小时候在乡下见过的溪流,干净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 富商很快察觉到了异常。那天他故意让她去少爷房里送点心,刚走到门口,就听见里面传来争执声。少爷说:“爹,您不能这样对她,她也是爹生娘养的。”富商的声音像闷雷:“我花了银子买回来的,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她端着托盘的手开始发抖,转身想走,却被富商叫住。“你倒是说说,是愿意留在我身边,还是想跟着这毛头小子?”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像在看一只待价而沽的牲口。 她沉默了半晌,突然把托盘往桌上一放,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老爷当初花50两银子,买的是我替您当差的力气,不是买我的良心。”说完这话,她从怀里掏出那半块碎银,轻轻放在桌上,“这是我自己的银子,今日起,我不欠您的了。” 管家后来常跟人说,那姑娘真是个犟种,放着福不享,非要连夜收拾包袱走人。有人说她去了京城,跟着少爷读书识字;也有人说她回了乡下,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就像没人记得那年街边的寒风里,她为了埋葬父亲,曾把尊严折成了几两银子的模样。可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有些东西看着金贵,攥在手里却硌得慌;有些东西看似廉价,放出去时却能让人挺直腰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