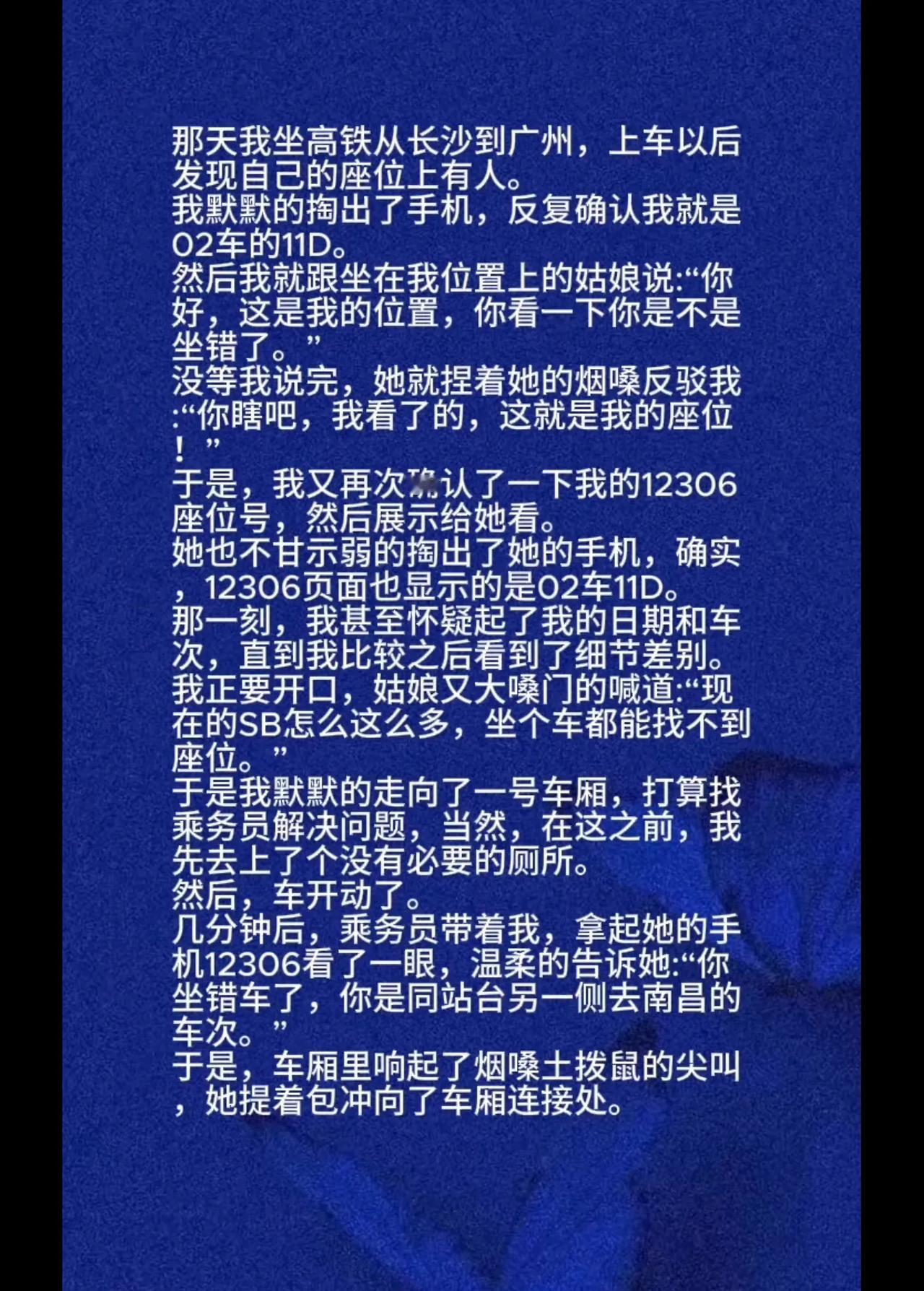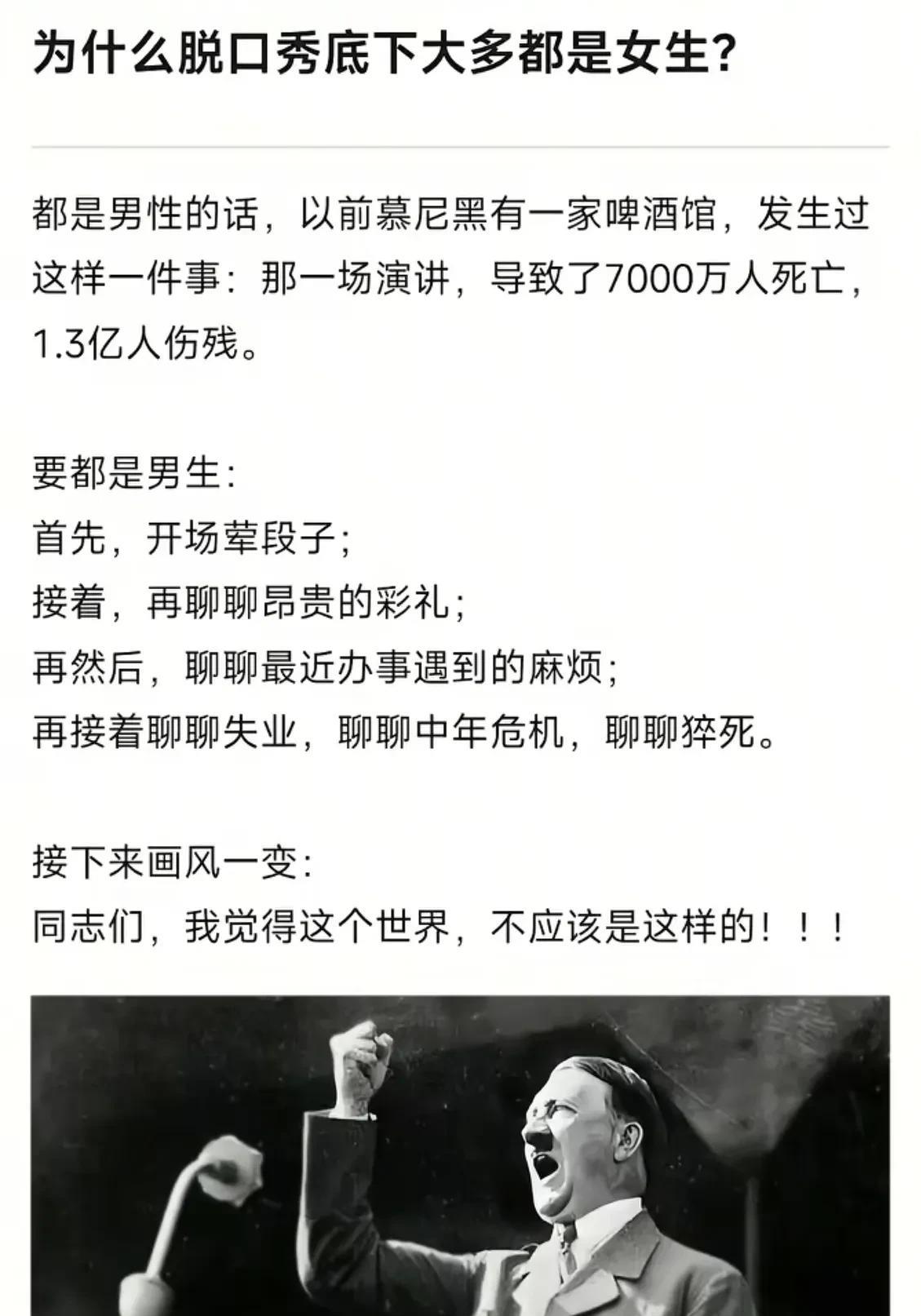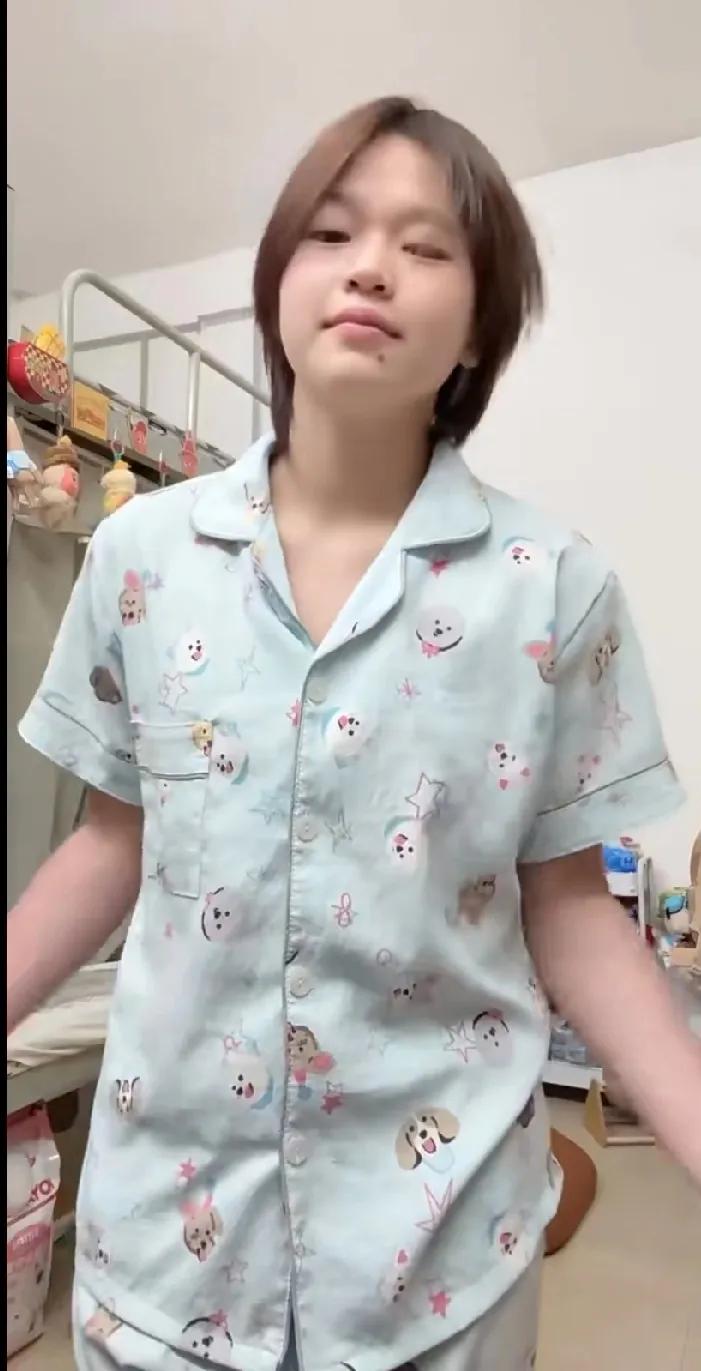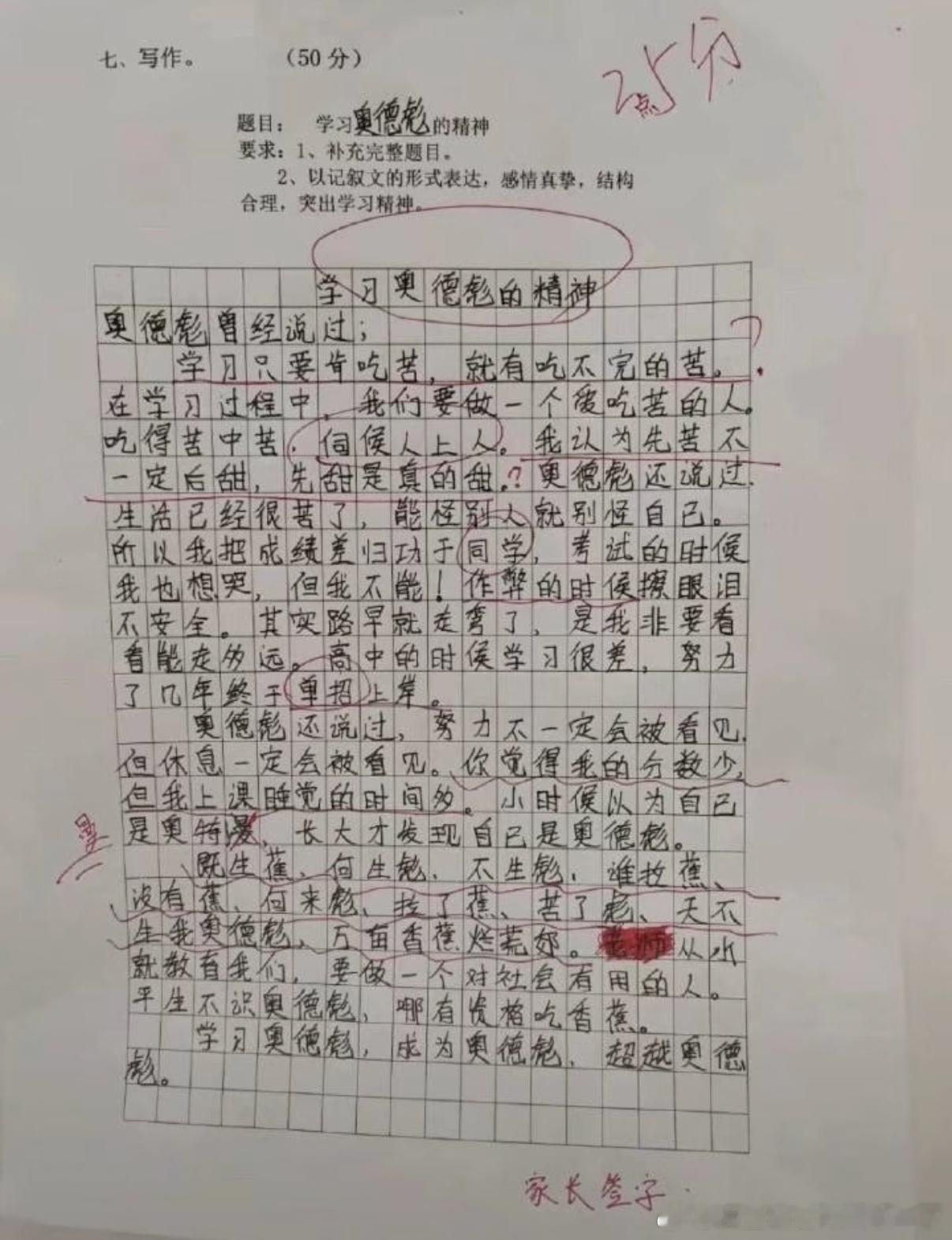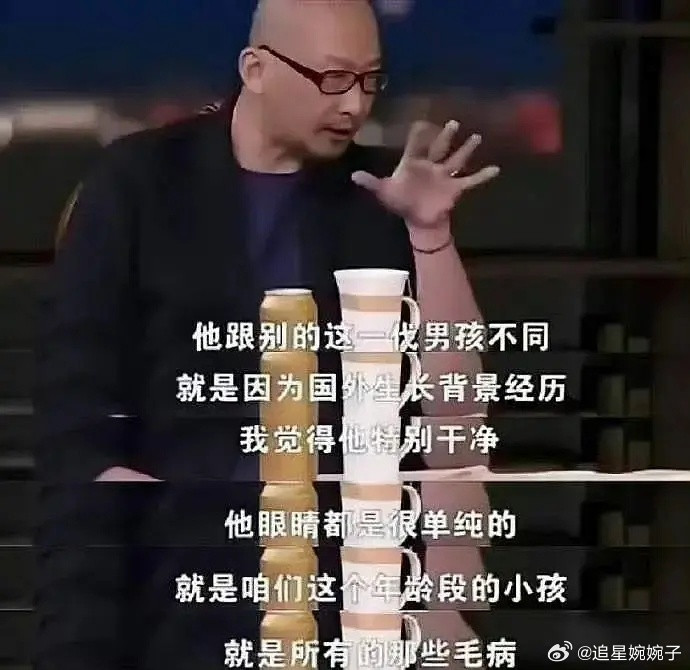溥仪参观井冈山时,一番感慨闹笑话:这么多房子,难怪毛主席要来 “1964年4月9日早上六点,你们快看,那一排排房子真壮观!”车刚在井冈山脚下停稳,溥仪拉着身旁的溥杰低声嘀咕。 一路颠簸的疲惫瞬间被山雾冲散。井冈山的云在脚边游走,树梢滴水,远处传来伐木声。队伍里大多数是北京文史馆的同仁,平均年龄五十上下,久坐案头,突然换成陡坡与碎石路,一个个气喘吁吁。可溥仪没事似的,一会儿蹲地看野花,一会儿端着相机找角度,活像重获自由的少年。 1959年的抚顺,他对“自由”这两个字还完全不敢奢望。那年毛泽东向人大常委会建议特赦部分战犯,外界惊讶,狱中更是炸开了锅。大家私下议论,论罪恶深浅,最不可能被列入首批的就是末代皇帝。然而名单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监舍一片静默,他本人更是眼圈通红,几乎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回忆那一刹,“像突然有人把冰冻的血脉一下子烤热,整个人都晕了”。 获释后他五十三岁,没有行当、没有积蓄,连户籍都得公安部特批。周恩来几次找他谈话,问干什么合适。他先说当工人,被问会不会看图纸;又说做医生,被问出错谁负责;最后周总理拍拍他的肩——“你就是一本流动的史书,干文史最合适。”这一句把方向定死,他从此跟另一群“活档案”坐到一张桌前,翻阅旧档案、校正旧照片,自己也写《我的前半生》。写书辛苦,可他告诉身边人:“比当傀儡皇帝强多了!” 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批示安排文史馆员赴南方考察建设成果。文件下到馆里,溥仪第一个报名。有人打趣:“江南水多船多,您不会又想坐龙舟吧?”他笑呵呵:“龙舟早沉了,只想看看新中国到底修成啥样了。”队伍挑了二十七人,春季启程——南京中山陵、杭州西湖、苏州园林,处处新貌。只是这些地方对他来说不过“历史课堂”,真正勾起他好奇心的,还是井冈山。 四月初,车子从南昌上高速,摇摇晃晃进吉安。司机叮嘱明天清晨五点半发车,要爬九九道弯。半夜山雨,窗外黑得伸手不见指。凌晨,车灯像两把小刀,割开浓雾。大家昏睡又醒来,几次差点撞石坎,肾上腺素飙升。溥仪倒兴奋得像探险家,时不时用胳膊肘戳同伴:“再高点,再高点,传说当年红军就是挑着米爬这路!” 抵达茨坪镇时才七点多,天光刚亮。镇子不大却干净,水泥路、三层招待所、砖瓦平房排得整整齐齐。溥仪望着这些新楼房冒出一句:“哎呀,莫怪毛主席当年要来这里,有现成房子住,真方便!”话音刚落,团里立刻爆笑。陪同的当地干部赶紧解释:现在看到的建筑几乎都是解放后修的,当年只有茅草屋十几间。溥仪面红耳赤,自嘲一句“见识短”,算是把尴尬压了下去。 上午九点,革命博物馆首先参观。大厅里陈列的扁担、马灯、大刀让许多人站住脚。讲解员提到“朱德扁担”时,溥仪抢话:“真的是朱老总亲自写字那根?”得到肯定,他又凑近玻璃柜研究字体,半分钟没挪步。同行的杜聿明轻声说:“看他,和研究古碑一样。”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些日常器物对末代皇帝的冲击比对普通人更大——曾经的权力体系不过一根扁担、一口马灯就维系了。 黄洋界的车程更险。几十个S弯,车窗外就是深不见底的谷。有人晕车,干呕不停。溥仪却趁停靠点让司机开车门,自己跑上旁边山包眺望。一进阵地遗址,他摘帽行礼。石碑上“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几个楷字墨迹犹新,他抬头细看:“毛主席笔力真沉稳。”随后他提笔写下《黄洋界旧战场》——七律一首,字字工整。史馆同仁捧读,连忙拍照留底。 接下来的访谈比单纯参观更精彩。当地宣传部找来几位八旬老赤卫队员,坐在敬老院竹椅上聊当年。老人们讲挑粮小道、夜袭茶陵、割电线杆,一口客家话,年轻翻译边听边擦汗。溥仪竖着耳朵,听不懂就追问,生怕漏一句。老人说当年供给紧张,连朱老总都把手枪当号角敲,“叮叮当当”一响,全营集合。溥仪摇头感慨:“末代皇帝吃满汉;总司令啃红米,真叫天壤之别。” 午饭是在茨坪食堂。每人一碗红米饭、一勺南瓜汤,外加两块腊肉,和当年红军口粮几乎一致,就是量足些。按现代口味而言,米糙、汤淡,可不少人吃得津津有味。溥仪更是端着汤碗喝得咕咚响。他悄悄告诉我:“想象当年,如果没有这些南瓜,恐怕饿死人也说不定。”那一刻,他显得像真正的平民。 傍晚回宾馆,雨停云破。一群人把《空山计》剧本摊桌上,对照沙盘高谈阔论。溥仪端着京胡,小心试拉两下,发出“咿咿呀呀”的长音,声音不准却胜在投入。他说小时候宫里唱昆曲京剧都得跪听,如今能自己操琴,痛快。沈醉插嘴:“要不是朱毛的‘空山计’,咱们哪有机会唱!”众人哄笑,氛围一片轻松。 游程最后一天,队伍拜谒红军墓。荒草掩着石冢,风从山谷灌进松林,呼啸作响。溥仪脱帽弯腰足足十秒,没有抬头。他曾多次在回忆录里写“悔恨、亏欠”这样的词,真正站在无名烈士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只默默把胸前的小红花别在纪念碑脚下。现场无人提醒,但所有人自觉肃立。那种沉默,比任何口号都震撼。





![酷似溥仪男子收到横店邀约哈哈哈,突然想起了这个段子[笑着哭][笑着哭][笑c](http://image.uczzd.cn/412101062398020049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