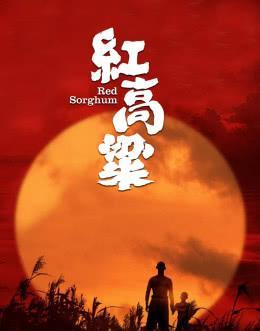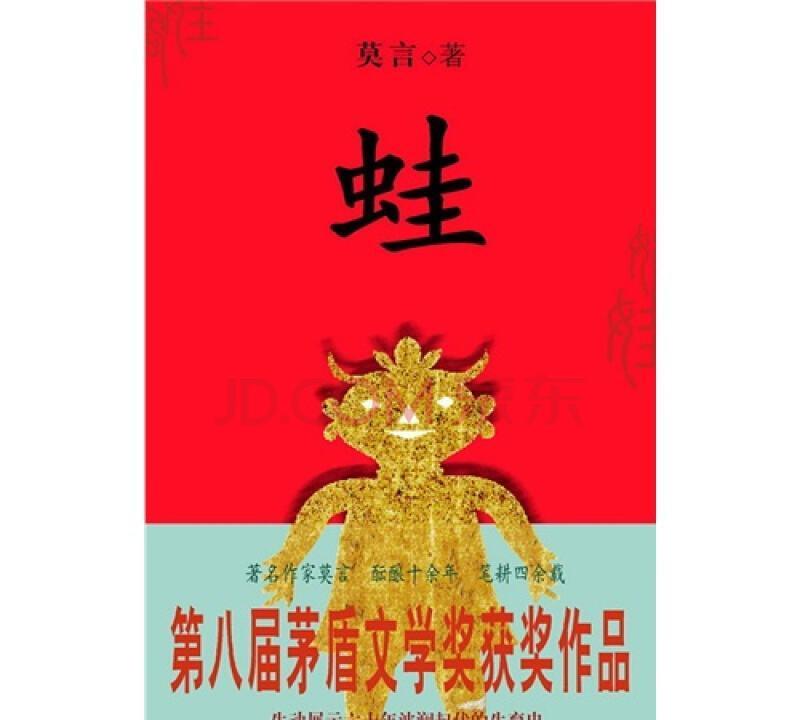有些反对莫言的人认为:“莫言获诺奖是因故意讨好、献媚、贿赂西方世界的结果,他的《生死疲劳》、《蛙》、《檀香刑》等长篇中暴露的是丑的一面,而这正符合西方对中国的固有印象,所以这些作品是专门为诺贝尔文学奖炮制的。”对此,复旦大学栾梅健认为,莫言挖掘了社会中各种已经存在的各种问题,而西方又对中国的这种举措存在很多歧视和误解。莫言从一个辩证的角度进行了阐述,这样的文学主题是比较受欢迎且客观的,不存在献媚、讨好的问题。 对莫言的小说语言的争议一直以来都比较大,褒贬不一。赞赏的人称之为语言的“天才”,认为莫言语言上的才华让人惊讶,对他的小说语言顶礼膜拜,奉为经典。他们觉得莫言的语言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够打开读者内心深处那些被尘封的情感和想象空间。比如在一些描写自然景色的段落中,莫言用他那独特的语言,将高粱地的壮观、河流的灵动、山峦的雄伟描绘得栩栩如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而批评的人则认为,莫言的语言过于“粗俗”“毫无节制”,他在语言上过分地任意而为,放任自流,使得他的小说充斥着欲望、暴力、血腥描写,消解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他们觉得这些描写过于直白和露骨,违背了文学应有的审美和道德规范。 以上两种观点其实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莫言在语言上那种诙谐生动、独立个性、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特点十分明显,在他的小说创作历程中都有所表现。从早期的作品到后来的成熟之作,莫言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和创新自己的语言风格。他创作上的青涩到成熟,语言上也有数次转向。早期他的语言可能更多地受到民间文化的影响,充满了质朴和野性;随着创作的深入,他开始学习西方先锋话语,将一些先锋的叙事技巧和表达方式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让作品更加具有现代感和实验性;同时,他又熟稔中国传统语言的优胜,多处有意使用,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文学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貌。这种创新与回归的交织,使得莫言的小说语言始终保持着活力和魅力。 莫言的小说语言个性十足,这无疑是他对先锋创作理念高度认同的一种鲜明体现。在当代作家群体中,莫言的语言风格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特而耀眼的光芒。他的语言不拘泥于传统语言规范的条条框框,有着一种冲破束缚、自由驰骋的豪迈气概。那是一种狂乱驳杂却又大气磅礴的语言风貌,时而婉约清丽,如潺潺溪流,流淌着细腻的情感;时而又深情款款,仿佛在诉说着岁月深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以《红高粱》为例,这部作品的语言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那高粱地里的激情与豪迈,通过莫言独特的语言表述,仿佛带着读者穿越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热血与激情的年代。书中的语言既有对乡村生活细致入微的描写,如对高粱生长状态、乡村景色的刻画,让读者仿佛能看到那片火红的高粱地;又有对人物性格大胆直白的展现,那些充满野性的对话和独白,将人物内心的情感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乡村世界。 《酒国》同样如此,莫言在作品中构建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酒国世界。他运用丰富多样的语言手法,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书中的语言时而幽默风趣,以诙谐的笔调描绘出酒国里那些荒诞不经的现象;时而又严肃深刻,对人性、权力、欲望等主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多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感受到惊喜和震撼,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谜题的迷宫之中,随着情节的推进,不断探寻着其中的奥秘。 莫言的小说语言完全偏离了常规,在词语、语序的使用和句子结构上,表现得狂放而又毫无节制。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说:“所谓作家的语言风格,实际就是对正常语言的偏离。”莫言正是如此,他大胆而又激烈的语言独具特色。他敢于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也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色,任意而豪爽。他的故事粗犷坦荡,透着一种野性,爱恨情仇都能够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来,狂放不羁。 莫言说:“作家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作,每一位作家都知道应该将自己独到的东西传递出来。……某种叙述腔调一经确定并有东西要讲时,小说的语言就会自己蹦跳出来,自言自语,自我狂欢。”这正是莫言独特的风格,失去了这种风格也就不是莫言了。正如在语言上鲁迅的锋利,他的文字就像一把锐利的匕首,直刺社会的黑暗角落;王朔的调侃,他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对社会现象进行嘲讽和解构;莫言的狂放语言同样给予读者独特的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