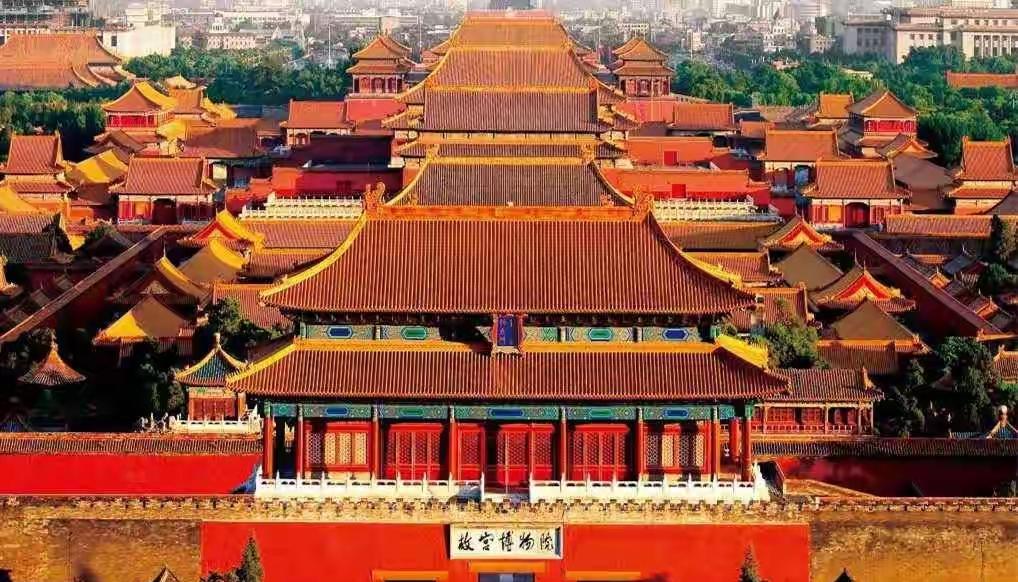835年的一天,五百多太监手持刀斧冲进中书省,见人就砍。宰相李训等大臣被乱刀分尸,头颅高悬宫门,上千具尸体横陈殿前。这场“甘露之变”,主谋竟是皇帝身边的大太监仇士良。 那日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仇士良站在紫宸殿的角楼上,看着底下蚂蚁似的禁军在宫道上排开。他手里把玩着一枚玉扳指,那是文宗皇帝去年赐的,冰凉的玉质抵着掌心,倒比刀斧更让人觉得刺骨。远处传来报时的晨钟,他突然笑了,声音像老鸹在枯枝上扑腾。 仇士良不是普通太监。 他伺候过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手里攥着神策军的兵权——那是唐朝最精锐的禁军,枪杆子硬得很。 中晚唐的太监早就不是端茶倒水的角色了。 他们能废立皇帝,能杀宰相,敬宗皇帝就是被太监害死的,文宗能坐上龙椅,也是太监们拍的板。仇士良这伙人,住着比王府还阔气的宅子,养子养孙遍布朝堂,比皇帝还像“真主子”。 唐文宗呢? 这皇帝登基时才二十岁,心里憋着股气。 他看着太监们在朝堂上指手画脚,看着自己想提拔个官员都得看仇士良的脸色,夜里常对着先帝的牌位哭。有次他跟大臣说:“我还不如汉献帝,他受制于权臣,我却受制于家奴。” 这话传到仇士良耳朵里,只换得一声冷笑:“皇上还是少读点书好,免得胡思乱想。” 宰相李训,是文宗手里的一把刀。 他出身名门,脑子活,敢干事。文宗拉着他的手说:“朕想让你帮朕把这受制于人的日子,了结了。” 李训咬着牙应了。 他们筹谋了大半年,想出个“甘露计”。 左金吾卫衙门后院的石榴树,据说夜里降了甘露——那在当时是“天降祥瑞”。李训跟文宗说:“陛下,这等吉兆得让仇公公他们去看看,沾沾喜气。” 文宗点头,心里跳得像打鼓。 他以为,左金吾卫里早埋伏好了甲士,仇士良一进去,就会被剁成肉泥。 可他忘了,仇士良在宫里混了四十年,鼻子比狗还灵。 那天仇士良带着一群太监去左金吾卫,刚进门,就看见一个小吏慌慌张张地跑,额头全是汗。他一把抓住问:“跑什么?”小吏吓得直哆嗦:“里面……里面有刀……” 仇士良心里咯噔一下,抬头看见帷幕后面有刀光闪。 “不好!有埋伏!” 他拽着还没反应过来的文宗,转身就往紫宸殿跑。太监们护着皇帝,像疯了一样冲,金吾卫的士兵追出来,砍伤了几个太监的胳膊。 到了紫宸殿,仇士良喘着粗气,盯着文宗,眼睛里全是血丝:“陛下,这就是您给的‘祥瑞’?” 文宗脸白得像纸,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仇士良没再看他,转身吼道:“传我的令!神策军,抄家伙!” 五百多太监,其实是神策军里的死士,平日里穿着太监服,藏着刀斧。这会儿得了令,像饿狼似的扑向中书省、门下省。 宰相李训正带着官员往宫里冲,想护驾,迎面撞上这群疯子。 “李训!你敢弑君!”仇士良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李训拔出剑,刚砍倒一个太监,就被七八把刀围住。他骂着“奸宦误国”,最终被乱刀砍翻,脑袋被割下来,挂在朱雀门上。 那天的长安,血水流进了排水沟。 户部尚书王涯、京兆尹罗立言……凡是跟李训沾点边的官员,不管是不是参与了密谋,全被搜出来砍了。家属也没能幸免,老人孩子哭着求饶,照样被拖到街上杀头。 宫门前的头颅越挂越多,乌鸦在天上盘旋,啄食着地上的血肉。 文宗被仇士良软禁在宫中,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仇士良每天派人盯着他,奏折得先过太监的手,想见哪个大臣,得看仇士良的脸色。有次文宗想召翰林学士,仇士良直接拦在宫门口:“陛下,朝堂的事,有我们呢,您歇着吧。” 文宗看着宫墙上的蛛网,慢慢变得沉默。 他不再读书,不再见大臣,常常一个人坐在殿里,对着空椅子发呆。840年,他在抑郁中去世,才三十三岁。临死前,他想立个年长的太子,仇士良不同意,硬是把年幼的武宗推上了位。 仇士良呢? 他又辅佐了武宗几年,权倾朝野。告老还乡时,跟其他太监说:“伺候皇帝,就得让他吃喝玩乐,别让他读书,别让他接近大臣,这样他就离不开咱们了。” 这话成了晚唐太监的“秘诀”。 甘露之变后,再也没人敢跟太监叫板。士大夫要么投靠太监,要么闭嘴装傻,朝堂上只剩下阿谀奉承的声音。 百姓们路过朱雀门,还能看到风干的头颅,想起那天的血雨,都低着头快步走。 有人说,这场事变,是文宗派李训先动的手,仇士良只是反击。可细想想,若不是太监把皇权啃得只剩骨头,文宗何苦要冒这险?若不是太监手里握着军权,哪能说杀就杀上千官员? 中晚唐的气数,其实在甘露之变那天就漏得差不多了。 皇帝成了傀儡,大臣成了刀下鬼,太监成了真主人。这样的朝廷,还能撑多久? 仇士良死后没几年,黄巢起义爆发,长安被攻破,宫阙烧成了灰烬。那些挂过头颅的朱雀门,最终塌在战火里。 (信息来源:《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旧唐书·文宗纪》《新唐书·仇士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