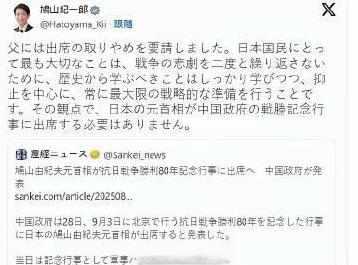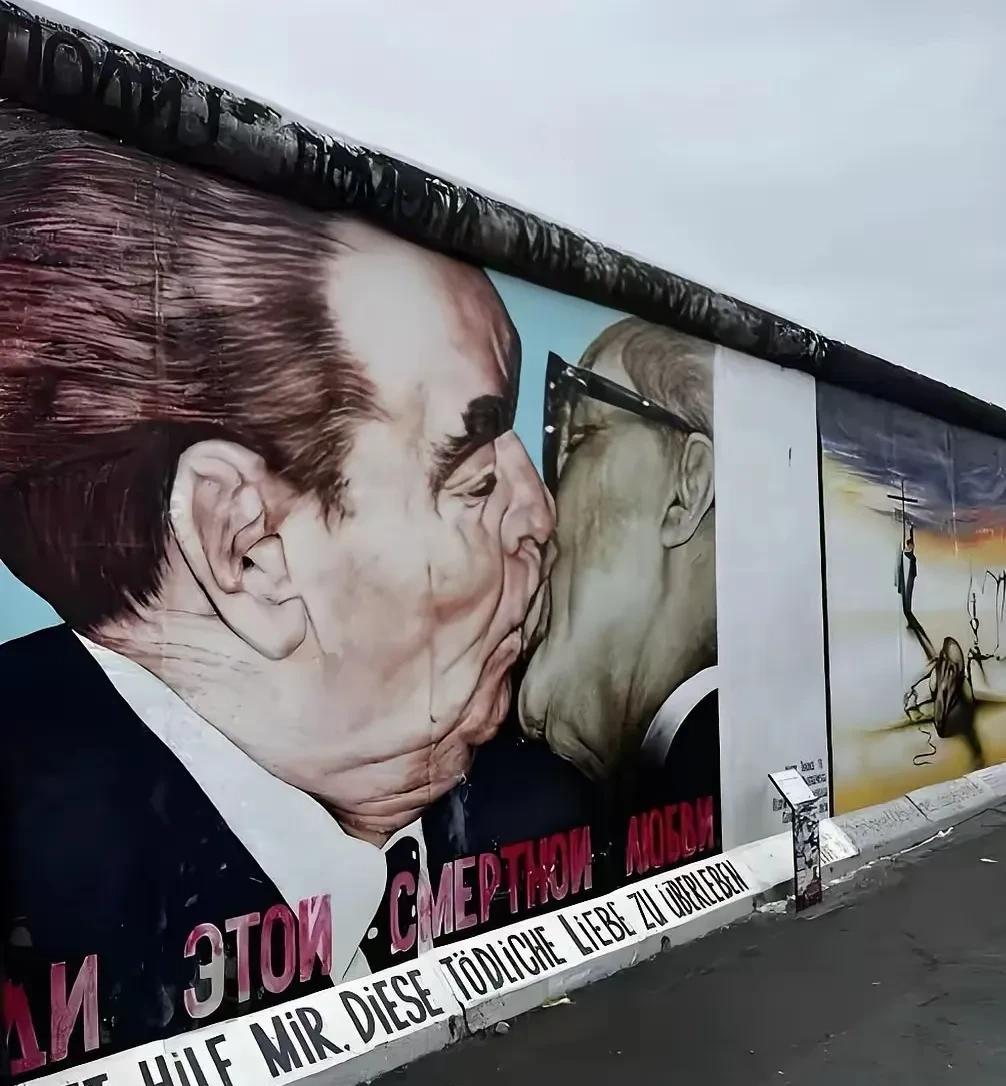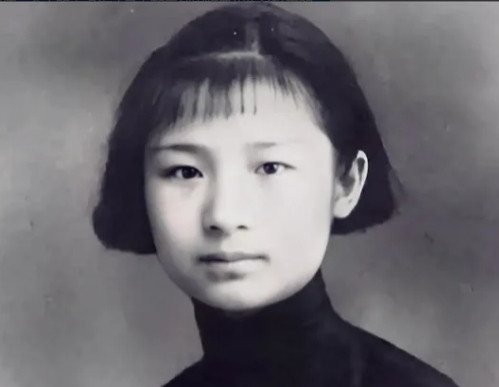1901年,19岁的马一浮丧妻,他发誓不再续娶,岳父怕他孤单,便问他“我三女儿14岁,酷似她姐,要不你娶她吧?”马一浮拒绝:“亡妻地位无人能替,无心再娶。”
这事还得从五年前说起,那时候马家在当地算是有头有脸的读书人家,马一浮打小就显露出过人才华。
16岁参加县考,愣是把鲁迅这些后来的大文豪都比下去了,一举拿下解元,这消息传开后,前清举人出身的汤寿潜坐不住了。
这位后来当上浙江省都督的实权人物,正愁着给大闺女找婆家呢。
要说两家也算门当户对,汤家大女儿汤仪刚及笄,知书达理又会持家。
汤寿潜托人上门提亲时,马家老爷子二话不说就应了,那年月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年轻人成亲前连面都没见过。
洞房花烛夜掀盖头那刻,马一浮才看清妻子模样——鹅蛋脸细眉毛,低眉顺眼的样子倒像幅水墨画。
要说这桩婚事起初也就是旧式婚姻的套路,可日子过着过着就变了味儿,马一浮是个书虫子,经常半夜三更还在书房翻书,汤仪就摸黑起来熬莲子羹,轻手轻脚端到案头。
有回马一浮读《史记》正入神,冷不丁抬头看见妻子踮着脚往书架上够《诗经》,问起来才知道她是想多认些字好陪丈夫聊天,这么着,两人真就处出感情来了。
可惜好景不长,成亲第二年马老爷子过世,按绍兴老规矩得守孝三年,这期间不能办喜事。
偏巧这时候汤仪有了身孕,族里几个长辈急得直跺脚,说什么"冲撞了祖宗要遭祸"。
马一浮拗不过这帮老顽固,硬着头皮去找郎中开堕胎药,谁承想这碗药下去,汤仪的身子骨就再没缓过来,拖了大半年终究撒手人寰。
岳父汤寿潜看着女婿整天失魂落魄的,心里也不是滋味,有天把马一浮叫到跟前,说家里三闺女今年十四,模样性子都随她大姐,要不续个弦?
这话搁当时再正常不过,续娶小姨子的旧例多了去了,哪知马一浮当场就摇头:"三妹年纪尚小,岂能做替代品?"说完深施一礼扭头就走,把老丈人晾在原地直叹气。
要说这人也是轴得很,那年头男人三妻四妾都不稀奇,更别说续弦了。
街坊四邻没少劝他"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马一浮愣是油盐不进。
有回在茶馆听见几个闲汉说风凉话,说什么"装模作样给谁看",他倒好,慢悠悠呷口茶跟没事人似的。
后来有人看见他书房墙上挂着自己写的条幅,斗大的"曾经沧海"四个字,墨色浓得化不开。
打那以后,马一浮真就过起了苦行僧般的日子,白天在之江学堂教书,晚上回来就窝在书房抄书。
最绝的是他用三年时间把《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多册翻了个遍,这事后来被记在浙江省图书馆的档案里。
有学生回忆说,马先生讲课时总带着本磨破边的《礼记》,书页间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那是汤仪生前最爱别在鬓角的饰物。
等到民国初年,马一浮在杭州开了间书院,说来也怪,他定的规矩里第一条就是"只收真心向学之士",第二条更绝:"凡有家室者须以读书为重"。
有次新来的学生不懂事,问他为啥不续弦,老先生摸着花白胡子笑笑:"心里搁着个人,哪还容得下别的?"
这话后来被记在《马一浮年谱》里,边上还批注着"情至深处,金石为开"。
要说这故事里最让人感慨的,还是时间的力量,汤仪墓前的柏树从小苗长到两人合抱,马一浮也从青丝熬成了白头。
有年清明,学生们跟着去扫墓,看见老先生颤巍巍往坟头放枝白梅,嘴里念叨着"今儿带了你最爱看的《楚辞》",后来才知道,他每年清明都带着当年夫妻俩共读的书来祭奠。
这事传到汤寿潜耳朵里,老丈人抹着眼泪跟家里人说:"当初真没看走眼。"
后来汤家三小姐出嫁,马一浮还特意托人送了套《十三经注疏》当贺礼,据说扉页上题着"琴瑟和鸣"四个字,笔迹跟当年写给汤仪的诗稿一模一样。
晚年的马一浮住在西湖边的小院里,每天晨起都要对着东南方作个揖,有好奇的邻居打听,老人家只说是在跟故人问早安。
1967年春天,84岁的马一浮安然离世,学生们整理遗物时,在枕头底下发现个褪了色的香囊,里头装着缕用红绳系着的青丝——那是汤仪新婚时剪下的结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