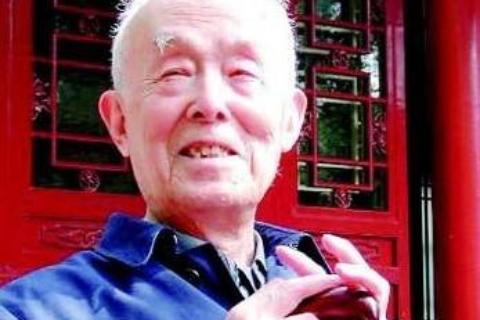[太阳]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参考资料:2006-12-28 京报网——季羡林的贫民底色) 季羡林先生身上最耐人寻味的,恐怕不是学问,而是一种近乎分裂的矛盾:他是个公认的富人,生活却简朴到近乎“寒酸”。 这种反差,远比他等身的学术著作更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能把一个富翁“折磨”成这副模样? 要解开这个谜,得先看看季羡林的人生底色,季羡林早年的人生,就是一个“穷”字,在老家官庄,他是穷娃;到了济南,成了寄人篱下的穷少年,这份贫困,一直跟到他考入清华。 季羡林自己就说过,在清华食堂吃饭,专挑快关门的时候去,好菜没了,就随便买点没人要的“孬菜”,一个人扒拉几口算一顿。 翻开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能看到家底有多薄:拿到一笔稿费,最大的犒劳,无非是上街买点烤红薯、板栗;偶尔请朋友“奢侈”一把,上限也就是一只烤鸭。 更有意思的是,碰上同样拮据的朋友请客,场面就更显朴素了,季羡林日记里写,曾被人两次“拖”到合作社,“结果肚子里灌满了豆浆”,用豆浆管饱,这便是那一代学子清贫又真实的青春。 可以说,早年的穷困,在季羡林心里刻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于这成了他一辈子都擦不掉的底色。 不过,这种穷日子并没有过太久,1946年,季羡林从德国留学归来,端上了北大的铁饭碗,从此便与贫困彻底说了再见。 杨澜曾问季羡林为何放弃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国,他的回答直截了当:“钱多”,他解释说,四十年代中期,北大副教授月薪五十块大洋,正教授八十块,而当时一石谷子才两块钱,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到了五十年代初,季羡林的财富更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作为一级教授,他月工资三百四十五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一百元津贴,每月总收入四百四十五元。 这笔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去高级的“老莫”西餐厅,汤菜、黄油面包加啤酒的一顿大餐,不过一两块钱;吃一只全聚德烤鸭,也就六七块。 季先生的富裕,还有一个旁证:他从那时起开始玩收藏,而且起点极高,给自己定了条规矩——“齐白石以下的不收”,这种底气,靠的可不是情怀,而是实打实的钞票。 按理说,富裕起来的季羡林,总该好好享受一下了吧?可事实恰恰相反,物质上的丰足,似乎完全没能改变他骨子里的简朴,他曾自嘲“胃是农民的”,只爱吃青菜萝卜豆腐。 和季羡林一起吃过饭的人回忆,先生的餐桌简单得惊人:早餐是小米粥、花生米、腐乳;午餐则是馒头、大葱、青菜,他对花生米情有独钟,晚年住院,早餐也必须有这道小菜。 旁人好奇季羡林没假牙如何嚼得动,他只笑笑说“没问题”,有一次,有人特意请他去上海饭店,想让他尝尝鲜,结果他点来点去,还是要了一碗面条配几碟家常小菜。 这份节俭甚至带有一点“严苛”,据儿子季承回忆,季先生“容不得丝毫浪费”,房间里没人看书,灯必须马上关掉;在水龙头前洗东西,时间稍长就会被他呵斥,逼得后来季承和姐姐洗大件衣物,都宁愿拿回自己家去洗。 与季羡林打过交道的人,普遍感觉他身上“看不出半点富贵相”,反而总透着一股“逼人的寒酸气”。 然而,这份对自己近乎“抠门”的吝啬,却和对待他人的慷慨形成了刺眼的对比,他把钱看得极淡,却把人情看得极重,对于有困难的人,无论认不认识,只要找上门来,他几乎有求必应。 更难得的是,季羡林资助了别人还不让对方声张,认为“真诚就不要宣扬,不要报答”,这份菩萨心肠,源于他对贫穷的切身体会,也成全了他研究佛学之外的另一种修行。 财富和地位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却没能改造他骨子里的那份“土气”,也正是这份朴素到近乎“土气”的本真,让他在富足与简朴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