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又一座“青春工厂”,熄灯了。
11 月 18 日深夜,东莞长安镇沙头村的振安中路上,最后一盏厂房灯熄灭了。曾经每天傍晚挤满穿蓝色工服人群的金宝电子厂门口,只剩几个老员工蹲在石阶上抽闷烟,地上散落着刚拍完合影的照片 —— 照片里几百人挤在厂牌下笑,现实里有人抹着眼睛把照片塞进外套内兜,手里攥着刚领的离职补偿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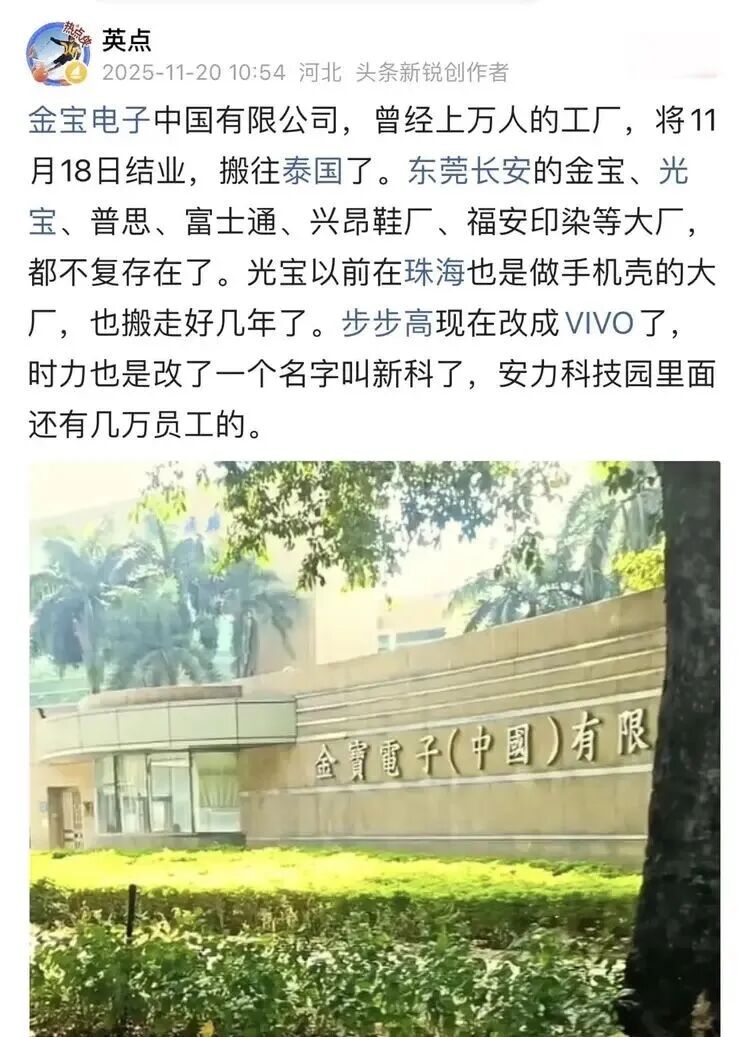
这座从 1996 年就扎根东莞的电子大厂,巅峰时上万工人在这里拧螺丝、焊电路板,每天有装满计算器、手机配件的货车从这里发往全球。可如今,车间里的机械臂被拆得只剩底座,仓库里的纸箱堆成空壳,连食堂墙上 “高高兴兴上班” 的标语都被撕得只剩边角。11 月 19 日一早,第一批载着设备的集装箱车驶出大门,目的地很明确:泰国。
“十年前进金宝,比现在考公务员还难!” 在厂里干了 15 年的李哥翻出旧工牌,塑料壳子已经磨得发亮。2010 年他从湖南老家来东莞,排队三天才挤进厂门,当时月薪 2000 块包吃住,他每个月能往家寄 1500,“那时候觉得在金宝干一辈子都值,车间里姑娘多,不少人在这里处对象、结婚,孩子就放在附近的民办幼儿园。”

最热闹的时候,金宝厂门口的小吃街从早到晚都飘着炒粉香,厂车每天早晚各 20 趟接送员工,周末电影院里一半都是穿金宝工服的人。作为东莞出口十强企业,它生产的计算器曾占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后来还接了惠普、戴尔的订单,代工手机和卫星定位设备,母公司金仁宝集团的年营收能飙到 360 亿美元。
可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李哥记得大概是 2018 年,厂里开始断断续续裁人,后来又把部分生产线搬到湖南岳阳。“那时候就听说泰国厂在招人,那边工人一个月才 800 块,咱们这边底薪都涨到 3000 了,还得交五险一金。” 有次他跟组长聊天,组长叹着气说 “老板要算成本账,东南亚那边政府还给免税,换谁都得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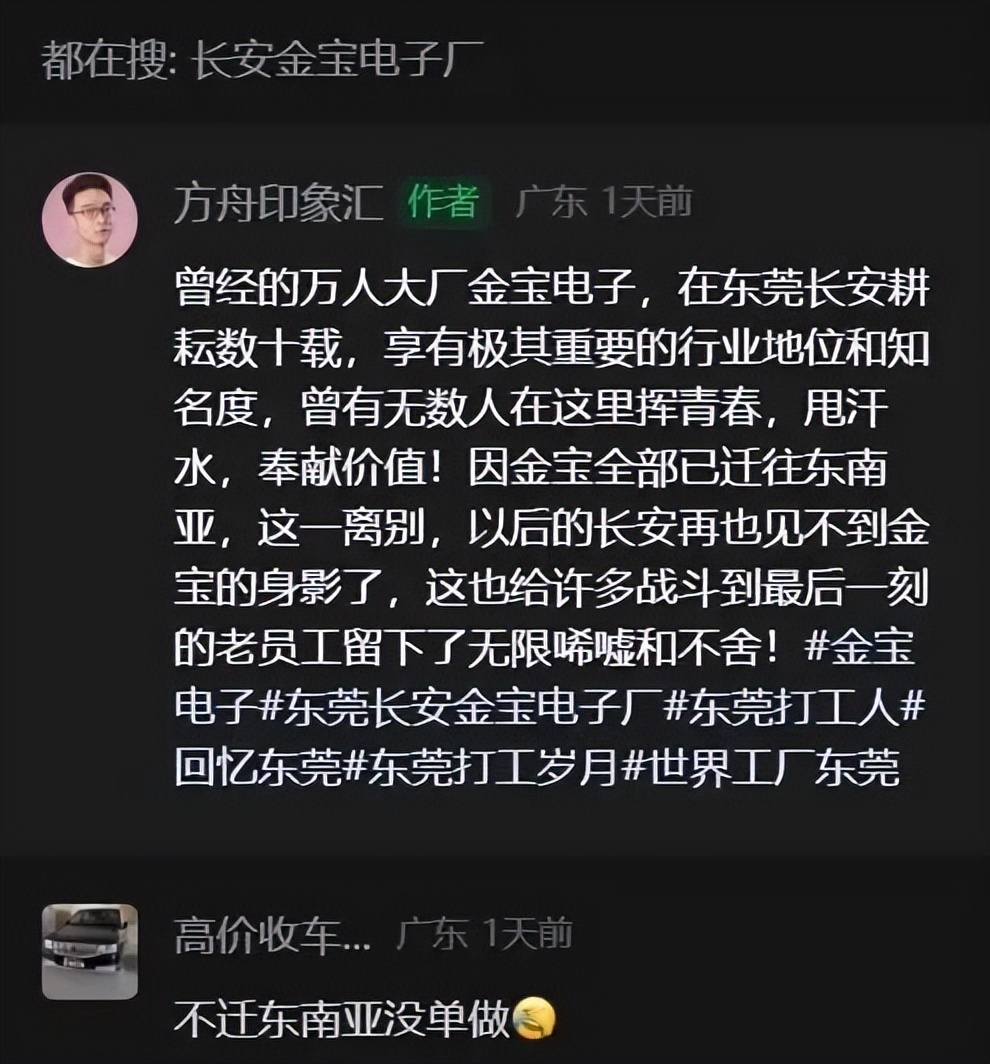
其实早在 2015 年,金宝就出过一次 “悄咪咪搬家” 的事。那年国庆放假,凤凰厂区的员工收假回来,发现车间里的机器全没了,300 多号人堵在门口讨说法,最后只拿到很少的补偿。这次还算 “体面”,干满一年给一个月工资的 N+1 补偿,李哥干了 15 年,拿到近 5 万块,“钱攥在手里沉,可心里空落落的,这年纪再找工作太难了。”
42 岁的他现在每天揣着简历在人才市场转,智能制造厂要会操作机械臂,他连 Excel 都用不利索;外卖平台要求 40 岁以下,他超了两岁;回老家吧,宅基地早就被村里收了,父母年纪大了还得靠他养。“以前觉得在流水线拧螺丝稳当,现在才知道,稳当的日子早被时代甩在后面了。”

跟李哥一起离职的还有张姐,她在质检岗干了 12 年,最骄傲的是自己检查的产品从没出过质量问题。“我儿子去年考上大学,学费还是用厂里发的年终奖交的,现在厂没了,明年学费还没着落。” 她试过应聘超市收银员,老板嫌她 “没服务行业经验”,最后只能先去菜市场帮人理菜,一天挣 80 块。
厂区附近的商铺也跟着冷清下来。开了 10 年便利店的王老板,最近把货架撤了一半,“以前每天能卖 200 多瓶饮料,现在一天卖 50 瓶都难,旁边的理发店、网吧都关门了。” 他指着空荡荡的厂房说,“以前晚上这里亮得跟白天一样,现在黑黢黢的,看着心里堵得慌。”

其实不止金宝,这些年东莞好多老厂都悄悄消失了。光宝厂以前做手机壳很有名,早就搬到越南了;富士通的厂房现在改成了跨境电商仓库;兴昂鞋厂的旧址上在建新能源汽车展厅。有人说这是 “腾笼换鸟”,可对李哥、张姐们来说,“笼子腾出来了,我们这些‘老鸟’却没地方飞了。”

11 月 20 日那天,最后一批员工聚在以前的食堂吃散伙饭,有人带了自家酿的米酒,喝着喝着就哭了。有人说 “以后再也见不到这么多一起熬夜赶订单的兄弟了”,有人说 “希望泰国的厂能好好的”,还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说要留着给以后的孩子看,“你妈以前在东莞最牛的电子厂干过!”
金宝走了,但它的故事不该被遗忘。因为下一个可能就是你我,在技术迭代、成本压缩、全球化博弈的浪潮里,没有人能永远站在安全区。

愿那些散落天涯的老员工,能找到新饭碗;愿这座城市,在追逐“高精尖”的同时,也给“老黄牛”留一条活路;更愿我们记住:
所谓经济奇迹,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时代的齿轮下,咬牙前行的身影。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