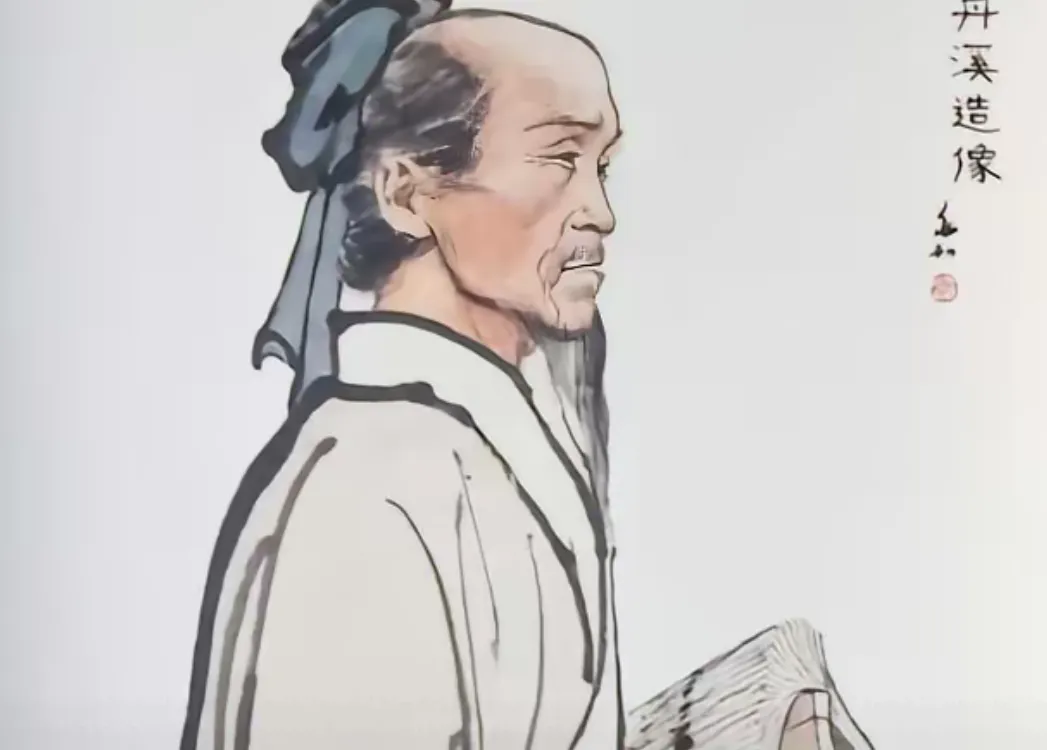元代,名医朱丹溪出诊,偶遇一貌美洗衣女。他咂咂嘴,对同行的侄儿说:“去,弄戏弄戏那女子!”侄儿点点头,上前一把搂住,女子大惊失色,尖叫救命。没想到,不久后却成了朱丹溪的侄媳妇。 女子尖叫着挣开时,发间的木簪掉在青石板上,滚到朱丹溪脚边。他弯腰拾起,见簪子雕着简单的缠枝纹,边角已磨得光滑——这是寻常人家姑娘的物件,却被他侄儿吓得指尖发颤,攥着捣衣杵的手背上青筋都绷起来了。 “朱先生这是做什么?”女子看清朱丹溪身上的药箱,语气里的惊恐掺了几分疑惑。她身后的石阶上晾着半排衣裳,皂角的清苦气混着河水的潮气漫过来,倒比药铺里的陈药好闻些。朱丹溪没接话,只盯着她的脸看,又绕到她身后瞅了瞅脖颈,忽然对侄儿说:“还不快赔罪?” 侄儿红着脸作揖,女子却不依不饶:“光天化日耍流氓,赔个罪就完了?”说着就要往河边的柳树林跑,想喊对岸浣纱的邻里。朱丹溪赶紧拦住:“姑娘莫急,我那侄儿是个憨人,方才是我让他试试你——你这身子骨,怕是有隐疾吧?” 这话倒让女子停了脚。她确实时常心口发慌,夜里总冒冷汗,找过几个郎中都说是“劳气”,抓了药也不见好。此刻被一个陌生老头点破,倒忘了方才的惊吓,只瞪着眼问:“你怎么知道?” “你方才挣开时,左肩抬得比右肩慢半分,”朱丹溪掂了掂手里的木簪,“方才尖叫时嘴角往左边歪,这是肝气郁结的兆头。再看你脖颈后,有层淡淡的青气,不是累出来的,是常年忧思伤了脾胃。”他说得笃定,女子的脸慢慢白了——这些症状,她从没对人说过。 侄儿在旁听得发愣,原以为叔父是见人家姑娘好看,才让自己上前搭话,没成想是在诊病。朱丹溪已从药箱里摸出张药方,用炭笔写了几味药:“先去药铺抓三副,每日辰时煎服。不过这病光靠药不行,得少思虑,多笑笑。” 女子捏着药方没动,半晌才憋出句:“我没钱抓药。”她爹前几年染了风寒去了,娘卧病在床,家里就靠她洗衣缝补度日。朱丹溪哦了一声,又从箱底翻出个小纸包:“这里有些晒干的陈皮和茯苓,先拿去煮水喝,能缓一缓。” 往后半个月,侄儿总借着送药的由头往河边跑。有时女子在洗衣,他就蹲在旁边帮着捶衣裳;有时撞见她背着竹篓去采野菜,就默默跟在后面,见她够不着高处的荠菜,便踮脚替她摘了。女子起初防备,后来见这后生说话脸红,递东西时总先擦三遍手,倒也渐渐松了戒心。 这天侄儿又来送药,见女子正对着件半旧的夹袄发呆。“这是我娘年轻时的衣裳,”女子叹了口气,“想改改给她穿,却总缝不好领口。”侄儿忽然说:“我会。”他自小跟着婶娘学过针线,当年婶娘卧病,家里缝补的活都是他做。 他接过针线,手指虽粗,缝出来的针脚却比女子细密。阳光透过柳叶洒在他发顶,女子忽然发现,这后生虽看着憨,睫毛倒比常人长些。等侄儿把缝好的夹袄递回来,她红着脸说了句:“多谢朱小哥。”这是半个月来,她头回叫他的名字。 朱丹溪把这一切看在眼里。那天他故意让侄儿“戏弄”,本是想试试女子的反应——肝气郁结的人若性子怯懦,受了惊吓只会憋在心里,病情必重;若敢当场发作,倒说明心气未绝,还有救。后来见侄儿对女子上心,女子看侄儿的眼神也软了,便托了个相熟的街坊去说媒。 成亲那天,女子穿着朱丹溪特意让人做的红裙,头上换了支新银簪。拜堂时侄儿紧张得忘了跪,还是她悄悄拽了拽他的衣角。朱丹溪坐在主位上喝了杯喜酒,见新人交杯时,女子笑起来眼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心里便有了数——这姑娘的病,怕是不用再吃药了。 有人说朱丹溪这招“诊病顺带说媒”太冒险,万一女子当真告官,岂不是坏了名声?他却摇头:“医者治病,不光要治身上的病,还得治心里的结。那姑娘缺的不是药,是个能让她安心的人。”后来这对小夫妻过得和睦,女子再也没犯过心口疼的毛病,倒是常跟着侄儿去药铺帮忙,见谁都笑眯眯的。 其实朱丹溪这辈子治过的病人里,有大半都像这洗衣女——病在身上,根却在心里。他常对弟子说:“药材能治寒热,却治不了孤苦。”就像那次看似唐突的“戏弄”,旁人只当是老顽童胡闹,却不知他早已算出,一场惊吓能撞开郁结的肝气,一场缘分能补全亏空的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