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村里有刘王两家,是多年的老邻居,祖上又是远亲,因此两家的关系不同一般,六零年吃大食堂,刘姓男子掌着食堂的大勺,村里饿死了好多人,得益于刘姓男子暗中特殊照顾,王姓一家个个都挺了过来。为此王姓一家念念于怀,两家的关系格外好起来。村里人都羡慕不已。 刘姓男子叫刘老实,人如其名,话不多,却实在。六零年那阵子,他掌着食堂的大勺,手抖一下,多给半勺稀粥,可能就救一条命。给王家的粥,永远比别家稠点,窝头也偷偷多捏半个,为此他自己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家里娃饿得直哭,他也咬着牙没动过私心。王家人都记着这份情,王大爷总说:“老刘是我们家的再生父母,这辈子都得敬着。” 七十年代生产队里上工,两家的田挨着。刘老实力气大,犁地是把好手,每次都先帮王家把地犁了,自己的地黑天半夜才忙活完。王大娘针线活好,刘老实家四个娃,衣裳全是她给缝的,补丁都打得整整齐齐,看着比新的还结实。有回刘老实的小儿子掉进河里,是王大爷跳下去捞的,上来时冻得嘴唇发紫,抱着孩子往家跑,鞋都跑丢了一只。 那年头谁家都不宽裕,可两家有啥好东西,总想着对方。王大爷赶集换了两斤红糖,回家就分出一半给刘家;刘老实打了只野兔,收拾干净,剁成两半,拎着就往王家送。村里孩子眼馋,围着看,刘老实的大儿子就喊:“王婶做的野兔汤最好喝,你们谁也抢不走!”王大爷的闺女听了,咯咯笑,把手里的野兔腿塞给他。 有一回,生产队分棉花,王家分的那批有点潮,王大娘看着犯愁,怕纺不出好线。刘老实没吭声,夜里扛着自家的棉花去了王家,把潮的换了回来。王大爷发现时,棉花都快纺完了,气得要把棉花送回去,刘老实拦着说:“当年你们家要是没挺过来,我现在看谁去?这点棉花算啥。”王大爷眼圈红了,转身杀了家里唯一的老母鸡,炖了锅汤,两家老小围在一起喝,热乎气儿飘出老远。 村里有人不理解,说刘老实傻,当年的情分早该还清了。刘老实听了,嘿嘿笑:“人家王大哥跳河救我娃的时候,咋不说还清了?”也有人说王家人太较真,没必要天天把“报恩”挂嘴边。王大爷听了,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人活着,不就图个良心安稳?人家给的是命,咱还的是心,这不一样。” 最让人记挂的是1976年那场大雨。村里的土坯房漏得厉害,王家的屋顶塌了个角,王大爷急得直转圈。刘老实带着三个儿子,冒着瓢泼大雨就来了,踩着梯子上屋顶,用塑料布、稻草一层层糊,刘老实的二儿子脚下一滑,从梯子上摔下来,胳膊擦出老大一块血,爬起来揉揉,又往上爬。王大娘在屋里煮姜汤,手都抖,嘴里念叨:“这可咋好,这可咋好。” 雨停后,王家的房子修好了,刘家的墙却被水泡松了,第二天塌了半边。王大爷二话不说,带着全家老小上了阵,搬石头、和泥巴,比修自家房子还卖力。王大爷的小儿子才十岁,也跟着搬碎砖,累得满头大汗,说:“刘叔上次救了我哥,这次该我帮刘叔了。” 村里人看着这两家,慢慢不说羡慕了,改成了敬佩。有户人家吵架,媳妇哭着回娘家,婆婆就指着刘王两家的方向说:“你看看人家,当年一点恩,记了一辈子,互相帮衬着过日子,哪像你们,为了个鸡蛋就吵翻天。” 后来分田到户,刘老实种的麦子总比别家好,他就把育种的法子教给王大爷;王大爷会编竹筐,编好了就挑到镇上卖,回来总给刘家的娃买块糖。两家的娃长大了,互相帮着说媒,刘家的闺女嫁了王家的侄子,亲上加亲,办喜事那天,全村人都来帮忙,热闹得很。 现在刘老实和王大爷都不在了,可他们的后人还住在老地方,门对门。春天一起种玉米,秋天一起收豆子,谁家有难处,另一家准第一个到。有回刘家的孙子在城里买房子差钱,王家的孙子二话不说,把准备买车的钱先垫上,说:“老祖辈传下来的规矩,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村里人都说,刘王两家的日子,过得像灶台上的铁锅,看着普通,却总透着股热乎气。其实啊,这世上最牢的情分,从来不是嘴上说得好听,而是你帮我一把,我记你一生,不是算着“谁欠谁”,而是想着“我能为你做啥”。 就像六零年那碗稠粥,暖了王家人的胃,也暖了两家人的心。往后的日子里,你添一把柴,我加一瓢水,日子才能烧得旺旺的,情谊才能传得远远的。这道理,搁到啥时候都管用。 ——《乡村岁月里的互助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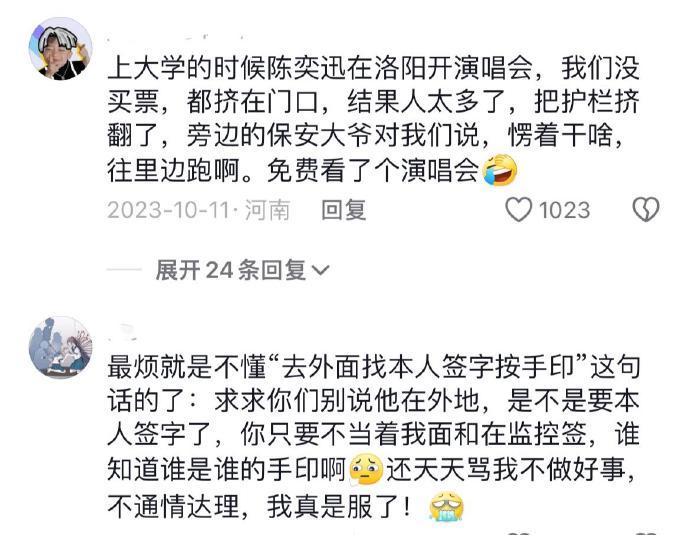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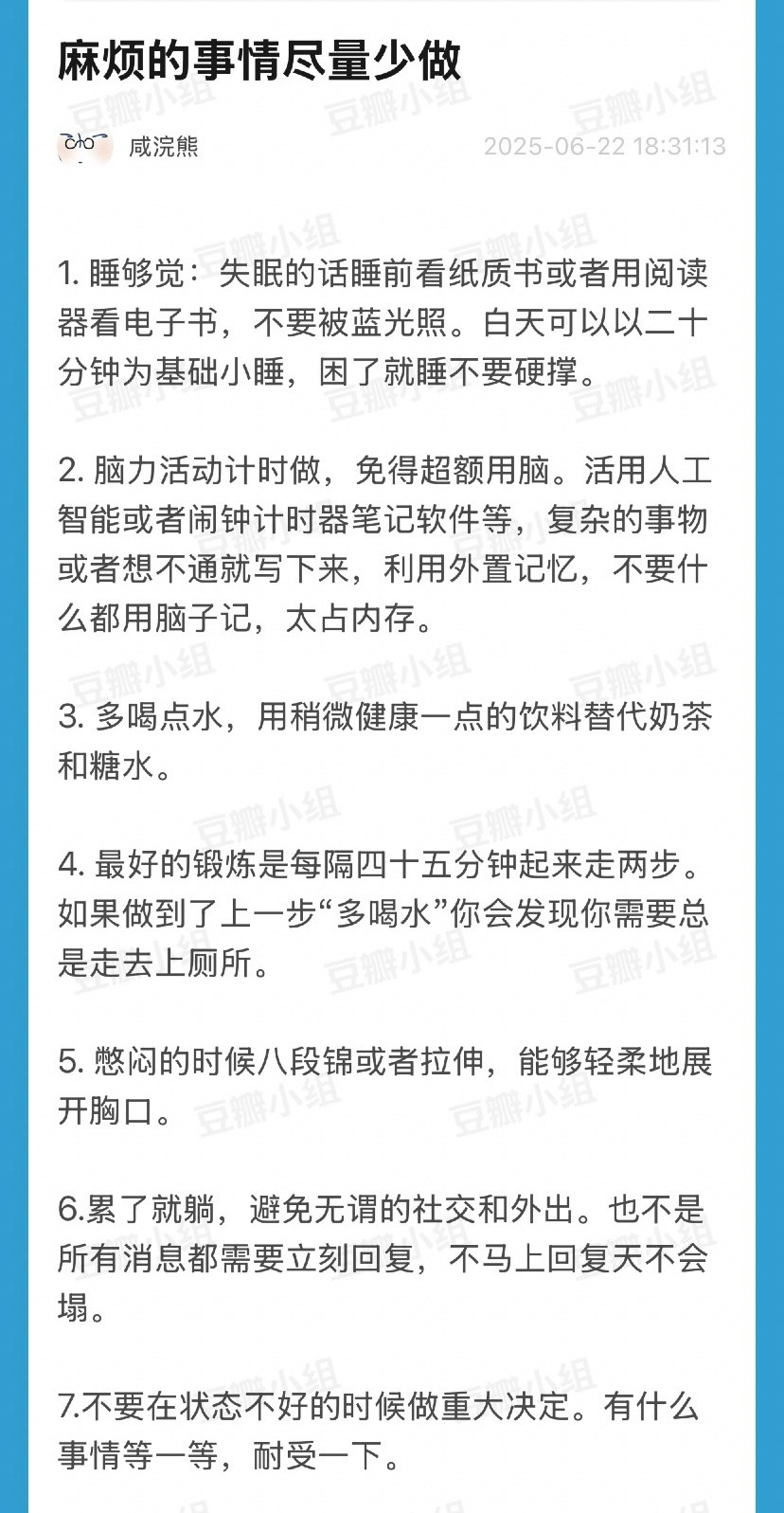

静肃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