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 年,21 岁知青李文忠救起一名 11 岁的落水女孩。然而,女孩竟认真地对他说了一句:“你别结婚,等我长大了,我就给你当媳妇儿!” 李文忠正拧着湿透的衬衫,闻言笑出了声,用手背拍了拍她的后脑勺:“傻丫头,先把鼻涕擦干净再说。” 他没当回事,这年头像他这样的北京知青,村里的姑娘们难免多看几眼,但一个 11 岁娃娃的话,谁会往心里去? 可刘俊霞却当了真。第二天一早,李文忠发现窗台上多了个粗瓷碗,里面盛着两个热乎乎的玉米面窝头,碗底压着张歪歪扭扭的纸条:“李大哥,谢谢你。” 往后的日子,他走到哪儿,这丫头就跟到哪儿。他在大队部记账,她就蹲在门口帮他整理散落的票据。 他在夜校教孩子们认字,她就坐在第一排,眼睛瞪得溜圆;连他去河边洗衣服,她都会提前把石头摆好,让他能坐着搓衣裳。 乡亲们看出了门道,打趣李文忠:“你这是提前把媳妇儿养上了?” 他总是红着脸摆手:“小孩子家懂啥。” 心里却也暖烘烘的。 这年冬天,他收到北京家里寄来的棉鞋,转手就给刘俊霞送去了 —— 她的布鞋早就磨破了底,冻得脚后跟通红。 刘俊霞捧着棉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突然踮起脚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扭头就跑,像只受惊的小鹿。李文忠愣在原地,摸着脸笑了半天。 1975 年知青返城的消息传来,李文忠收拾行李时,刘俊霞就蹲在门槛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搓着衣角。 离村那天,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他回头望了三次,每次都看见那抹瘦小的身影站在村口老槐树下,像根钉在那儿的木桩。 车拐过弯,看不见了,他才掏出贴身藏着的一张纸条 —— 是刘俊霞塞给他的,上面写着:“我会去找你。” 回到北京,李文忠进了机床厂,日子过得按部就班。母亲给他介绍了个纺织厂的姑娘,见面那天,他看着对方精致的发卡,脑子里却莫名想起刘俊霞扎着布条的麻花辫。 相亲没成,母亲急得直叹气,他却总说 “再等等”。1977 年冬天,车间里炸开了锅 —— 高考恢复了。 李文忠连夜找出压箱底的《数理化通解》,白天上班,晚上就着 15 瓦的灯泡学到后半夜,手指冻得握不住笔,就往嘴里含一下。 开春时,他收到一封来自陕西的信,信封上的字迹娟秀了许多。刘俊霞说她高中毕业了,不想嫁人,想考大学,问他能不能帮着看看复习资料。 李文忠眼睛一亮,赶紧把自己整理的笔记誊抄了一份寄过去,末了加了句:“我也在考,咱们一起努力。” 放榜那天,李文忠挤在工厂的布告栏前,心脏跳得像打鼓。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 “李文忠” 三个字时,他突然想起刘俊霞,不知道那丫头考上了没有。 正愣神,传达室大爷喊他:“小李,有你的挂号信,陕西来的!” 拆开一看,是张录取通知书,和他报考的竟是同一所大学! 照片上的刘俊霞剪了短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开学那天,李文忠在报到处前等了半个小时,终于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刘俊霞背着个旧帆布包,站在人群里东张西望,个子长到了他的肩膀,眉眼还是老样子,只是褪去了稚气,亭亭玉立。 “李大哥?” 她试探着喊了一声。李文忠快步走过去,喉咙有些发紧:“小霞,你真的来了。” 大学四年,他们成了校园里最惹眼的一对。刘俊霞还是改不了老习惯,总跟在李文忠身后,却不再是那个只会默默递水的小丫头。 她会在课堂上和他争论《红与黑》的主人公,会在他写论文时帮他查资料,甚至会拉着他去参加学生会的辩论会。 有次李文忠发烧,她守在宿舍外,硬是把熬了整夜的姜汤从窗户递进去,烫得自己手背上起了泡。 毕业前的那个中秋,两人在操场散步,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刘俊霞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认真地说:“李大哥,我长大了。” 李文忠看着她眼里的光,突然想起 1972 年那个夏天,河滩上女孩湿漉漉的誓言。他没说话,只是伸出手,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1982 年的婚礼很简单,北京的亲戚和陕西的乡亲来了不少。 刘俊霞穿着红棉袄,给李文忠的父母敬茶时,还红着脸说了句:“爸妈,我当年就说过,要给李大哥当媳妇儿的。”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李文忠看着身边的姑娘,突然觉得,这世上最靠谱的承诺,有时候偏偏藏在最稚嫩的童言里。 后来他们有了两个儿子,老大出生那天,刘俊霞躺在产房里,握着李文忠的手说:“你看,我说过的吧。” 参考来源:中华网文化|暮色青春——知青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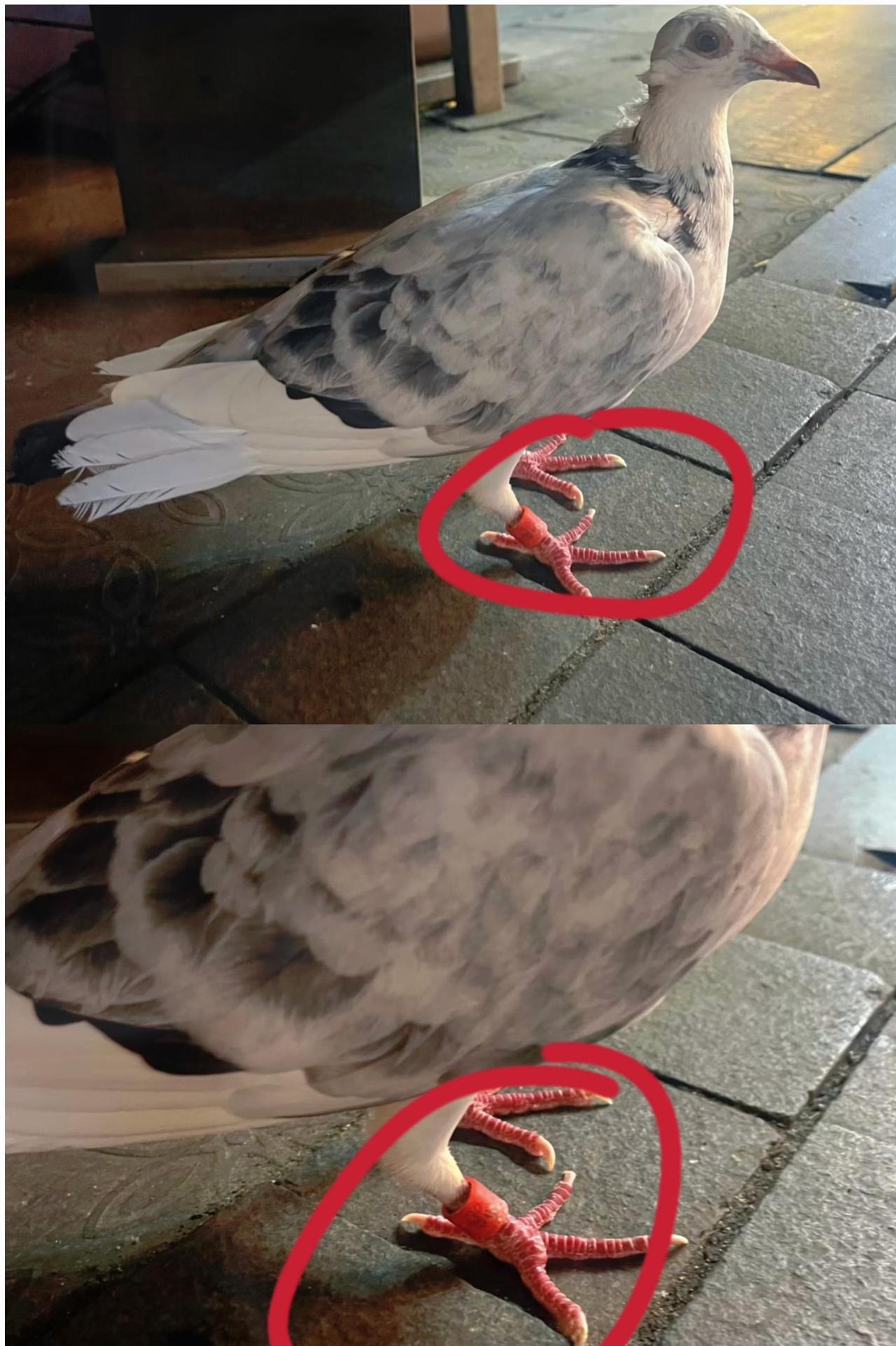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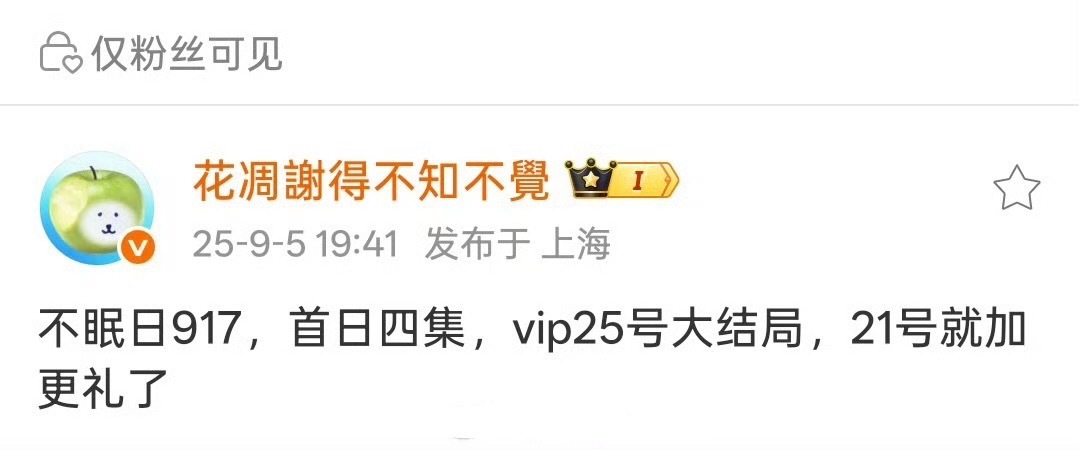
![国内小仙女,国外女保姆[笑着哭]](http://image.uczzd.cn/15607976452770489910.jpg?id=0)

车夫斯基
要相信这世界上有真情,这世界上有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