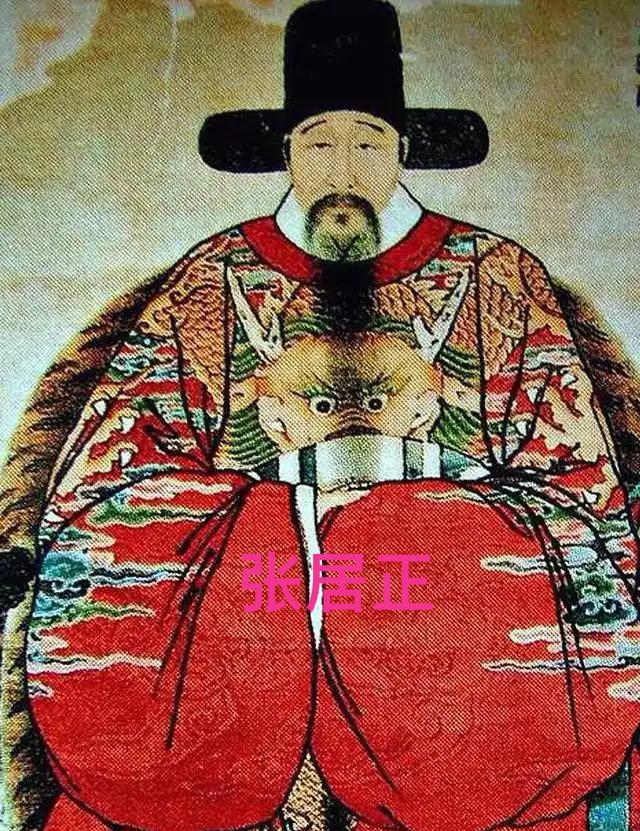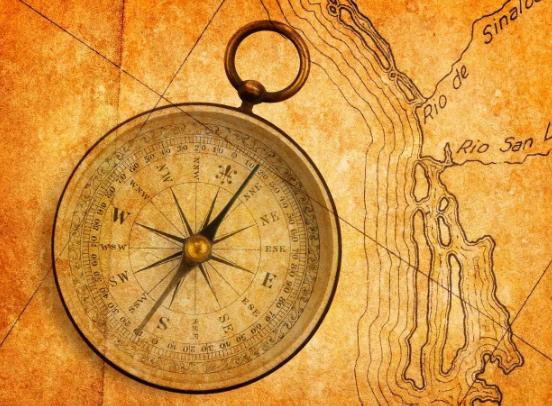古人也要刷牙:从嚼树枝到刷牙子的那些事儿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中国历史剧烈转型的节点,王朝频繁更替,士人风气独特,礼法与养生观念也随之发生转变。在这个既有战乱纷争又有文化融合的时代,关于日常生活的细节记录虽然不多,但从为数不多的出土文献与文物之中,仍可窥见当时人们在口腔清洁方面的讲究与探索。 这一时期口腔卫生习惯的形成,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对先秦两汉以来生活经验的延续与深化。 早在秦汉时期,就已有“晨嚼齿木”之说。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明确记录了人们清晨使用齿木擦牙的习惯。齿木多为杨柳、榆木等枝条,一端咀嚼成纤维状后用于揩齿,颇似现代牙刷的刷毛。这种方法本身体现出古人对于口腔健康的基础认知,即通过机械摩擦除去牙垢并保持口气清新。 更进一步的分层使用,例如贵族选用香气浓郁的沉香木,平民使用随处可得的柳枝,说明当时已经存在明确的清洁阶层差异,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等级分化”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礼制体系对个人卫生行为的影响。 漱口作为古代最常见的口腔清洁手段之一,在魏晋时期也有明确的记载。 《礼记·内则》早已提出“鸡初鸣,咸盥漱”的生活规范,到魏晋时期,漱口法更是逐渐制度化并融入日常起居之中。漱口液的材料不一,最常见者为淡盐水,亦有使用茶汤、药草汁液者。 盐水具有一定的杀菌和清洁作用,在没有现代化抗菌技术的年代,是一种简便有效的解决方案。 有些士人甚至在晨起之际含香草于口,借助香气驱除口腔异味,亦可舒展精神,这种结合芳香与保健功能的习惯,与印度佛教中“净口”的修行实践不谋而合。 自东汉以来,使用手指蘸盐粉揩齿的方式逐渐普及。 魏晋时期,这种方法与齿木并行不悖,成为多样化口腔清洁手段的一部分。 《五十二病方》中曾载有以青盐、明矾制成粉末,结合手指或布巾进行擦牙的方术。这一做法不仅具备清洁牙面的作用,也兼有除口臭、抑制牙龈出血的功效。 当时医家对口腔疾病已有基本认识,例如牙痛、牙龈出血、口气异味等,都被视为体内湿热或脏腑失调所致,往往通过内服药与外用方结合处理。 张仲景等医学家的著作中也记录了使用青黛、鸡舌香、佩兰等药材进行口腔清洁的配方,强调中药材在防治牙疾中的作用。 在魏晋佛教影响扩大的背景下,口腔清洁习惯被赋予了更多精神与礼仪的意义。 敦煌壁画中多次出现僧人于晨起打坐前,以杨柳枝或齿木洁口的图像。这些形象并非仅为装饰,而是对当时僧侣生活细节的真实描绘。 佛教强调外在洁净以辅助内在修行,口齿之清被视为身体净化的一环。僧人普遍使用柳枝咀嚼后擦牙的行为,在信徒中也有较强示范作用,从而影响到更广泛的民间洁齿习惯。 牙签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使用,并出现专门盛装牙签的器具。湖北地区出土过多枚牙签筒,其形制多为青铜或骨制,外壁常饰有几何纹或动植物纹饰,既具实用功能,也体现了工匠技艺的发展。 牙签的普及,一方面说明饮食结构中纤维性食物较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对仪容整洁的重视。饮宴、会客、讲学之际,保持牙缝干净被视为教养的象征,这种礼仪意识进一步推动了口腔清洁工具的演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虽未发明现代意义上的牙刷,但相关技术已在积累之中。 到南北朝后期,关于植毛工具的零星记录开始出现。例如部分文献中提及用兽毛制作擦齿用具,多为马尾、猪鬃等质地坚韧而不易脱落之材。 刷毛的固定方式尚未明确记载,但由唐代出土的部分口腔清洁器具可推知,其雏形已然存在。 除工具外,魏晋时期的牙粉配方亦日趋复杂。 不仅使用矿物成分如盐、矾石,也开始引入芳香药物如丁香、沉香、龙脑等,这些配方不仅注重清洁效果,更强调口气清新与味觉体验的融合。 有些贵族甚至将制牙粉当作一种日常手艺,交由家中仆役专门配制。制粉用具常见者为铜臼、木杵,需反复碾磨至极细方可使用,其过程耗时颇多,亦显示其为身份的象征之一。 这一时期还未见“牙结石”一词的明确记载,但牙垢清除的方法已有流传。 如《外台秘要》中的一则偏方主张用细砂或鱼骨粉揩齿,以去牙垢光洁齿面。南朝医家陶弘景曾提及以“蚌壳末”入药粉,可除黄渍、美白牙色。虽然手段简陋,但说明当时人们已能意识到口腔表面沉积物对健康与美观的影响。 牙齿清洁在魏晋时期不仅限于实用层面,更渗入审美观念之中。 《世说新语》中形容士人的“皓齿朱唇”,表达的不仅是仪表之美,更暗含口齿洁净的重要性。清洁的牙齿成为风雅与涵养的象征,甚至影响婚姻择偶与社会评价标准。 文学作品中的“明眸皓齿”“齿若编贝”等辞句,固然带有夸饰意味,但也反映出洁齿在文化心理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