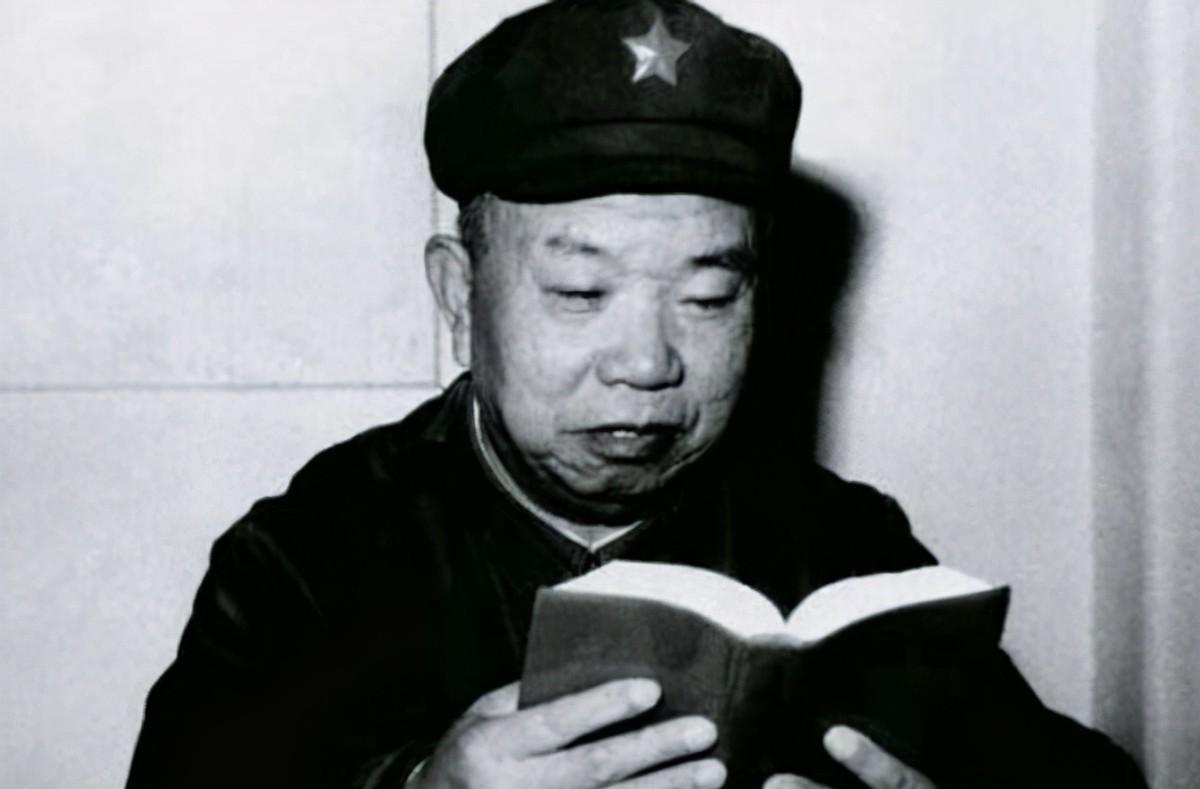开国大将王树声之子回忆:父亲一生打恶仗,不迷信,却逢七便倒霉 【1988年深秋,什刹海旁】 “王政委,您父亲真信‘逢七不顺’这种说法吗?”记者刚落座便提问。王鲁光抿了口茶,眉毛一挑:“他呀,连菩萨都不会多看一眼,可命运偏偏喜欢拿‘七’开玩笑,这才有了说法。” 王鲁光的这句玩笑,让人忽然想到父亲一辈子翻山越岭的锋刃岁月。若把王树声的战场经历摊开,1927、1937、1947这三道年轮确实红得刺眼,像一把年轮上的刻刀,总在七字节点重重划下。 1927年,蒋桂战争尚在胶着,国共合作骤然瓦解。湖北黄安的稻谷还没完全收割完,22岁的王树声已经领着百余名赤手空拳的农民在山道间穿梭。他不服气:“没有枪?那就去夺!”于是黄麻起义爆发。十一月初的夜色只有油灯光,枪声一出,黄安县城的古旧石墙像被闷雷炸裂。起事成功不过几天,十二军教导师压境,敌我力量悬殊。王树声把仅有的轻机枪布在巷口,硬撑到子弹打光才下令突围。黄麻城外的竹林成了掩护,他边撤边将伤员背到山沟。那一役,他失去近半弟兄,却摸清了自己最适合的打法:贴着泥土,靠游击慢慢磨。 时间拨到1937年初,西北高原的风比子弹更利。西路军2.1万人渡过黄河,目标是张掖—酒泉一线。徐向前、陈昌浩站在军参谋图前说“必须西进”时,王树声皱了眉。他懂后勤缺口有多大,但军令如山,他只能把疑虑压进肚里。古浪一战打得艰难,马家军骑兵昼夜冲杀。火力不足,王树声干脆把饲养员、卫生员编进枪排。十几天连轴转,他连睡觉都抱着短枪。到祁连山时,横贯草原的雪线挡住归路,西路军再难凝成完整建制。最终,二十余人勉强突围,队伍零落得连野狼都提不起兴趣。有人劝他北上投靠新三军,他摇头:“走散了还能聚,方向乱了就完了。”这股执拗劲儿,后来被战友总结成“王疯子脾气”。 如果说前三十年代的“七”让他体会到残酷,那么1947年的“七”更让他咽下苦涩。解放战争伊始,中原野战军被裹进蒋军“丁字形”合围。王树声身为一纵司令员,肩上还背着中原军区副司令的担子。那年盛夏,淮水一带蒸得喘不过气,部队饥渴、弹药匮乏,夜行百里要靠从稀泥里捞野菜榨汁充饥。突围失误后,损失数字让他直皱眉:两千余人、千支枪。12月8日,他给中原局发长电,自责“战术迟滞”“干部思想僵硬”。据信发出数日,他仍拿着草稿改来改去,像在给死去的兄弟写诀别信。 有意思的是,王树声哪怕屡遇险境,也没在战场上求过神佛。行军途中碰上破庙,他只会把泥佛搬到墙角给伤员腾地儿。有人悄悄摆香,他会当场呵斥:“枪膛里没油,不去擦,烧什么纸?”但他又固执地记录“七”带来的不幸:七年、七月、七日,只要部队伤亡集中过大,他就会在日记边缘画个小圈标注。或许这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残酷的备忘,提醒自己不许再失误。 战争之外,王树声的生活朴素得甚至有点“掉价”。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在湖北处理剿匪,再到国防部主管训练。亲戚想借势进城,他摆手:“公家权力不是家传田契。”一些乡里人不解,他也不辩解,只给地委打电话让乡亲领救济粮。家里孩子想吃细粮,他回一句:“配给怎么发就怎么吃,司令员的嘴和战士一样咸。”这股石头缝里蹦出的直脾气,持续到生命最后。1972年他患重病,白天喘息困难,夜里却坚持口述战史给秘书记录,理由是“伤疤摊开给后辈看,比唱赞歌管用”。 不得不说,他的一生确实被“恶仗”包围。黄麻起义的破城墙、祁连山的漫天飞雪、中原突围的硝烟,大多是死中求活。可人在激流里漂久了,总会留下某些奇怪的符号。“七”就是那道符号。王鲁光轻轻合上父亲的旧日记,里面字迹凌乱,唯数字“7”被圈得厚重。聊到此处,他意味深长地补一句:“父亲不怕‘七’,他怕的是人忘了那几场败仗。” 战神也曾狼狈。那些失败、折损、遗憾共同塑造了王树声。数字不过是数字,真正刻在血脉里的,是一个老兵对战友和责任的执拗。